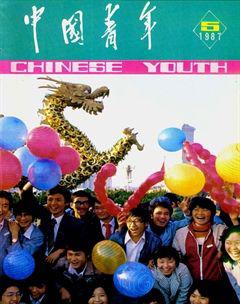他抓住了“狗儿爷”的魂
陈传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话剧《狗儿爷涅槃》,象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近年来萦绕在话剧界人士和观众心头“不景气”的阴霾。该剧以浓墨重彩,深刻描塑出一位视土地为命根子的传统农民的肖像。他善良、质朴、勤劳,在渴望发家的强烈愿望下,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流露出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有时还有那么一丝狡狯贪吝的小私有个体劳动者的特性。他的复杂多舛、大起大落的命运,强烈撞击着观众的心灵,并使人们在酣畅大笑之后陷入沉重的思考。
随着该剧的场场爆满,越来越多的观众被“狗儿爷”的扮演者林连昆的表演艺术魅力所折服。他紧紧抓住狗儿爷的“魂”—渴望占有土地的那种惊人的忍耐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这个魂一直贯穿到他获得土地娶媳妇,失去土地发了疯的一生中。林连昆的表演,哪怕一个极细微的形体动作,都透着那股劲,给人真实可信而又淋漓尽致之感。
解放后,狗儿爷好容易分到了土地,合作化前又买下了别人的一块好地“聚宝盆”,眼瞅着地主祁永年那样的排场日子指日可待了,但还缺个媳妇,正好同村的要他去相个小寡妇。狗儿爷乐颠颠地直奔而去。当他见到19岁的水仙花似的冯金花时,抑制不住满心欢喜。林连昆设计这“满心欢喜”的动作是—一个劲儿地围着金花转磨,瞅也瞅不够,又不敢太亲近。整个动作透着那股求亲心切,马上就成的劲,但又朴实憨厚,毫无油滑放荡之嫌。一夜之间,土地归了大堆。在猛然失去土地的强刺激下,狗儿爷疯了。这种疯,在舞台上是很难演的。疯得太多了,让观众厌烦;疯得不够,又不合剧情。林连昆把握着疯的分寸,不演疯,象常人一样真听真看真实地交流,在关键当口却疯出了狗儿爷的魂来。比如受到失去土地的强刺激,这是狗儿爷疯的高潮。林连昆设计了在舞台上疯跑着拉屎,要将屎拉在自己的地里,最后找不到自己的土地,拉在裤子里这样一个强烈的形体动作。观众在大笑之后品尝到的是狗儿爷内心的辛酸苦涩,是一种蕴含着泪的苦笑。
林连昆在台词上的造诣,也堪称一绝。在《狗儿爷涅槃》里,狗儿爷在坟地上有一大段台词,700多字,几乎相当于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处理起来难度相当大。林连昆在处理这些台词时,不是为表演台词而表演台词,而是,首先经过加工,还原成生活中人物的本来语言,语气注重轻重变化,时而清楚明白,时而嘟嘟哝哝唠唠叨叨,并加了一些语助词,听起来就象同观众娓娓谈心,可亲可切。他的语言塑造能力很强,能根据不同剧情的要求,借助方言塑造人物。林连昆祖籍福建,生长在北京,平时一口流利的京腔,但在《红白喜事》中饰郑二伯,一口唐山味;饰《左邻右舍》里的洪仁杰,一口北京土话;饰《绝对信号》里的老车长说的是标准普通话;而饰狗儿爷,在同金花定情那段戏里,有几句台词—“芝麻掉到针眼里,巧啦!咱们成啦!”“不成?不成再说。咱长长的功夫,耐耐的性,你看还怎个?”—竟念出了信天游、陕北道情的韵味。这些创造实践了他的表演艺术观点:台词能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情感和气质,这样创造出的人物,才有根。
一位司机说:“不管演什么戏,只要有林连昆,我就愿意买票。”一位观众说“如果话剧有‘金鸡奖‘百花奖的话,林连昆无疑是‘最佳男主角最热门的候选人。”我想,话剧舞台要想景气,就应该有象《茶馆》《狗儿爷涅槃》这样抓魂的戏,就得有象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等名角儿那样的演员,一挂牌就满座。这样,我们的话剧艺术就和人民群众紧紧贴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