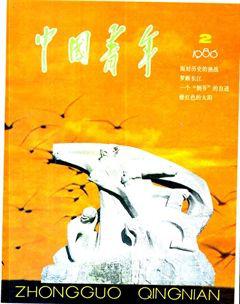橙红色的太阳
梁粱
左树声1985年生 足球运动员
(天津河西区有个地方叫土城,土城有户人家姓左,左家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踢足球。人称“左氏三雄”。才能大左树起,老三左树发,老二就是左树声。
左树声1979年入选国家队,1981年出任国家队队长,绰号一:坦克;绰号二:推土机。1985年5月19日,中家队败于香港队脚下。随后,127名闹事球迷被抓,曾雪麟教练辞职,国家队解散,左树声含泪回到天津土城。)
早先土城的孩子净光脚丫子踢球。我们哥仨都是这么踢出来的。为嘛?半个月一双鞋,买不起。我瘾头最大,上场就嗷嗷叫。光脚丫子在十地上蹬,一划老长一个口子,拿纱布包包,还得上。我爸爸看我都踢野了,揍我。揍也踢。想不踢也没辙,这双脚丫子不能遇见球,遇见球就得踢。
到后来,人说我天生是块踢球的料。这话沿说错除了足球,我从小就没喜欢过别的玩艺儿。你说男人该干什么?是啊,男人可干的多了。可我说男人就该踢球!你往场上一站,那对抗,那竞争,那拚搏,你躲都躲不开。怕这怕那你上不了足球场,偷奸耍滑你上不了足球场,你没力量没速度不咬牙也上不了足球场。这就是足球让人着魔的地方,别的什么都没这效果。也有人不地道,不踢球,成心踢人。碰到这种事,我也不吵,我就想:这小子没出息!
开始是野踢,没嘛想头。把足球和国家连到一起,是七六年进了天津队以后。沈福儒是我们教练。他跟我说:树声,你踢球是那意思,你得进国家队,他给我讲我们国家足球史,说贺老总说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说我们这帮人不行了以后得看你们了,说你好好练我好好教,你一定得进国家队。沈教练给我影响很大。我从他那儿明白了球踢好了能给一个国家争光,也知道了当个运动员不好好干会给老百姓添恶心。我这个人踢球豁得出去,我发誓进国家队。
七九年,我真的进了国家队,而且一踢就是六年。
(这六年,是中国足球史上最为激昂、也最为悲壮的六年。中国足球的水平和中国球迷的热情双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足球健儿南征北战,几起几伏;父老乡亲翘首企足,大喜大悲。左树声经历了这一切。)
那年我21岁,好些事还没怎么懂。比如:我们的足球同世界水平差距到底有多大,一个国家队队员肩上担子到底有多沉,我们要冲出亚洲前头有多少困难,都不是很清楚。刚进队就去新加坡,踢22届奥运会预选赛。当时教练是年维泗,老队员有相恒庆、李福宝。那回我们没出小组就让人家给踢下来了。回国后,年指导辞职,国家队改组,相恒庆、李福宝离队。他俩都踢了十来年,都想踢进奥运会,结果含着眼泪走了。我心里挺不好受。说实话我当时个人压力并不大,我是新队员。可看着老队员就这么走了,心里不好受。我还跟自己说:左树声,你以后可不能这么走。
苏永舜从广州来了,国家队重新组建。这届国家队任务很明确,就是踢第12届世界杯。那时候我们信心挺大。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届国家队是建国以来最强的国家队。再说,那时候形势也比以前好多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就是那时候叫响的。关心体育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足球,球迷呼啦一下子就冒出来一大片。你知道一个国家的足球要想上去,没有真正上瘾的球迷那就别想。
(1981年,世界杯外围赛拉开战幕。中国足球队驻军北京,以3:0大胜科威特;继而挥戈马来西亚,以4:2力克沙特阿拉伯。届时,国内十数座城市齐鸣鞭炮,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中国足球队万岁”呼声震天。上海某大学有三名学生,欲做火把,苦于就近没有燃料,便随手点燃了自己的床单和枕巾。人们认定:此次出线,胜利在望。左树声的两个绰号,即得于此时。)
踢足球得讲个气势。输赢先撂一边儿不说,一场球从头踢到尾,你那个气势不能减。对手再横再奘,你心里不能先怕他三分;人家先破了你的门,赢了你了,只要终场哨声没响,你就得拼就得抢,还差一分钟,你也得想着捞回来。你要是怵头,要是泄气,对不起,那就请您走人,您踢不了足球!
那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踢了几场好球。踢得痛快、漂亮。赢沙特那场,就是先0:2落后,离终场还有20分钟,一连进了四个球,反败为胜的。几场球下来,大伙儿更来情绪了,说:这回非“进军西班牙”不可了。但后来情况变了。第二次跟科威特踢,中国队不能抢球,只要两人撞到一起,裁判就判中国队犯规;中国队还不能向前突破,一突破就吹你越位。这球简直没法儿踢了。结果我们0:1输了科威特。还有一场是新西兰对沙特,本来新西兰已经出线无望,没想到沙特队敞开大门让人家灌,愣送了新西兰5个球。我们当时看电视转播,气得把电视机关了好几次。这还叫踢足球吗?最后,中国队又和新西兰加赛一场,结果1:2输了。
回国后,苏指导辞职,国家队又一次大换血。苏指导在总结会上发言,一边说一边掉眼泪。他说:“不用强调客观,说到底,还是我们功夫不到。如果我们具有巴西队、联邦德国队那样的实力,人家再搞小动作也白搭。身为国家队教练,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在绿茵场上耗尽了青春的老队员。我个人最大的遗憾,是永远失去了率领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的机会。”苏指导后来全家去了加拿大。容志行也离队了,他是在北京被新西兰球员一脚踹在小腿上,用担架抬出足球场的。容志行是很内向的,不爱露感情。他当时躺在担架上,血隔着纱布往外渗。他举着拳头冲我们喊:“咬住牙,拼了!”这情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他红着眼圈,声儿都变了。他不甘心啊。我们拼了,玩了命,可是没拼出去。我们到底让新西兰给踹下来了。苏指导上飞机那天,我没去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走一步三回头。要是我去了,要是苏指导回头,我想,我不敢看他的眼睛。肯定很惨。
可是,我还有机会。曾雪麟来国家队挂帅,代替了苏永舜,我被留下来,当了国家队队长。这年我23岁。
(左树声是相对幸运的。尽管经历了两次失败,他却没有被淘汰,反而由此走上自己足球生涯的峰巅;这一届国家队是相对幸运的。她有着以往任何一届国家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机会:第23届奥运会预选赛,第9届亚洲杯锦标赛,第13届世界杯外围赛。这三次机会中只要能抓住一次,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夙愿便将在左树声和这一届国家队手中实现。而当时的国内各界均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对此不抱乐观态度的理由。于是,广大球迷再度欢欣鼓舞,拭目以待。)
这届国家队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团结向上。用我的话说,就是有那个气势。大伙儿对我们有个评价我认为很准确,就是:碰上强队不弱。比如我们在国内踢联邦德国曼海姆队、英国沃特福特队,在印度踢波兰队、阿根廷队,都是这样。不管输赢,输也输得不窝囊,输个明白。当然还有一句话,说我们碰上弱队不强。这话说得也对,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先不说它吧。
我们是抱着很大希望去踢奥运会预选赛的。当时分组很有利,四个队出线两个,泰国、香港都比我们弱。按一般情况看,应该我们出线。我们就是没想到比赛期间曼谷一个劲儿下大雨。先是在泥里踢,后来在水里踢,踢着踢着就乱了章法。对泰国队那场关键比赛,球都在水里漂起来了。泰国队本土作战,如鱼得水;我们就被动了,越踢越没样儿。结果输了,憋着一肚子气回了国。回来后,我看了一张报纸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天不助我》。我把这报纸拿给大伙儿看,大伙儿也说:可不是么,咱这叫运气不好。我们还收到好多来信,都是宽心丸。说老天作怪,怨不得运动员;说国家队新组建,打大比赛没经验;说这回输了别泄气,亚洲杯赛去拿个冠军就找补回来了。这些话让人觉得很热乎。你想,老百姓这么通情达理,球迷这么通情达理,我们往后不踢出个模样来,对得起谁呀?当然也有来信说,你们下回亚洲杯不拿个冠军,就别再回来了。这话大伙儿听着也不反感。本来么,老百姓养你这个国家队为嘛?是让你耍呀?不就是盼着你们为国争光么!
亚洲杯我们踢了,亚军,第二名。这是建国以来国家队最好的成绩。回来能有个交待了。可大伙儿没觉着痛快。冠军是沙特,沙特原来跟我们踢一场输一场,这回是冠军。回来总结,大伙儿心里就是这么一种矛盾状态。球迷们也是有褒有贬。只是有一点儿大家公认:这个队有进步,正在成熟,可以指望下一次踢出好成绩。现在该干的,就是把眼睛盯住13届世界杯外围赛,练。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训练自然有不少问题。而我们练得可够苦的。大伙儿不叫苦,心里都清楚,这恐怕是这届国家队最后一个机会了。再说,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可以出线两个队,我们是亚洲杯亚军队,希望非常大。
(第13届世界杯外围赛分组名单公布,中国、香港、澳门、文莱为一组。球迷们先是一阵庆幸:老天,这不是白给吗?继而感到了不满足:难道踢这样的队也值得一看?多数人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关心这几场比赛的结果,他们把眼光投向了更远处:中国队小组出线以后,将会与哪些对手相遇?
于是,当无线电波传来中国队同香港队在港以0:0握手言和的消息时,惊疑与不理解之声四起:平了?怎么跟香港队平了?居然跟香港队平了!)
说实话,跟香港队踢平,大伙儿心里比球迷还别扭。你知道,有时候两个队实力不好比,说这个强,那个弱,不好说。可香港队跟我们比,那是明显差一截子!大伙儿当时也没话,就一个念头:香港队,咱北京见!
这就说到了5.19。说到5.19,我就觉着是在说昨天。昨天的事有时候今天就忘了,可5.19,只要我活着,就决忘不了。
(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与香港足球队各自带着一平四胜的成绩易地北京再次交锋。是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出现了包括它本身在内的中国所有体育场从未有过的沸腾。这场比赛及其后发生的球迷骚乱,被称作519事件。作家理由、刘心武分别以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的形式对此作了详尽描述和剖析。不过分地说,这一事件以及这两位作家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将同时被载入我国足球运动史册。5.19之夜,就是左树声为国家队效力六年的终结。)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场球会输。天时、地利、人和让我们占全了。我想的不是能不能赢,而是赢多少。那场球我由右前卫改踢左边锋。因为在香港踢的时候,对方左前卫盯我很死,曾指导让我调一下位置,摆脱那个左前卫。曾指导说:“你争取15分钟之内破门,如果没得手,看我手势再改回右前卫。”我说:“行。”我相信不管我踢什么位置,这场球我们都能赢。开踢了,我一看,对方那个左前卫这回又调到右后卫上了,还是盯我!15分钟到了,我没破门。我往场外看,也看不见曾指导给手势。那个右后卫象影子一样贴住我,别扭透了。香港队任意球先得一分,李辉射门扳平,我们始终占优势。第35分钟,场外举起牌子,我一看,换我下场。往外走的时候,我抬头看见台上晃动的那条大标语:天津球迷进京助威。我突然挺不是滋味。运动员换下来调上去是常事,我过去从没觉得怎么样。那回就那么奇怪,不是滋味了。也许这就是预感?可是,当时要是有人打赌,我敢把脑袋压上,说:中国队赢!
下半场我就坐着看了。我们一直堵着香港队家门打,可就是不进球。这时候下雨了,我先是出汗,后来就一阵阵发冷。我上又不能上,坐又坐不住,干脆出了体育场。我在场外用耳朵听着动静。其实哪用听,那声音就往耳朵里灌。我凭声音知道我们一直压着半场,也知道我们一直没有破门。这时候我还不担心,根据净胜球,我们踢平了一样出线。我只是觉得不多灌几个不过瘾。突然不对头了,几万观众轰的一声,香港队进了!这是下半场开赛不到20分钟。我想,还有时间,还能捞回来,还能赢,这时候场里什么声音都有了:喊,吹喇叭,跺脚,唱国际歌,混成一片。我看着表,专等着那个声音,我们破门的声音。我想抽烟,没摸着;过了一会儿又摸,还没有—我根本没带。我就这么在雨地里站着,等着那个声音,一直到结束。结束的时候,场里一下子就没声了,从外头听好象那里头根本就没人。我知道,完了!
这就是我的5.19。这场球我踢了35分钟。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为国家队踢的最后35分钟。当年容志行下场,是用担架抬下去的,是英雄。我左树声下场,不明不白。整个国家队都不明不白。实力不足出不了线,条件不好出不了线;面对香港,实力强、条件好还出不了线。人家当然要问:你们得怎么着才能出线?!
国家队解散,曾指导辞职。那几天,国家队就象死了人,大伙儿不想说话,不想吃饭,不想喝水,不想睡觉。分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对曾雪麟,说句公道话,他算是把一切交给了足球。队员们老用一句话说他,就是“呕心沥血”。其实何止曾雪麟,哪一届教练,哪一届队员,包括我们在内谁没有尽了自己的努力?可归根到底,我们没有出线。你知道男人是轻易不哭的,舍不得那眼泪!可我在国家队这六年,亲眼看见了多少男人掉下眼泪。年维泗,李福宝,相恒庆,苏永舜,容志行,迟尚斌……这是些什么人?这些人一个个拿出来,全是梆梆硬的汉子。也许,他们要是早干别的,早就成了。可他们全选上了足球。中国的一代足球精英,就这样,一拨一拨的,涨潮似的,起来,下去,起来,下去。想想啊,真惨!现在轮到我们了,曾雪麟,我们。我们更惨。
我回家了,走出天津站不敢抬头。我老想着那条标语,天津球迷进京助威。我知道天津的球迷。国家队一踢国际比赛,天津球迷就骑着自行车呼啦呼啦往北京赶。二百多里地呵!看完球随便找个澡堂子一猫,忍一宿,第二天又是二百多里地。图嘛?盼着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呀!这时候,如果哪个球迷认出我,给我左树声俩大嘴巴,我决不还手。我十几天没出门,不见人,也不见球。我想从今往后再不踢球,没脸再往下踢了。
(可他还是又踢了。就在他坐在我面前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已就任天津队队长。球迷们依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他,他离不开足球、中国不能没有足球运动。5月19日之后,中国的足球运动,用一位行家的话说,已经“进入一个思考的时代”。同足球有关的观念、方法和管理体制,都在被思考之列。)
再过两年,我想找个少年队去当教练。我18岁的时候,沈福儒跟我说,我们不行了,得靠你们了。现在,我们也没行。我想把沈福儒的话再告诉我的队员。如果他们还不行,我就让他们把这话传下去。我们就这样,一拨一拨的、涨潮似的,下去,起来,下去,起来,中国足球总有行的那一天……
人没有下辈子。要是,人能有下辈子,我左树声,还踢球……
(你呀,左树声。你这个土城长大的孩子,你这个足球场上的坦克加推土机,你这个身经上百役负伤十几处哼也没哼一声的硬汉子,为什么说到最后,还是没有止住你几次要流出眼眶的泪水?
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的眼泪,真正男子汉的吝啬的眼泪。)常宽1968年生第16届世界流行歌曲节总指挥奖获得者
我的名片只能这么写:中国北京,常宽。我还没单位。要是去年我考上了高中,还能再加上:海淀区八一中学。我初中就是在那儿上的。可我没考上。所以就是:中国北京—下头空着。
上礼拜我开记者招待会,大部分记者都是问我在日本获奖的情况。但有一个记者就问:你对自己去年没考上高中怎么看?我说:我当时很难过。我真的很难过。差十几分。怎么说也白搭。
我不喜欢“待业青年”这个词。别扭。我没待过业。我头一次到外面唱歌是去年2月,为电影《九月》配插曲。那时候我初中还没毕业。我去吉林演出,上台之前和省音协的老师们聊天。我说:你们音协怎么只要老的不要小的?他们说:不是这样,年轻同志当然也吸收,比如你,我们就可以考虑。于是我一上台就对观众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吉林音协正考虑吸收我当会员。观众马上鼓掌。我又加了一句:我还没填表呢。好,掌声更响了。所以你看,我这个北京的常宽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吉林分会的会员。
我这个人属于爱幻想的。最早想当警察。那时候大伙儿全穿灰黑,就警察雪白。那时候我户口还在我妈妈下放的河南农村,可我想当北京的警察,北京车多。后来是骑兵,保尔·柯察金。我有个叔叔去内蒙了,我老跟他打听骑兵的事。接着是潜水员,麦克·哈里斯!我觉得麦克对我们这些男孩子的影响比保尔·柯察金要大。他不光是一种信念上的东西,还有科学和幻想。再后来是学画画,当画家。画了两年,有位画家在我画的马上面题辞:常宽学画,无师自通。可我又转了,学音乐。不学小提琴,小提琴要是能直着脖子拉我就学。我学钢琴、吉他,写词作曲。我认为我的才能在音乐上。
我写的第一首歌叫《走向生活》,那年我上初二,15岁。我这个人童年和少年结束得都比别人早,我急急忙忙地就走向生活了。我在日本获奖的是另一首—《奔向爱的怀抱》。一位日本记者问:你写下这样的歌,是否可以表明你已经有爱人了?我回答:象我们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大都在心目中为自己的爱人画了个轮廓。画了这个轮廓就能理解爱,不一定非得有一个特定的爱人。你们日本不是这样吗?他说:日本也是这样!
我考过音乐学院没考上,不过细想想也没什么。我是搞流行歌曲的,我们的音乐学院根本不开这个课,考进去也不对路子。我知道有人对流行歌曲有看法,好象不能登大雅之堂。光有看法没用,你捂上耳朵也挡不住它照样在那儿流行。是不是?这东西你还得研究它,发展它,提高它。
我参加过侯德建的花果山乐队,都属猴,挺来劲的。后来散了。王昆想让我去东方歌舞团,说房子都准备好了。后来管人事的没批。你看我挺不走运。可我心想:不批就不批吧,有你们后悔的时候!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信心。我有几个挺不错的哥们儿,大伙儿一块儿练。大冬天坐在草地上,一发声嘴里冒一股白气。我们说:嗬,瞧咱们1这气息程度,官震!云南声像公司一个人到家里来找我爸爸,让给推荐个人灌磁带,我爸爸正好不在家,我跟客人说:您看我怎么样?他说:你也会唱?我把吉他一挎说:您先听听再说。我刚唱了两首歌,他就说:行,就你了。马上签了合同。这就是我录的第一盒磁带。
我认为人还是得有个偶像。我就崇拜日本的谷村新司。我处处学他,把他当作追赶目标。我不光喜欢他写的歌,他的演唱风格,甚至包括他的外形。我晚上睡觉前照镜子,看自己挺瘦的,就说:老谷就这么瘦!其实我明白谷村新司未必就什么都好,但是我觉得你要崇拜什么人就得把他神圣化、偶像化,这样你才有动力有奔头。这回去日本参加比赛,我见到了谷村新司本人。我去看他排练,大厅里坐了十几个人。谷村新司坐在头一排正中,我在第二排他身后坐下。突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人一惊。接着那大鼓一下一下就象打着你的胸口,然后是各种乐器的合成从四面八方向你压来,让你透不过气。等着看谷村新司排练的人都退出去了,受不了那个刺激。我当时心里直犯恶心,想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战术。但我看谷村新司一动也不动地端坐着,我也硬挺着。乐声终于停止,谷村新司正式上台排练,台下只剩我一个人了。他唱了三支歌,唱得非常棒。我坐在台下想什么?你猜。我想:能亲眼看到谷村新司排练,是我这回的运气。如果下回再来日本,那老谷对不起,我就是跟你抗衡来了!
去日本前,妈妈说:这次咱们国家就你一个人被选上去参加比赛,你可是代表十亿中国人去的。我说:您别吓唬我。我谁也不代表,我就代表常宽。到了日本我也没觉得怎么样。演唱比赛在东京武道馆举行。进了比赛场,我还不大在乎。我跟自己说:行了常宽,今儿你也混到日本武道馆来了?那时候你骑个破自行车,军大衣外头挎着吉他,顶着西北风从海淀半夜三更往家赶,那模样可够惨的,呵?可等到一报我的名字,下一个演唱中国常宽,我那间休息室的门一开,外头灯光劈里啪啦一闪,我心里那么一股劲儿腾地就都上来了。我心说:常宽!你这么个小毛孩子算什么呀?中国中国中国啊!我往台上一站,真觉着后头有上亿人给我戳着似以的!
比赛委员会专门安排一位小姐负责我的衣着打扮,别的歌手们都是一去一套班子,我是单枪匹马。那位小姐很负责,老说我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应该如何如何。其实在家里让我穿什么我穿什么,根本无所谓的。可在那儿我就听不顺了,因为我真觉得有点儿代表中国似的。我容不得别人说我不好,说我不好就跟说中国不好差不多。我对那位小姐说:请你记住,我要是穿了什么衣服,什么衣服就是好衣服;我要是这样打扮,这种打扮就是好打扮。后来她真的不说不好了。我获奖的消息一公布,日本新闻界一哄而上地说我是当代歌星。回国之前,好几位日本朋友帮我联系买冰箱彩电,我都谢绝了。我花了100万日元买了一批乐器:电子鼓、电吉他什么的。这笔钱够买一堆彩电。不是都说我是当代歌星吗,歌星买乐器,艺术不分国界。你家用电器再好咱一样不要。咱堂堂中国来的歌星不给你们留话把!咱常宽代表中国。可说实话我们家还真没有彩电。
我现在很想出名,我爸爸妈妈不想出名,他们也是搞艺术的,搞了一辈子艺术,批了一辈子名利思想。我跟他们思想上有差距。可是出名凭什么?得凭真本事。说实话我眼下没多大本事。作了几首歌,灌了一盘带子,得了一个奖就算有本事啦?差不少呢。再多叫几声歌星也帮不上忙。而且现在歌星有多少?小伙子一开口女里女气也是歌星,我都腻歪。男孩子唱歌得有男孩子样儿,往那儿一站一唱起码得让人知道你是个男的,是吧?我的目标很明确,笼统地讲,就是要成为中国最好的。我是说在流行歌曲方面,我说的最好的不一定就是最受观众欢迎的。有些恰恰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家使劲鼓掌。有的观众可能对我们这个没兴趣。你没兴趣没关系,我培养你的兴趣。我希望后火提起这一段的时候说,有那么一个时候,流行歌曲,最好的就是我—常宽,我还希望以后如果有条件,我自己办个乐队,不是那种交响乐队,是滚石乐队。这个乐队也是中国最好的。能跟日本美国的抗衡,至少盖过香港。
我妈妈昨天晚上还跟我说,我不担心你事业上不努力,我担心的是你其他方面别出什么问题。我知道她是指张行出事说的。张行和我可以算是朋友,他到北京来过我家,他还演唱过我写的一首歌。他有才华,也有毛病。我听说他出事了心里挺不好受的。真的,一个人让自己的毛病断送了事业真让人不是滋味。我对妈妈说:您放心,我好事还忙不过来,没功夫考虑别的。到时候我给您娶回来一个仪表美加心灵美的贤惠媳妇,就平安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