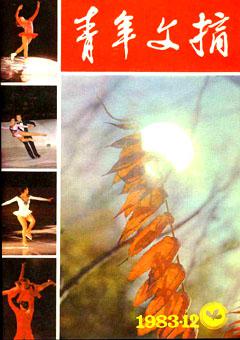艺术·村庄·理想
徐洁人
这也是农村新事一桩: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上海郊区新场镇举办了一个农民个人画展,二十四岁的农家姑娘的三百多张画,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农村生活风情,吸引着许多参观者。青年社员们流连在她的作品前,逢人就说:“她,是我们农民的骄傲,我们农民中也有文化人才。”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假小子?野小子?
一九六九年以前,在南汇县下沙公社沿江大队十三小队里,你是找不到这个叫康金梅的农家姑娘的。人们见到的只是一个赤着膊,穿着短裤衩的小“男”孩。
“谁有本事,就从这里跳下去。”小金梅指指桥下几米深的小河。男孩子们怔住了。
“哈,胆小鬼。”她纵身一跳,小河溅起浪花。她浮出水面喊道:“下来呀,胆小鬼。”
这个农家的顽童,除了头上两条羊角小辫、一双秀美的大眼睛,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女性外形特征,连一对眉毛也浓黑浓黑,是个十足的假小子。她从五岁开始就扑在玻璃窗上描摹哥哥画的穆桂英,花木兰,除了打架,还会画图。哪家孩子同她吵架,哪家门上就会被她画上一幅开玩笑的画。
其实,画画,金梅也要付出代价。此刻,妈妈正在骂她:“你给我坐下,给我纺纱!女孩子家,哪有象你这样野的,你再走,打断你的脚!”妈妈丢给她一把粗棉条,下田去了。
金梅等妈妈一转身,拿哥哥画的人头像,贴着窗户描起来,小脸上还挂着泪珠。
门咿呀一声,金梅直跳起来。妈妈回来了,她一看小丫头不纺纱,又在画什么图,赶过去一扯两半,吼道:“种田人画啥图!画图能当饭吃吗?给我割羊草去!”
金梅捡起扯碎的画,背了竹箩向田坂走去。一到田坂,她放下箩筐,在那张撕碎的图纸上又画起来,身后围了一群割羊草的小姑娘。这个要她画房子,那个要她画鸭子,七嘴八舌象一群小麻雀。到傍晚,草篓空空,妈妈又骂她。
金梅一气,躲在门角里面画了个妈妈打人的画。窸窸窣窣,被妈妈发现了,拖出来一看,看到自己上了图画,也禁不住笑了,叹口气说:“小金梅,我们种田人,不学手艺,怎么过活啊!”
小金梅从妈妈眯成缝的笑眼里看出,原来妈妈也是喜欢图画的,不然她又怎么对着自己的图画看了又看呢?
这小精灵看准了,就在妈妈怀里撒娇了:
“嗯,我喜欢画嘛。”当然,她也懂得,爸爸做木匠,妈妈种田,家里姐妹又多,生活的担子不轻啊。
一九七四年,画家江南春到惠南公社深入生活。康金梅挤在一群美术爱好者中间看他作画。江南春向他们讲解、示范,然后要他们每人画一张。
康金梅握笔凝思,开始画红旗。这本是她的拿手戏。前几年,家里的门上、墙上,到处是她画的红旗、红星、天安门。这会儿她蘸着红颜色,一笔一笔往纸上涂抹。不知怎么的,她忽然端起调色盆,朝纸上一泼,用大笔肆意挥洒起来。
“金梅,你干啥啊!”有人叫起来:
“不要紧,不要紧,让她画吧!”江南春看出了这个姑娘胆子大。他是理解的,人们常说,艺高才能胆大,反过来,也只有胆子大,将来才能取百家之长,闯出自己的路子来。
下一天,画下沙公社全景,有人提议上五层楼高的水塔。可是来到塔下,人们怯步了。金梅却利索地登上了铁梯。大家焦急地劝她不要上去,她却一下上了几十级。朝下一望,心里也有点慌了,索性仰起头朝上爬。耳边的风,天上的云,一切都在颤动着,就连这水塔,似乎也在风声中微微摆动,几个男青年终于也跟了上去。
画完《下沙全景》,下到地面,江南春说:“康金梅不是假小子,是个野小子。她要是认真学画,倒是可以画出来的。”他送给她《中国画图录》,还给了她两张宣纸,鼓励她好好学画。这可开了她的眼界:世上竟有这么好的画,有这么好的纸。
她把宣纸裁成小张,轻易不用。从那以后,她做起了买宣纸的梦,梦见她抱着一大捆宣纸回来,铺在地上,自己趴在上面画着大幅的画,又在上面打起滚来,变成了画中的一朵鲜花。
不久,村里来了献血队,康金梅知道,献血可以得到一笔营养费,正好买纸笔。她瞒着爹妈,报了名,穿上姐姐的宽大上衣,脖子里挂了一只装着石头的书包,凑满九十斤体重,献了血。瞒着家里,换回了一批纸笔颜料。
可是,她感到身子软软地,到河边淘米,蹲久了,站起来眼前一黑,连人带箩栽到河里去了。原来她贫血了。
这一年她高中毕业,正式务农了。夏天,张灯插秧。午夜收工过渠,她又晕倒在渠里,泡在水中谁也没有发现。醒过来时,皓月当空;颈边的流水,耳畔的蛙鼓,好一幅夜景。夜风吹得她浑身哆嗦,脑子里却想着回去画一幅美丽的夜景。
有搏斗,才有幸福
迟来的春天,终于催开了桃花。姐姐们给她滋补的营养品,到底换来了姑娘两颊的红晕。十九岁,康金梅终于发育成长了,还给了她少女的羞涩和魅力。男孩子们爱和她接近了,而她却仍然把心思用在画图上。
姐姐们开始为她操另一份心:
“金梅,阿福参军回来了,人倒生得端正,还是干部的儿子,将来要进社办厂的。”
“东头宅子里的德康人品蛮好。他们宅子里全是好人家。”
妹子睁大眼睛说:“阿姐,我不找对象,我还小哩!”
娘忍不住了,说:“十九岁还小吗?我们这点年纪早成家了。你今年一定要找对象,如果不找,我拿你的图画全烧光。”
金梅也火了,说:“啥人上门来相亲,我用棒打出去。”
金梅的画箱果然空了。从小到大画的五百多张画被妈妈烧了。她眼睛哭红了,两天未去出工,躺在床上不思茶饭。
妈妈还在唠叨:“你不找对象,再画,我再烧。”
金梅躺了两天,起来了,对妈妈说:“娘,我已经有对象了。”
“鬼丫头,谁相信!对象在哪里?”
“在部队里,过几天给你看照片。”
照片让金梅妈高兴了,她迫不及待地要见见亲家。金梅推三阻四,西洋镜就拆穿了。妈妈一生气,又要烧画了。
这一天,金梅真的领了一个小伙子来。大头方脸的小伙子,腼腼腆腆,一副毛脚女婿望丈母的样子。
妈妈乐了。叫金梅买排骨,买老酒,招待未来的新女婿。
小伙子还弄不懂比自己大的金梅老师今天为啥这样客气,大妈筷头上已送过来红烧大排,一边还笑盈盈地说:“阿弟,伲穷么是穷,日子倒过得蛮好。”
小伙子一杯酒喝下,脸红红,醉醺醺,话也多了:“是蛮好,蛮好。大妈,你真好。”
“你觉得大妈好么,多来来,伲金梅人是蛮好的。”
“好好。”小伙子答应着。金梅却暗暗好笑。她觉得他们都醉了。
饭后走出村口,小伙子喃喃地说:“金梅,你家大妈客气来。我要不是有了对象,一定认她做丈母娘。”
借过对象后,家中平静了。金梅觉得时光宝贵,作画更勤奋,半年中学了素描、水彩、油画,连田头休息也捧着速写本。
有人看不惯她这样迷画,一九七七年把她调到市郊大治河工地开河。金梅想不通:难道画图是为了我个人吗?党要我们劳动人民掌握文化,我画图难道错了吗?但是她只得去报到。
十一月的一个阴霾天,她同民工们坐上机帆船,开赴工地去。她坐在船头上,在膝头上写日记:“滚滚河水向东流,丹青学不成,理想在何方!不,霜打梅花花更红,金梅要学红梅,不怕困难,向艺术进军。”
工地上已造好一排排工房,推门进去,却是满地稻桩,禾稻收割不久,泥土湿烂。铺上青稻草,蒙上白被单,就算床铺。
金梅打开被包,几本书滚到地上,这是《门采尔素描》《罗丹艺术论》《西洋绘画概论》。她抱起这些书,不知放到哪里去才好。她感到胸口郁闷难平,把书在枕下一放,连衣裳也不脱,蜷缩到草铺里去了。
踏上工地,她参加了挑土。一天下来,肩被扁担磨破了,火辣辣地疼痛,坐在铺位上,难以入睡。
邻铺的大嫂酣声如雷。金梅皱着眉头侧过头去朝她看看。
咿,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模特儿吗?再看看前后左右,女民工们各种睡姿、各种神态,一个个好象都是为她摆布的,等待着她去画。这好象一线光亮漏进这潮湿气闷的工棚,把这里照耀得象一个素描室,正好让她慢画细描。
她从草铺上走下来,痴痴地凝视着她们,挥动着木炭笔,发出轻轻的擦纸声。此刻,她觉得这工棚不那么冷了,似乎还散发出泥土的芳香。
看,一位年轻的女民工提来了一桶热水,脱去上衣,露出长长的颈、圆浑的肩、高高的乳房。这美好的人体,立刻叫金梅联想到维纳斯。那美丽的体态,曾描绘过多少遍啊,唯独没有机会画真正的裸体。
她转过画笔贪婪地描起来,好象面对着的是一尊石膏像。
“喔唷,这小姑娘怎么画这个啦!”
一语惊破了沉寂,那位擦身的青年妇女早羞得满面红晕,慌忙用衬衣挡住了自己的胸脯。金梅也如梦初醒,悻悻然躺到自己的铺上,闭上眼,睡了。
其实,金梅眯缝着眼睛,在被窝里继续画她未完成的作业。她还要去投考师范学院艺术系啊!她不相信,农民就登不上艺术的殿堂。她不会忘记,当她前几次出现在落第者行列里时,几位大学生讥诮的眼光象电火花一样刺痛着自己的心灵。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工地上,她画完了带去的纸,又买来了手纸,画速写用了二三十斤。那是精疲力竭的农民,是把全部精力献给大治河的农民:他们皲裂的手,蓬乱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她意识到,严酷的年代刚刚过去,自己速写的,也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个年代在农民脸上留下的深深的烙印。
一种创作的意念在冲撞她。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凿大治河,但她要画劳动在大治河工地上的民工。收工以后,她久久地伫立在工地上。远远望去,她的身影好象立在河床旁的一尊雕像。
故乡呵,我将献给你
嵊泗岛海边上坐着个姑娘,凉鞋放在她的脚边。她正在画画,把普蓝、群青往画布上挤,一会儿又换了锌白。画布堆上了厚厚的颜料。她又用整支的颜料在画布上涂涂擦擦,使劲地划。画布弄得象一块被犁过的田,颜料高高低低,沟沟渠渠。
海涛在脚下岩石上激碰起飞溅的白浪,似乎想把岩石掀翻。难道海也在发怒吗?也象康金梅一样第五次考不取大学,被父母剥夺了画图的权利,逃到海边来,经历着一场心海的咆哮吗?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康金梅,觉得咆哮的大海才是自己的知音,写下它的汹涌波涛,才能吐出胸中的积郁。
她把画推远些看:海上一艘孤舟,在浪谷浪尖沉浮,这是自己啊,眼下的自己不正象那艘孤舟吗?
背后发出了惊叹声:“唷,真好看。”是一种清脆悦耳的童声。
三五个渔家孩子朝她笑着,她也笑了:“你们喜欢画图吗?”
“喜欢。”孩子们抢着回答。
“好,阿姨给你们画。”她就在海边认真地工作起来。
夕阳染得大海七彩瑰丽时,金梅已给每个孩子画了一张速写。他们成了朋友,她被孩子们拉着进入渔村,成了渔民小张夫妇的客人。晚餐桌上有牡蛎,有淡菜,有带鱼,还有烤虾。
消息传遍了渔村,渔民们拥到小张家,把金梅团团围住。
一位黑楞楞的渔家姑娘冲出人群,一把拉住金梅说:“走,今晚住到我家去。明天给我画一张。”
小张爱人一把将金梅拉回去:“不行,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我来说吧,今晚住小张嫂家,明天到凤英家去,后天么给我老头子画一张。”于是,又一片爽朗的笑声。
大海抚慰了金梅。勤劳的人民原来就是艺术的知音。这些天来,她紧锁的双眉舒展了。她在海边给这一家那一家画了几十张速写。渔民们你争我夺地把她当作上宾,她却在渔民们出工,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沐着海风,画了不少张海边的风景。
在她离开这座渔村时,十户渔家五户墙上贴着她的画。
告别嵊泗,她又去了嵊山、桐庐、西子湖。
她迷失在嵊山岛的丛林里,迷失在西子湖的波影山色中。
当林中的阳光洒落树丛,映出微妙的光色:当月光溶溶象轻纱披上海滩,她贪婪地凝视着,凝视着,思索着,思索着。
她理解了,为什么面向大自然的大师们,要从繁华的巴黎迁往巴比松森林。她内心升腾起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你听,空气中似乎还流荡着森林之曲;这夜景不正是象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所描写的?
她感到,城市的建筑,高大、巍峨,是直线条的美。那乡村、茅舍,则富于曲线的美。你看,每一棵树,每一丛草;弯弯的小河,微隆的土丘,无处不蕴含着曲线,深深吸引着她。
她记起了故乡,故乡的茅舍、土路、小河:那依门相望的老母,辛勤终年的老父。原谅他们吧!他们是曾经举过纱棒揍自己,他们是曾把画夹抛入小河,烧去过几百张心爱的童年之作,引起过自己内心的烦乱和暴怒,甚至要走上自灭之路,然而,这是故乡啊,这是亲人啊,他们不都是因为担心女儿走上歧途?和解吧,亲人啊!
她轻声哼起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中的“回家乡,回家乡……”歌声中两行热泪挂上了腮帮。
这一两个月来,她消瘦了,海风把她吹黑了,但她心绪宁静了,内心充实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更强烈了。
三天之后,她已倒在老泪纵横的母亲的怀抱里。
“金梅,娘再也不骂你了,你画吧,只要你不再逃走。”
“娘,金梅不走了。”她抬起泪眼,看见娘脸上凭添了许多皱纹,丝丝白发覆盖着她萎黄的面颊,眼圈儿也陷得更深了。
“娘,金梅不走了,啊,不走了。”
娘点点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父亲坐在门边的矮凳上,动情地拭了一下眼睛。
金梅冲过去,捧起一双树皮般粗糙的手,紧贴在自己脸上。
故乡,你宽宥了女儿,女儿又沉醉在你的胸怀里了。
从外面写生归来,金梅觉得,西子妩媚,瑶琳奇幻,富春江清澈,景色都很秀丽,但家乡的小桥、流水,村舍、茅屋、绿树、田野是另一种美。如果说贵妇人的雍容华贵,是一种浓艳的美,那么乡村少女的天然秀色,是一种淡淡的自然之美。
哦,故乡,你就是一位纯静、娟美的乡村少女,我愿意为你献出内心的全部色彩和韵律。
小别的故乡,使她觉得一草一木都那么亲切。大自然,这位天才的画师,给家乡创造的美的意境,使她迷醉了。
在那光色变幻中,宅旁的谷仓、草垛、牧场,胜过了莫奈笔下的《草堆》;屋后小河在晨光中升起的薄雾,隐约的船影,比法国著名画家笔下的《日出》更富于诗情画意。而家乡的人们呵,你们于我是多么的亲切,我将描绘你们。
她看到农妇抱着孩子,想到了珂勒惠支的《母与子》;她见母亲喂鸡,联想到米勒的《喂食》;她自己在水埠漂衣、洗菜,好象看到了杜米埃的《洗衣妇》;还有,那牵着小羊走过的社员,那佝偻着腰还不息劳作的老农,那驾驶铁牛的小伙子,谁曾描绘过你们啊?
我,我将把一生献给你们,象米勒说的那样,“我将生于农民,死于农民”,因为,我是农民,因为,我有一个可爱的家乡。
早晨,金梅站在村头;中午,她顶着烈日走向田野;傍晚,直到夜幕轻垂,她还踯躅在村头,宅前。她在仔细观察,记下家乡风景在一天中的光色变化。
创作开始了,《田园组画》诞生了。家乡的朝晖、暮霭、夜雨、晨雾、春耕、秋收,调子不同的作品排列在一起,使人感到画面上流动着音乐,而节奏又那么明快。站在画作之前,使人感到农村、田园、故乡在发出召唤,让人们去亲吻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亲人,去看看他们正经历着的三十多年来少有的巨大变革。
康金梅,这个农家姑娘,艰难曲折、默默无闻地画了十几年,画了几千张速写、素描、水彩、水粉、国画、油画,作品装了几箱子。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人发现了,才在下沙公社党委、新竹书画社的支持下,在市郊举办了上海建国以来第一个农民个人画展,她的才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她,却写下了这样的几句“我还将每天每天静静地涂抹,离开绘画,我将死去;我愿一辈子为农民描绘丹青,因为我是农民的女儿。”四月,康金梅通过考试,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美术研究室的绘画班;著名的画家给她上课,使她渐渐懂得,世上一切艺术都不应该是为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在自己的周围,有那么多人在挥动画笔建设精神文明。一种想法在萌动:赶上去,赶上去,投入这伟大的行列!她拿起画笔,坚定地走向画架……
(章颜青摘自1983年8月2日《文汇报》)
(插图:刘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