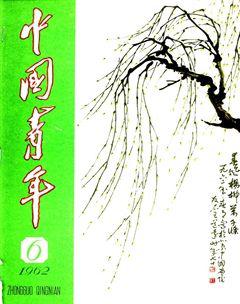乌毡帽
任大霖
我们家乡的农民都戴乌毡帽。这种帽的样子象一只倒放的圆盆,不过帽边是翻起的。有的读者可能想象不出乌毡帽的样子,如果看过《祝福》这个影片的人,就会知道这种帽是什么样子,因为影片中贺老六这些农民戴的正是乌毡帽。
解放以后,一些爱打扮的小伙子往往不戴乌毡帽,而改戴圆顶的干部帽;除了这些人以外,戴干部帽的大多是“脱产干部”。但也有少数例外,1959年我在红星公社参加劳动,我们的公社主任郑德炳同志——大家都叫他阿炳伯,就一直戴的是乌毡帽。
阿炳伯是当地的一个老模范,从1950年搞互助组开始,就一直是先进的旗帜;1953年入党后,曾担任过乡长。人民公社成立,他就被选为主任。当然是“脱产干部”,常常上县里、专区开会,但他一直戴着乌毡帽,从外表看,根本就是个普通的老农民。甚至,别的农民都换上新的乌毡帽了,而阿炳伯还是戴着那顶旧帽,乌毡都褪了颜色,发黄了,顶上还加着两块补丁,但他还是戴着它。
据说,乌毡帽是“冬暖夏凉”的,戴惯了,冬天可以保暖,夏天可以防晒。所以阿炳伯也象其他有些农民一样,整年戴着乌毡帽,即使在夏天,傍晚在小河里洗过澡,坐在土场上吃晚饭,身上赤着膊,面头上的乌毡帽却还是不取下来。看着这种“矛盾”的现象,我每每忍不住要笑,不过当地好些农民(尤其是老农民)都是这样的,看惯了也就不觉得怪了。
但是阿炳伯的乌毡帽似乎还有它特殊的作用。在它那翻起的帽边里,往往藏着一些小东西,一支铅笔头,半截香烟,或者一小卷纸,在纸上写着某某生产队出勤率多少、某某生产队有几块田没有施过追肥,等等。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他在帽边里摸呀摸的,我们就知道他要“摊出些情况”来了,这种“情况”有时比生产队的干部掌握得还深入、准确。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摸”来藏在乌毡帽里的。
有一次,托儿所的一个年轻保育员(是城里来落户的中学生)工作不安心,家长有些反映。阿炳伯和我一起在托儿所跟保育员们开会谈心。谈着谈着,阿炳伯又摸起帽边来,但这次却没有摸出什么“情况”来,而是(真想不到!)摸出一根缝衣针,针上还穿着线,他随手拉过旁边的一个孩子来,让他躺在自己膝盖上,就一针一针地给那孩子补起衣服来。把破洞补好,阿炳伯在线头上打个结,随手就把针插在乌毡帽上。那次谈心时间并不长,但据说效果挺不错,家长反映:托儿所的工作后来有了不少改进。
你瞧,阿炳伯的乌毡帽里藏着多少东西呵!不过从外面看,它只是一顶普通的、发了黄的旧毡帽。
有一天,阿炳伯的乌毡帽遗失了。
那是秋收的时候,阿炳伯在我们生产队检查工作,他从早到晚在田里忙着,割稻啊,打谷啊,挑担啊,一个人足可抵上两个劳动力。也许是因为收成太好了,阿炳伯又高兴又忙,等到晚上收工,在回家的路上,他摸摸头,发现头是光着的,乌毡帽遗失了。
他非常着急,马上要回去找。
我们同走着的几个人说:“算了吧,阿炳伯,你那顶毡帽也旧得不能再旧了,早就该换上顶新的了。连过去最穷的贫农也都换上新的毡帽了,你一个主任,还舍不得那顶破毡帽干吗!”
阿炳伯说:“话是说得不错。我也当然不是买不起一顶新帽。不过,旧的还照样能用,又去买新的干吗!我那顶毡帽虽然旧了,打过补丁,戴着还很舒服,只怕新买的还不及它舒服呢。不能丢,得找回来!”
我们就跟他一起回去找。找来找去,总算还好,在村外找到了。一个赶鹅的孩子检到了它,把它挂在竹竿上玩当他知道这是阿炳伯遗失的,连忙交还,说:
“我还当是人家丢掉不要的,准备把它放到稻草人的头上去吓唬麻雀呢!”
“丢掉不要?”阿炳伯说:“能戴的帽子干瞩要丢掉不要?吓唬麻雀也用得着这样好的东西?真是不懂事!”
他拍拍帽上的灰土,珍惜地把帽边翻好,就戴在头上。
路上,他告诉我们:“我活到五十岁了,一共只戴过两顶乌毡帽,连这顶在内。第一顶,是十二岁那年,我爹买给我的。那时我在地主家放牛,寒冬腊月,没有帽子,只好用块破布把头包着,西北风刮来,把我的两只耳朵冻得成了红萝卜似的,血一点点凝结在裂开的口上。我爹来看我,心疼得哭着回去,拚一拚,卖掉了一斗口粮,给我买了顶乌毡帽。起先戴着太大,后来越戴越小,一直戴到廿九岁,我结婚那年,帽上已经有十三四个补丁了。结婚的时候,买了第二顶乌毡帽,一直戴到今天,就是这一顶。”他拍拍头上的帽说。“是共过患难的老伙伴了。我总是舍不得丢掉它。解放后,我老婆劝我好几次:乌毡帽旧了,买顶新的吧!我对她说,旧就旧些吧,我又不是小伙子了,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干吗?你难道还叫我去另找对象吗?哈哈!”
阿炳伯抹抹胡子,爽朗地笑了,我们也笑了起来。
“我老婆见说说没用,就自作主张,在供销社给我买了顶新的乌毡帽,还是用她自己的钱买的。这乌毡帽好是好,又结实,又好看,比解放前的好得多,可是我戴着总觉得不舒服,又象太大,又象太小,又觉得太软,又觉得太硬,比一比,总不及原先的那顶舒服。这不能怪新帽,只能怪我的头,戴不惯新帽。过了两天,我见食堂里烧火的张生老头戴着顶风皮帽(据说还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东西),又不保暖,又不象样,就把新的乌毡帽给了他。我自己,还是戴这顶。”
阿炳伯给我们讲完了乌毡帽的经历,已经来到村里。他一眼看见几个年轻社员在迭稻蓬,迭得不大够格,便走过去动起手来,直到把稻蓬迭好才去洗脚吃饭。
县委通知阿炳伯,叫他到省里去开会。阿炳伯的妻子就给他买了一顶新的干部帽。“金水他爹,”她这样对阿炳伯说:“听我这一次,换上这顶新帽吧!你戴了破帽到省里去,首长要跟你握手,新闻记者说不定要给你啪照,知道的人说你节省,不知道的人还当你是穷。你自己无所谓,也得想想别给我们公社丢脸啊!”
阿炳伯虽然不大同意“金水他娘”的看法,但见她说得恳切,不便拒绝,便勉强戴上了新帽。
这是一顶用上好呢料制成的圆顶干部帽,阿炳伯一戴上它,立刻容光焕发,“年纪轻了十岁”,配上他那端正、纯朴的脸,短短的胡子,还颇有些神采。真是“人要衣装”,过去有谁会料想得到,这位放牛娃出身的老贫农,居然还是位相当漂亮的人物呢!
“ou,阿炳伯!”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在打招呼中间多了个“ou!”的声音。这包含着惊喜的成分,似乎是说:阿炳伯漂亮起来了,阿炳伯不平凡起来了,或者其他意思。
阿炳伯显得有些不安,他也许觉得这个“ou”的声音很不受用。他不喜欢人们用这样的眼光看他。总之,他希望自己跟别人完全一样,希望人们还是用随便的态度跟他说话,而不带有一点“不平凡”的色彩。在开会的时候,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常常用手摸摸耳朵。在劳动的时候,他干脆不戴帽子,光着头干活。
这天早上,阿炳伯出发去开会了。我跟他一起坐航船进城去。公社里好些干部都来送行。阿炳婶也来送他,同时为了监督他把新帽子戴去,因为她还不大放心,还在为公社的荣誉操心呢!
阿炳件戴着新帽子,红光满面地站在船头,向送行的人告别。他还特地对阿炳婶说:“放心回去吧,保证戴新帽就是。”
航船开了。阿炳伯坐下来,忽然从头上摘下新帽了,塞在包裹里;接着又在小包裹里翻出了他的旧乌毡帽,戴在头上。
立刻,阿炳伯又回复了旧模样,显得老了些,“士”了些,但是象原先一样的亲切、普通,也似乎更可亲近些,看着更舒服些。
阿炳伯换上帽子,也似乎觉得轻松多了,舒坦多了。他用手习惯地在乌毡帽上面摸了摸,取下来半截香烟,点着了,吸起来,一边说:“新帽子戴不惯,真没法。要是真的给我拍照,只好临时戴一戴,省得我老婆生气。”
初升的太阳从船蓬窗口照了进来,正照在他那顶旧的乌毡帽上,把褪了色的毡帽涂上一层金黄的光彩。
1962年初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