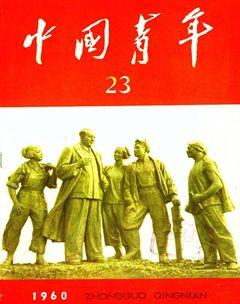北大荒的老红军
张开平
奔向党最需要的地方
一九五四年六月。铁道兵×师在东北正待向鹰厦线转移的前夕,王震司令员来到工地。他在工地上,与一批将要退伍的战士作了亲切的谈话。战士们要司令员介绍工作,他们要到党和国家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时候,王震同志就回忆起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指示要自力更生开垦南泥湾;解放新疆后又指示要自力更生开发祖国边疆,这样就产生了在北大荒屯垦安置退伍战士的主意。他想要一个好的带头干部……
“余友清,去北大荒 办农场怎么样?”这是在另一段工地上王震司令员见到余副师长的第一句话。
余副师长并不感到突然,在这以前他们谈论过采伐兴安岭的森林;开垦黑龙江省的荒地。在过去频繁、紧张的战争岁月中,他已习惯了这样接受上级所交给的任务。于是他毫不犹预地答道:“党需要我去,我马上就去!”
将军和蔼地笑着,说道:“考虑考虑,开荒种地这是一个艰苦的战斗岗位啊!”
余副师长斩贸钉截铁地答道:“早就考虑好了!”他一边说看,一边将手指头捏得咔咔直响,这是他在心情激动时的习惯动作。
到北大荒办农场,不是司令员刚才告诉他的吗?为什么他说早就考虑好了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余副师长看见许多老战友都调到国家经济建设岗位,上去了。他心想:打了几十年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这只是搬掉了前进路上的一块大石头。毛主席教导我门说,这只是万里长征中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任务是更加繁重、艰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很需要人,那自己也应该有调去搞经济工作的思想准备。当部队调到东北修铁路时,他深深为沉睡着的沃土痛惜,心想,能到东北开荒,种这样的地,才幸福呢!
司令员见余副师长的态度很坚决,于是高兴地说:“你先带一部分转业官兵去。你们是打头阵的,是去点火的,得搞个样子,搞得红红火火的才行,以后的发展很大,后来的要按你们的脚窝子走。你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搞些粮食。有了粮食,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好办了!……”
余副师长兴奋地说道:“保证全心全意地与退伍战士同甘共苦,把农场办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请首长放心吧!”
司令员满意地点了点头。二十多年的战斗友谊,使他们了解对方,就好象了解自己一样.他说:“余友清的脑袋上有几根头发我都知道!”因为余友清同志从来都是党需要他到那里,他就满腔热情地坚决地奔向那里;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总是全心全意、千方百计地想法克服,从没有过三心二意,畏难不前。
余友清同志原名周玉庭,出身在湖南省慈利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他在十六岁时就跟父亲一块,担负起一个成年人的繁重劳动。他当过长工,撑过船。父子俩虽然累断了腰杆,但是一家人仍然挣扎在饥饿上。边年军阀混战,抽丁派款,穷人活不下去了。一九三四年,贺龙、任弼时等同志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长征中,和红六军会合,声势浩大。穷苦人的救星来了,人们奔走相告。一个夜里,他父亲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说道:“玉庭,找自己人去吧!不把地主、恶霸、蒋介石打倒,不要回来!”他噙着眼泪告别了父亲,披了一条麻袋,撑着一只舴艋舟,沿着沣水,晓宿夜行。经过于辛万苦,越过白匪的层层封锁,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他参加红军时一字不识,领导要他到营里当管理员,他毫没犹豫地就去上任。战士们每天走一百二,他走一百八。不管雪山、草地,征途艰难,就凭爱同志的一片心,和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诚,杂粮、野菜管够同志们吃饱。他也经常将自己的一份口粮,分一半,悄悄地放在体弱、负伤的同志的挂包里……到延安后,为了加强战斗力量,又把他调到战斗连当排长。临走时,他坐在供应处的凳子上,不用账本,就凭记忆,把一年的伙食账一文不差地算了出来。会计惊得瞪大了眼睛,说:“余管理员,你记性真好啊!”这何尝只是记性好呢!?这是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一片忠诚啊!在几年的红军生活中,他多次请求入党,就在这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小的时候,曾被马踢过一次,因此,以后见马就让路。可是一九四0年部队到绥远后,骑兵要干部。于是领导派他去当骑兵团长。为了很快地掌握骑术,他请了一名骑术好的战士当老师。又选了一匹劣性的枣红马,每天从早练到晚。不知摔了多少次,留下了多少青、红的伤疤。摔下来,再爬上去……有一次把右胳膀摔脱了节,在床上躺了十几天,当接好的胳膀刚能转动,他又去练习。那匹有名的枣红马,终归被他驯服了。有一次战斗,他骑着这匹枣红马,带着一队骑兵,象团烈火似的,沿着长城追击日寇。连坐着六轮大汽车逃亡的日本鬼子也未幸免。
余友清同志就是这样接受和执行党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的。
在王震将军和他谈话的第二天,他就背了一个小被包,带了一个警卫员,同将军一道,到北大荒踏荒,选择建场地点来了。
丰饶的荒原伟大的理想
一九五四年十月,余副师长踏荒回来。我们五百四十多个转建官兵,在他的率领下,背着被包,扛着铁镐、铁锹、枪枝,向黑龙江省虎林县出发。
辽阔的草原展现在我们面前。左边,隐藏在灰色大气中的完达山脉,象条长龙似的,蜿蜒伸向遥远的白云深处;右边,在远远的蓝天与大地接触的地方,弯曲的穆棱河闪耀着波光;中间,是一马平川的草原,没有尽头。一群群野鹅鼓动着翅膀,咯咯咯……地在我们前后左右飞来扑去。
余副师长抓起一把黑士,一展手,满掌都是湿漉漉的黑水,象油一样。多肥的土啊!余副师长容光焕发,嘴唇在兴奋地颤动。走着,走着,他一扭头看见我,于是大声地说道:“张干事,叫文化教员指挥唱歌!”望着这荒凉但又丰饶的草原,谁不激动呢?于是我们以志愿军战歌的曲子,唱起了我们自己填的新词:
雄赳赳,气昂昂
奔向北大荒
为人民、为理想
建设新家乡。
毛泽东的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艰苦奋斗
翻天复地干一场。
正当我们唱得高兴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一只刚待飞起的野鹅,哀叫了一声,堕入草中.余副师长提着枪,赶过去,抢起了野鹅,哈哈地笑着:“乖乖!好肥的家伙,今天我们又该打牙祭了。”
余副师长的枪法在部队也是鼎鼎有名的。据说,有一次和日本鬼子遭遇了,他发现鬼子有个指挥官正举着望远镜,向他们隐藏的灌木丛中了望。他不慌不忙地举起了“三八”大盖“嘎”的一枪,敌人指挥官应声倒地。等到打扫战场,检回了那副望远镜,只见子弹不偏不歪,正好从右边镜筒里射了进去。
傍晚,来到一处漫岗坡前,余副师长说道;“到家啦!这就是三大队的队部,以后的分场部!”于是我们卸下了被包,铲去了草皮,撑起了帐篷。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已点燃了一堆堆的篝火,烤着余副师长打的野味。
围着篝火,我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听着余副师长谈着农场的建设规划。他挥着手臂,热情洋益地说着:那里种小麦,那里种水稻,那里盖学校和医院……。他叉谈到学习宝泉岭九三、赵光等军垦农场
的经验……。面对着这片野兽纵横的荒原,他并不因将要碰到的各种困难感到丝毫的畏惧。他对党的事业的满腔热情和这种坚强的意志,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余副师长讲完,停了停,又说:“你们都是建设者,是主人,你们谈谈农场该咋个搞?”于是我们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东西都说了出来。他乐呵呵地听着,点着头,说:“对头,对头。只要是好东西,这里都应该有,北大荒地盘大,装得下,装得下……”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营建。北大荒的树条子、鸟拉草遍地皆是,不几天的工夫我们就盖起了十几座窝棚和适于过冬的坑道式的地窝子。
八五0农场的第一座房子盖起来了。余副师长叫我选了一块上好的黄婆萝木,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0部农场”。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战士们敲着脸盆、鸣着鞭炮,将这块牌子挂上了还散发着松脂清香的场部大门。
余副师长成为了我们的场长。他无限深情地说道:“北大荒今天只有这样一块牌子,以后将会有更多这样的牌子挂起来的!……”
向地球开战的第一个回合
五月,大地解冻。我们用自制的农具迎接了建场的第一个春天。这些农具是用废铁和炮弹头打制的。余场长第一次来虎林踏荒时,在虎头(注)的山洞里发现了许多日寇在溃败时未来得及消毁的大炮弹;部队来虎林后,他就率领着一个中队,从倒坍的钢筋水泥的洞子里把炮弹挖了出来。将卸下的炮弹头,仿照着南泥湾开荒时的工具,打制了一万二千余件农具。我们就利用这些工具,向沉睡了千万年的沃土一寸、一尺地夺取着阵地。
为了多开荒,我们又向当地农业社借了一部份双轮一铧犁。有一天,我们选了十八匹体壮骠肥的骡子开始了试耕。生荒地,草皮厚,最糟的是:有些低洼地,还积着一片片冰水,牲口在里面提不起腿,一步一跤。咋办呢?有的战士提出:用人来拉犁。余场长感到这个办法很好,但作业的人要艰苦些。这几乎成了惯例,越是艰苦的事,他越要走到前头。于是他派人找了几根粗绳子,选了十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把裤腿一卷,说了声“走!”一步就跳到泥浆里。在塞冷刺骨的冰水里和战士一起,拉起了犁杖。
头一年,就用人拉犁和锄头开出了九万三千多亩荒地。
就在开荒战斗的同时,一场在当年的生荒地上能不能播种的斗争在激烈地展开……
在一次场党委扩大会议上,余场长谦虚地向新来的农艺师问道:“你说我们先种些什么好呢?”
农艺师眉毛一扬,吃惊地回问了一句:“今年就要播种?”
“是啊!今年不播种,开出这么多地干什么?”余场长不解地反问了一句。
农艺师有些茫然,答道:“按照农业科学来说,在当年的新开地上是不能播种的!”
“那什么时候才能播种呢?”余场长急迫地问着。
“最好是休闲上一、二年。”
“什么?一、二年?”余场长唰地一声站了起来,脸账得红红的,半晌才说道:“国家需要粮食才派我们到北大荒来,不播种我们拿什么交给国家?难道说,这一、二年还要国家拿粮食把我们养着?……”
农艺师感到委屈,场长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解释地说道:“当年开的荒,又没耙过,土地板结,草根也没腐烂,种子播下去了,也会被草吃掉,到头来建种子都收不回来……”
余场长斩钉截铁地说:“能长草,就能长粮食!草能吃庄稼,庄稼就不能吃草?草长起来就锄草,我们这些人连草都斗不过?!”
农艺师感到余场长不理解农业科学的特性,于是为难地说:“就不谈农业科学,拿目前本地的习惯来说,也是耍隔一、二年的。”
“这习惯不好,我看可以改变”
“我是不同意播种的,我是这里唯一的技术人,我要在技术方面对国家负责!”农艺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国家需要粮食,能拿出粮食才是对国家负责。我同意播种!”余场长也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当天的会议上,余场长提议暂时不要作决议,请大家考虑一下。散会后,他没有吃饭,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低头寻思。他耳边又响起了来北大荒前王震司令员的指示:“……你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搞些粮食,有粮食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好办了……”他又想起了党提出的建场方针是边生产、边建设。绝不能等建设好了再生产。播种,一定要播种!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合乎党的方针的。但是,播什么作物,怎么个播法呢?他自己也感到没有经验。找群众商量去!当天晚上他赶到虎林县政府,找到了县农业科长。他俩一齐拜访了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许老大爷。
许老大爷二十多岁就到了虎林,他的胡子是北大荒的霜风染出的。他盘腿坐在暖炕上说道:“早些年我们闯关东的时候,都是当年播种。既然是逃荒,谁还有多少粮食呢?如果等一、二年才下种,咱们的骨头早就敲得邦邦响了!”他吧哒了一下烟嘴,又说:“当然,生荒地的庄稼不如熟地壮实。解放以后,生活提高了,家家户户手头都有了余粮。北大荒人少地多,熟地都侍弄不过来,谁还去搞生荒地呢?朝代不同啦,这老习惯也就不兴了!”
余场长听了非常高兴,在许老大爷的耳边大声地说道:“老大爷,朝代虽然不同了,闯关东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可不能忘哦!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过去有用的经验呢!”
许老大爷咧着嘴笑着,不住地点着头。
“老大爷,你说生荒地种什么好?”
许老大爷想了想,说道:“种大豆保收,有七、八成把握!”
“草能不能把庄稼吃啦?”余场长又问了一句。
“这就看人勤不勤啦!人勤苗旺,人懒草肥。另外,种子也要得劲,我看‘满仓金就差不离!”许老大爷说着从炕头上的藤篮中抓了一把橙黄、闪亮的大豆种。
“种小麦呢?”余场长接过了豆种,问着。
“小麦可没种过,那阵子咱也吃不上小麦啊!”
余场长想了想,又问道:“咱们今年试试看,请你当老师,行不行呀?”
许老大爷捋着胡子,笑嘿嘿地说:“不嫌我老吗?”
余场长爽朗地笑了:“人老是一宝哇!”
第二天,余场长在场党委会上汇报了访问经过。委员们一致同意,作出了当年播种大豆的决议,并在宝东二大队划了一块地试种小麦。
新开地上浮起了星星点点的绿色。可是杂草却长得更快,不几天的工夫就封垅了,把嫩苗压在下面。余场长带着战士们抢锄。月黑天,战士们才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收工回家。他们提出:杂草锄不尽,决不收兵!
小麦飘起了绿色的带子。大豆的枝叶迎着阳光向着周围舒展,把重新露头的杂草压了下去。于是余场长又带着战士们忙着追肥上粪。
向地球开战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慷慨的黑土给与了勤劳者以丰收的喜悦。当年的大豆平均公顷产量一千二百八十公斤;小麦平均公顷产量一千四百五十公斤。
坚决不当伸手派
一九五六年,中央成立农垦部,任命王震上将为部长。同年,铁道兵农垦局在密山成立。王震部长给余场长来信说:老母鹅该下蛋了。要以八五0农场为基础,在密山、虎林、饶河、宝清四个县扩建六个总场。并要余场长立即进京开会。余场长临走时向业务部门交代,要赶快编制扩场计划。
余场长开会回来后,在审查扩场计划。他拿起了财务计划一看,、在收入的总计下是一个很短的数字,但在支出的总计下却写着很长一串数字。这下子他火了,大声地说道:“这超支的数字向谁要?向上级要?上级又没栽摇钱树。自己不想法,动辄伸手,我就看不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北大荒遍地是宝,就怕懒人不弯腰!……”于是他主张组织人上山伐木,为扩场筹积资金。
就在三九、四九棒打不走的严塞里,余场长带着我们七个人到完达山找伐木地点。我们坐着四匹马拉的雪爬犁在凛冽的风雪中走了一天。到达完达山夜已深了。我们找了一棵大树,用雨布撑了一个天棚,接住大树上偶而被风吹落的霜雪。
我们用拾来的乾柴架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拿出了陈得象树皮一样多皱的油饼,在火上燎了燎,就啃嚼起来。
起风了!头上响起了树涛声,一股股的塞气向我们袭来。显然余场长的风湿性关节炎又发作了。他把膝盖靠近火头,用劲地揉着。我不禁为他的身体担心,说道:“余场长,你应该去休养才对,长期这么下去还行吗?”他笑了笑,往火上加了几根乾柴,答道:“咋个不行?!老毛病了,治不治都一样,关节炎又死不了人!”
警卫员王永富同志嘟着嘴说:“副师长,你为革命流血、挨饿,受累几十年了,你也不到城市去,偏偏要到这荒原来!”
余场长怔了一下,轻轻地问道:“你说什么?都往城市跑,这北大荒让谁来建设呢?”
“我是说现在革命胜利了,城市条件又好,你身体又有病,讲条件,论需要,你都应该去。城市不也是搞的社会主义建设么?!……”显然王永富还没有被说服。
余场长知道小王有个倔脾气,只要道理没讲通,不管你是谁,他都不认输。于是耐心地说:“当然,城市的条件是要好得多,城市搞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但如果都往条件好的地方跑,谁去建设条件差的地方呢?条件差的地方岂不是越来越落后?哪么,又怎能把我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呢。就是因为北大荒条件差,艰苦些,党才派我们来。我们正是为着克服困难来的。只要我们发愤图强,我看要不到几年,北大荒会变得比一般的城市还要好!小王!我们的建设事业还仅仅是开始,可泄不得气呵!千万不能把艰苦奋斗忘了……”
王永富的头低了下来,说道:“现在的艰苦奋斗应该让我们青年人包下来,象你这样的老干部,应该……”
余场长马上接着说:“当然,你这种想法很好,如果青年人都这么想,这么做,那共产主义来得就更快了。你说,你们年青人都有这种志气,难道我们这些多受了几年党的教育的人,不要有这种志气吗?”余场长停了停,又说:“现在这里又不打仗了,你也不要老跟着我,学技术去吧!想把工作搞好,不懂技术是不行的!”
余场长这语切情长的教导,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到了下半夜,我被严寒冻醒,感到两脚发麻,背上好象背了块冰似的,鹅皮疙瘩一层压一层。这时,我看见余场长在草料袋上也不断在折腾着。他索性坐了起来,把火加旺了,把袋子向火边移了移,然后用手撑着头,又闭上了眼睛。这时我激动地想起了余场长战斗的一生……在我们伟大的党的培养下,我们革命队伍中,不知有多少这样坚贞不屈的战士呵!他们,以斗争为幸福,把为革命而吃苦当乐事,从他们光辉的形象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的光荣、伟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厚力量。
第二天拂晓,余场长就带着我们在齐腰深的雪上爬着、滚着,踩过了一处又一处密林。沿着我们定过的道路,一辆辆雪爬犁,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急需的木材运了下来,保证了扩场资金的需要。
从山上回来后,王永富同志就去学开拖拉机。他现在已担负着总场修配厂车间主任的工作。
英雄本色青春长在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北大荒正经历着翻天复地的变化。
篝火在日夜燃烧;拖拉机在田间昼夜轰鸣;熟地在成万顷扩展;城镇一个接着一个涌现……。
成千成万的有志青年,打着支援边疆建设的红旗,扛着被包、来这里安家落户。
余场长以一个老北大荒人的身份,热情地接待着这些有为的青年。他经常竖着大拇指说:“好样的,毛主席的好儿女,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如果再晚来上几年,就当不.上北大荒人了……。”
一九五九年,中央农垦部确定以八五O农场作为全国国营农场高度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的试点单位。国家以第一流的机械装备着农场。笨重的体力劳动正逐步由机械代替。一九五九年农场的机械化程度已达到百分之八十点一。
八五Ο农场目前有五个以农业为主的分场、两个大型畜牧场、一个森林、煤矿场,拥有六十二万亩耕地。在云雾浮沉的云山脚下,已筑成了一座蓄水四千万方的人工湖。湖堤外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麦田、豆地。云山畜牧场座落在湖旁的山坡上。在嫩草萋萋的坡上坡下,散落着成群的猪、鹅、牛、羊。在土地没有定型的情况下,农场五年来共为国家生产了三万八千余吨粮食,上交了大批的肉类和鲜蛋。
总场所在地——西岗,在我们来时只有几座日寇关东军留下的残塌的军营,现在却是新房栉比。一座灰色的四层办公大楼,已在绿林中耸立起来。这座楼用的青砖,大部份是余场长带着机关干部从日寇军营的房基中挖出来的。在大楼周围的密林里,隐藏着修配、制材、面粉、榨油……等十四种工厂。
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的文化福利事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分场、生产队都设有供销商店、小学校、托儿所和幼儿园。商店里不仅供应一般的日常用品,而且还可买到农场自制的糖果、糕点、果酒和汽水。总场并设有一座普通中学、一座中专技校、一座三层楼的医院……。
变化是太大了,古老的荒原,迈着巨人的步伐,一下子就越过了几个世纪。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党领导下的北大荒人辛勤劳动的结晶,这里也包含着我们老场长的一份艰辛劳动啊!
在辛勤的工作中,余场长的风湿性关节炎日益严重,但是他在人面前却从不表露自己的病痛,他生怕同志们由于好心的照顾,而给他带来失去工作的痛苦。
去年,王震部长来牡丹江垦区视察,见余场长的病已严重,于是向场党委提出,要调余场长到南方休弄。余场长听说后,当天夜里就急匆匆地跑到王震部长的房里。他将上身俯在桌子上,把手指头捏得咔咔直响,只不吭声。
部长奇怪地看着他,问道:“嘿!出了什么大事了?”
余场长两眼望着地板,半晌才说:“听说要我离开北大荒?”
“哦!是这个事,我也听说了。有意见吗?”部长有趣地望着他说。
“有意见。这又为了什么?”余场长直挺挺地问。“说实在的,你的身体……”部长和蔼地打量着这位老战士。
“首长放心,我还行!”他陡然地站起来,走了几步,恨不得找到一块三百斤的大石头,当场举起来。
部长说:“你跟你们的党委书记商量一下吧!”
余场长大声地说:“什么事我都跟他商量,都喜欢听他的,这件事我可要狠狠跟他‘斗争。”
部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热烈。对这个浑身热爱北大荒的老战士,部长只有屈服,他能说些什么呢?
王震部长对余场长的身体很不放心,写信叫他到北京治疗,结果被余场长婉言谢绝了。接着部长又来了一封叫他进京开会的电报。当余场长探知,这仍是部长的深情关怀以后,就去央求党委书记:“张书记,代我说说罢,现在人手少、事情多,农场还没建设好,工作需要我,我更需要工作,我吃不下消闲饭……就是休养,农场的条件不是就蛮好嘛?……”
部长和农场党委体谅了余场长的心情,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却严格地规定了:在农场休养的期间,只准动眼、动嘴,不准动手、动脚。
有天上午,我们正在四层大楼门前挖坑,准备栽树。余场长来了,后面跟着一辆满载着青松的马车。我心想:余场长怎么又出来了?……于是我大声地问道:“余场长,你不是答应休养了吗?为什么……”没等说完,他就满不高兴地说:“休养干啥?大事不能做,干点杂活还不行吗?”一会他又笑呵呵地对我们说:“这是我从大山里拉来的好树苗,谁要是栽死了,我可是不依的。这个树好长,今年先栽它,明年就栽果树,以后工作时白渴了,一出门摘两个吃吃,那才得劲呢!”接着,他又靠着马车,发着树苗。然后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块去栽树。
老场长他并没有休养。同过去一样,哪几最艰苦,哪儿最需要,他就会在那儿出现……。
大楼门前,余场长栽的那棵青松,已生气勃勃地长了起来。清晨,当我推开窗子,一看见那棵沐浴在朝霞中的青松时,我就会想起余场长,想起了他经常教育我们的两句话:“党的话是真经,听了手巧心灵,照做就会胜利!”“群众智慧赛神仙、依靠群众法无边。”他战斗的一生都是遵循着这两句话在做。时间虽然把地推向了老年,可是他的一颗红心却永远年青,忠于革命,忠于党,就象青松一样,不畏艰苦,不是风霜,在哪里都一样显示着充沛的青春活力。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本色!我时常这样想:每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人,都应该象余友清同志那样去工作,去生活!
注:“虎头”是虎林县的一个区,税名“友好”。紧靠乌苏里江,和苏联的伊马城隔江相望。日寇曾把虎头作为侵略苏联的桥头堡,在虎头遍做工事,设炮台。日本投降后,此地到处都是军器的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