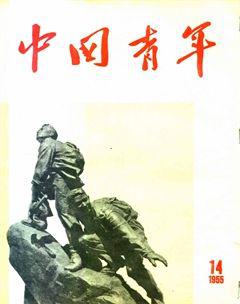双铃马蹄表
陆石 文达
“五一节动手”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只差三分钟就到十二点的时候,局长把顾群找去了。他进了局长的亦公室,看出局长把桌上的文件都收拾好了,但在那块放着绿色绒布的玻璃板上,却孤零零地留着一封信。局长察觉了顾群注意的目光,说道:
“看到了吗,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一个麻烦的问题,一定要在五一节前解决。详细研究研究吧。这是一位红领巾一小时前在西大街马路上拣到的,他交给了他的辅导员,辅导员便立刻送来了。信封原来就没有封。”
顾群没有立刻去拿那封信,他从局长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正伸手去拿那封信时,下班的铃声铛啷啷地直响了起来。局长一边锁好抽屉与文件柜,一边对顾群说:
“你把信先拿去,吃过饭立刻就来。”顾群把信拿在手中,看了一下信封的正面,又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抽出信纸对局长说道:
“您先去吧。我在您这屋里呆一会。”局长出去后,顾群把办公室的门窗都关了起来,免得嘈杂声响传进屋子来。他拿着信纸坐到靠墙的沙发上。
这是一封没有署名的密信,信纸是从三十二开的横格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
“大力兄并转赵金城及平兄:四月王日宴会时,兄等在钓鱼台商量的事,已蒙上峰批准,并指定动手时间,一定要在五一节,因少数民族代表团这时就住在交际处,兄等的汽车也会停在五一大会场附近。至于那东西,将以妥善方法送赵兄处。上峰祝兄等旗开得胜,弟即准备为兄等请奖。此信阅后即毁,免留平据。知名不具。”
顾群静静地把信看来看去,一字一句地默吟,一笔一划地推敲。他又把信封拿起来翻来覆去地考校。这是一个制得很坏的航空信封,左上角印着一架飞机,两只翅膀不大对称。信封上用钢笔写着:“交际处张大力同志收”几个字。
开门声,把顾群从沉思中惊醒过来,通讯员进来放了两个热馒头在桌上便立刻出去了。他一看表,已是十二点三十六分了。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便听见局长在他的身后笑着说道:
“趁热吃点吧,馒头里夹着酱牛肉,挺香的。不要太紧张了。”
“不是我紧张,时间太宝贵啦!”顾群回过身来辩解似地微笑着说。
“是呀,事情是够紧的。把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算进去,一共只剩下三十五个钟头。不过,我们总来得及亦完它的。”局长说完后就把顾群放在桌上的信件拿过来将信封和信纸并排摆在玻璃板上,习惯地皱了一下鼻梁,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坐在桌前仔细地看起来。他尽量不去注意顾群,好让他安静地吃饭。当顾群掏出手绢擦嘴角的时候,局长问道:
“你看出了什么问题吗?”
“问题不太简单。”顾群站在局长的侧面,指南信纸说道:“这封信不像是一个人写成的。”
局长仰靠到椅背上去,抬起头来,他那本来是皱着的额头展开了,两道细长的黑眉尖立刻平平地伸向苍白的鬓边,嘴角露出笑纹,眼睛里闪着愉快的光彩,透过浅度近视镜片,望着这个细长身材的年青人。意思似说:“开始得很好。”顾群受到上级的鼓舞,一双黑亮黑亮的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那张绛红绛红的脸,被射在玻璃板上的阳光反照着,露出一种沉静而愉快的表情。他继续说道:
“你看,信上的字写得这么恭整,可又显得很幼稚。从字迹上看,这信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成年人写的;但是,信的文词却很通顺,标点符合用得也准确。末尾这个凭据的“凭”字写作了平等的‘平字,这是用的简笔字,并不是写了别字。要是依照这些现象来判定的话,起稿的人倒是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了。很明显,这封信是一个人先写好了草稿,另一个人照着抄下来的。参与这事的人起码是两个。”他说完后,探询地望着局长。
“你看情况靠得住吗?”
“有两种可能。”顾群答道:“也许完全是事实。也有可能是挟嫌陷害。”
“当然,按一般情况来分析,这完全是对的。”局长把那封信拿起来,在手中抖动了一下,说:“但对这封信却是例外。在这样一个时机,写这样一封信,而且丢落在马路上,不会是没有原因的,要么是确有其事,要么是丢信的人别有用心。”
顾群听着局长的话,心里一下亮堂了。“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他想。局长像是猜中了他的心思似的,对他说道:
“看样子,你已经找到钥匙了。”局长按着顾群的肩膀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着,“但这只是好的开始,要打开那间隐藏着敌人的黑屋子,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敌人是很狡猾的呢。”
“还不知这回是什么花样,这些家伙很毒辣。”顾群把信纸照原样叠好装进信封里说。
“他们要在五一节动手呢。”局长特别强调:“五一节”这几个字。然后,直望着顾群的脸,好像是要从他眼睛里看出他心里想法似的。
“咱们不会叫他们误期的。”顾群幽默地但是很有把握地说。
局长轻轻地笑出声来,说:“好吧,现在咱们来弄个计划吧。”
互相矛盾的情况
顾群从拣信的少先队员的学校褒出来的时候,感到没有多少收获,但也肯定了原先的估计:这封信是从马路上拣来的,这情况没有问题。至于更多情况,少先队员和他的辅导员就无从提供了。少先队员只记得他刚从胡同转到马路上,就在胡同出口旁看见了这封信。他拿了信举起来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就拿回学校交给了辅导员。辅导员又分析了一下,说马路上人不少,却没有人踏上它,可见这信丢失时间是不久的。顾群和他们道别之后,就驾着汽车,按照计划急驶向“钓鱼台”附近的解放餐厅。这一带他是非常熟悉的。他把汽车停在一个树林子外面“解放餐厅”的门旁,迳直向经理室走去。在那里耽搁十分钟,他查明了:四月五日晚上某某机关曾在这里举行过宴会,到的客人有三百多,司机们全都在紧靠树林子的俱乐部里休息。他从经理室出来后,一个招待员领他到俱乐部看了一下,就出了俱乐部的后门。他迎着河里吹来的凉风,顺着树林中的一条沙石小道,向河沿走去。出了树林子,便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跨过马路就到河边,在河边上孤孤地长着一棵大垂杨,从树根起伸出一块可以容纳十人坐的大石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钓鱼台”。紧挨着这“钓鱼台“的斜坡上,长着一些灌木丛。顾群走到那石墩子的边沿坐了下来,一低头就看见那垂杨的枝影在清澈的河水中动颤着。他试验着扭回头来往周围看了一遍,除了对岸以外,背面的岸上什么也看不见。虽然有一条路,可是很少行人。这地方确实很幽僻。难道真是有人在这个地方商量破坏阴谋的?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个本子,很快在那上面书了一张地形草图,便离开了这个幽静的地方。
现在,顾群已经坐在交际处的接待室里了。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堆档案卷宗,但他的眼睛却望着窗外的槐树出神。槐树的嫩叶在夕阳里轻轻地摆动着。多么美好的天气!
顾群从机关里出来后,时间花费不少,跑了几个地方,找了不少的人谈话,也看了不少材料,可是仍是没有十足可靠的依据来作判断:那个阴险恶毒的敌人就是这三个受信的人呢,还是他们被人陷害了呢?据交际处的莫同志说,交际处所属的人员中确有三个司机与三个受信人姓名类似。本处有一个司机叫做张德理,不叫张大力;第五招待所的有一个叫赵建成,不叫赵金城;一所有个全处唯一姓平的,叫平小海。这些人的姓名是音同字不同呢?还是根本就不是呢?这也是问题。顾群多少有点困惑了。
莫同志进来了,又拿来一大捆顾群要的档案材料,足足有十多斤。接着是服务员送进一份饭菜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顾群一点都不觉着饿,不过他还是对他们连声称谢。等他们一离开,他就动手翻材料。他打算从这些材料中试着找出写信者的笔迹来,他一份一份地仔细地校对着,一个多钟头过去了,但是毫无结果。他把材料推在一边,拿起一个馒头来,又从暖瓶里倒了一杯热开水,一面吃着,一面看着窗外的槐树。
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对这三个受信人的了解,无论从材料中看,或者从认识他们的群众的口头反映,得到的都是互相矛盾的两种情况:有人确是看见张德理和赵建成,甚至还有平小海几个人,在四月五日那天去了“钓鱼台”。可是又有人证明:这四个人中张和赵两个根本不认识。并且说张德理为人很老实,除喜欢养金鱼之外没有嗜好。赵建成呢,沉默寡言,不爱交朋友。从他们的材料里看来赵建成历史复杂,给国民党的机关开过车;但解放以后表现积极,已经创造了九万公里安全行车的纪录,技术好。张德理是两代司机,历史清楚;但在日本人的车行开过车,还认识张得贵——这是个失踪的反革命分子,据说解放以后还见过面,为什么见面?不知道。另外一个是平小海,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刚出师不久;虽然年纪不大,但他的经历表上却填满了流浪生活的记录,他出生在杭州,父母早就没了。他在上海擦过皮鞋,在天津捡过煤渣,在武汉当过“堂倌”,解放以后才学开汽车,去年才从北京来本市。
情况就是这些,顾群作了几种正面可能性的设想。都被另外几种反面的事实推翻了。在他脑子里有几条错综交织着的线,逐渐把他引导向最初设想的那一点,他决心去寻找写信人的线索。但是首先要和受信的人见见面。他立刻和局长打了个电话,这个要求被批准了。
受信的人
“张德理同志,这是市府交通科的顾同志,来了解五一节汽车情况的。”
顾群由于莫同志的介绍,下午六时,认识了张德理。张德理正在检修他的车子,顾群马上就帮他上煞盒、接电路,又帮他试了试油门,两个人一面干着活,一面聊起天来。张德理被这个初交的人的热心帮助打动了,他一点不拘束地和顾群交谈着。顾群听张德理的谈话,同时仔细地观察着他的面貌和动作。他发现这个人很结实,身材不高,手脚很灵快,在安装车上的小螺丝的时候就像一个修表匠那么利落。他的面貌显得老一点,但是很朴实,眼角上已经显出皱纹了,鼻子直直的,嘴唇厚一点,髭须刮得挺干净。顾群想:这个人会是信上说的那阴谋破坏的头一个么?车子检修完了,张德理弄了一盆净水和顾群洗过手,顾群递给他一支烟,可是张德理不合吸烟。顾群点燃烟,帮着把车子倒进车棚,他们就坐在那车棚旁边的假山上“闲聊”起来。
顾群有意地把话题从车子谈到宴会,从宴会又转到四月五日。一提起四月五日的宴会,张德理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道:
“你看,那天我还答应赵师傅一件事呢,这些日子一忙,倒给忘得光光的了。”说着,他的脸就红了,还不住地责怪着自己记性坏。
顾群十分急于想知道这件事,而且奇怪:不是说他与姓赵的不认识么,为什么他答应给姓赵的办一件事呢?可是他仍然很平静地问张德理是什么事这样着急,那个赵师传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唉,你不如道,”张德理说道:“宴会那天,
我们几个年纪大点的人在俱乐部里嫌小伙子们咋呼,屋子里又有点热,就一起到‘钓鱼台上闲聊去了。……”这时,屋里的电灯亮了,张德理站起来说道:“到七点啦,咱该开会去了。回头再聊吧。”
顾群做了一个阻止他的手势,说道:“不要紧,我好像听说……”话还没有完,服务员在院里好像接应地似的喊起来了;
“今天晚上的会改期了,时间另通知。”
顾群笑了笑说:“你看,我听说的没有错吧。”
张德理也笑了笑;又坐了下来, 继续说道:
“你问那个赵师傅呀,就是五所的那赵建成,他开车有经验啦,创造了九万公里的安全行车。”
“早就听说过,就是没见过面。”
“多阵我给你一块去,向他请教请教。我也是五号那天头一回才见面认识的。”张德理望了顾群一眼,说道。顾群点了点头说:
“哦!一定陪你去。”顾群的疑问解决一半了。
“人常说‘武艺不能俱全不是,赵师傅就这样,他开车技术高,可修车不是专门。我呢,嘿嘿,当过两天技工,人都说修车还不大离不是,实际也不怎的。不晓得赵师傅怎么也信真了,我们那天在‘钓鱼台上说起他的新纪录来了,他说车子不晓得怎么搞的,好走不好站,总怕出事,一定叫我去给他整治整治。后来还约过两回,他说,五一节快到了,正是紧张的当口,动手迟了就不行了。你看,答应了几次的事给忘了,糟糕不糟糕。”张德理说完以后,还气愤愤地一股劲地埋怨自己,怕人家说他说话不算话。顾群这时却被另一个思想占据着,他没有注意张德理的情绪,但是,张德理谈的事情的真实可靠程度,是不能怀疑的,他想,这样看来,只要找到写信的人,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束了。不过,他还是按照计划进行。张德理突然问他道:
“同志,你的名字是……?你看我这个人的记性,刚说了就忘了。”
“哦!我叫……”顾群脑子里忽然一闪:那信上写的张大力不是现在这个名字。于是就有意地说道:“我有好几个名字咧,起来起去,总起不出个像样的。我小时叫顾大,上学叫顾全,解放了才改了现在这名叫顾群。”
果不出顾群所料,张德理说自己也一样,几个名字没一个好听的。乳名叫张大力,学徒时叫张德力,叫得久点,后来解放了,爸爸很高兴,说现在像个人了,起个号吧,就起了现在这个张德理。”
“鬼子在的时候,‘同文汽车公司有个张德力,是不是就是你呀?”顾群像是无意中问了这么一句,可是张德力立刻就红了脸,像受了侮辱似的小声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开车的嘛,还有不听说同行的好手的?”
“甭提啦,那阵真是倒霉透啦!”
“那车行还有个张得贵,技术也不错的,对吧?”
“那家伙是个反革命!”张德理有点冒火的样子。“两面派!解放后在街上碰到一回,他说在市百货公司工作,后来去一问,才知他撒谎。以后派出所还到我家调查了好几回。真是知人知面不如心!”最后他又愤愤地补充一句道:“我要再碰上他呀!不要命也得把他逮上派出所。”
顾群和张德理谈得很愉快,他送他出交际处大门,然后慢慢地思索着回到人事科的接待室。
当他回到接待室的时候,有一个年青小伙子站起来迎接他。顾群还没有来得及想想他是谁,那个小伙子就先发言了:
“你是市府的管理员不是?”
顾群有点莫明其妙,为什么这小伙子这么个劲头。没有等顾群回答,那小伙子又说下去了:
“人事科的莫同志打电话叫我来的,他说市府的一个管理员要找我谈谈,我想,谈啥?准是了解五一节的准备工作,就赶紧来了。来这里一个人影也没有见,我就坐在这儿,已经等你好半天啦。”顾群听了,才明月人事科的莫同志把他的意思转告错了。他原先是说自己去和平小海的管理员谈谈的。不过既然来了,也好。他把这小伙子打量了一下:他穿一身新做的蓝制服,左胸口袋里插着钢笔,口袋上沿别着一个“中苏友好”纪念章。一张自来笑的脸孔,粗眉黑眼,有一股俊气。顾群想,这准是一所的那个小平子,大概他是兴冲冲地跑来的。不过为了郑重起见,还是问他一句:
“你贵姓?”
那小伙子没有料到顾群这么郑重其事地端详他和问他,所以倒有点不安起来,回答道:
“我姓平,叫平小海,是……”他忽然又转过话头来,学着顾群的样,正正经经地问道:“管理员贵姓?”
顾群忍住了笑,答道:“我不是管理员,原是个开车的,现在市府交通科。我姓顾,人叫我老顾。”
“哦!”平小海有点失望的样子,不过他还是很热情地说:“开车的也是上级机关来的呀,不要紧,咱们是同行。你是要了解车子检修情况的吗?”
“是呀。咱们坐下来聊聊吧。”
“好。”平小海一坐下就说开了:“我们那里,准备工作不大离啦,车都检修完了,大家还订了保证书,比如……”
时间是有限的,顾群怕他拉得太远,赶忙插进来把话题转到开车的技术上去,想从这里转到正路上。谁知一提起开车的技术,平小海立刻眉飞色舞,话像河堤开了口子,别人休想插进半句去。
“咱们一所没有高明的,五所的赵师傅那才真是有本事,九万公里,哧,没有出点小事故。不过,苏联的纪录你知道,是十五万公里。我呢,现在才四万三千,正赶呢,向十五万公里赶。不敢说没问题,可真想赶上。噢,我说老顾同志!”他把声音稍微放低了点,像一件秘密那样凑到顾群跟前说,“我可是在找另外的窍门呢,就是省油的问题。”
紧接着他就说起苏联的先进经验来,提起好几个苏联先进汽车司机的名字,就像是他的老朋友。顾群几次想把话题引到四月五日的宴会上去,不但无效,结果反倒被这个笑脸的小伙子的动人的故事引入了神。平小海先是非常激昂地批评了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他们说“什么省油,行车安全,主要是看机器的好坏”其实呢,据他平小海的意见,“这完全是看你钻研不钻研”。他不让顾群张嘴就说了一个故事:苏联的一个同志,创造了省油的纪录以后,有人就说,那是油壶子的关系。反对的人的说法是,工厂里每出一万个油壶子就有一个是特别
省油的。他们要验一下这个同志的油壶子。这个同志一点不含糊,也不嫌麻烦就把油壶子换了。可是只跑了一天……
“你猜,怎么样?”平小海瞪着眼问顾群,可又不等顾群回答就说了:“结果还是这个同志节省油。”接着他又问道:“这是什么道理呢?”顾群只好点头,他又答道:“完完全全靠钻研罗。”
“对,钻研,就是靠钻研。”顾群好容易说上话了。他尽最大的努力把话转开,并且也决心不让平小海插嘴。说道:“要是大夥都钻研,你看咱们全市该省多少油,不说一年,就比方说一次宴会吧,要出多少车子,你想,四月五日那天一百五十多辆车,一辆来回就算省二两油也就是毛二十斤油呢。”
“嗬。谁说不是,”平小海又兴奋起来,“那天我还和他们争来着。从俱乐部争到‘钓鱼台,结果……”
这下差不多了。顾群想。赶紧又问道:
“结果他们都反对你,是吧?”
“那些人够呛,特别是主办宴会那个机关的有个家伙,他问我省了多少?你知道,我才开始研究呢。真他妈损人不利己。”小平不知怎么这样冒火,竟不客气地骂起人来。
“慢慢来吗,事情开头总是有困难的。”顾群好像是安慰他又像是鼓舞他地说。末了问道:“他们都是谁呀?”
“有处里的老张,五所的赵师傅,办宴会的那个机关的有两个,一个姓陈,那一个家伙谁知他姓个啥,一对耗子眉毛,三角眼,说话阴里阴气的。”小平子对这个人的印象不知为什么特别恶劣。
顾群暗暗地不住点头,同时又问了一些当天的别的事情,他想在这个小伙子身上证实一下刚才张德理谈话的真实程度。但是平小海说的与张德理说的几乎连词句都一样。顾群松了一口气,想道:看来问题在那个“耗子眉毛”的人身上了。要是真的这样,我倒愿意多听几遍你的省油的故事呢。
花布包
他送走了平小海以后,已经十点过了。谈话的声音还在他底耳朵里响着,他心里想道:这两个人无论你怎么说,至少我是不能把他们同反革命活动连系在一起来想的。但是写信的人又为什么花很大的功夫来打听他们的名字呢?而且连张德理的小名也打听出来了。难道三个受信的人中有一个有问题,两个是被利用朦骗了的?……他们几个人确实在历史上都有可疑点。未必就这封信是挟嫌陷害?唔,这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是,他们和别人有什么仇隙呢?因为是和那“耗子眉毛”争论省油问题吗?不可能。为什么呢?顾群想到这,情绪兴奋起来了。无论如何,总要弄清楚。又是时间呵,为什么过得这样快呢!
顾群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停留在院内那棵槐树下面了。他曾经多次凝神注视过的这棵槐树,好像问题的答案就在这树上的白花上一样。他纵身一跳,拉下一串槐花来,深深地嗅了一下,向着街上走去。现在,街上已比较清静了,行人已很稀少了,偶而有一辆汽车在马路上急驶而去。他的思想已不像几小时以前那样纷乱,而是好像把一团乱麻理出了根头来似的,只要抓住这根总头,整个麻团就会缠在他的手上了。他要使自己的脑子稍稍休息一下,以便开始更紧张的活动。于是迈着平稳的步子,向人民广场走去。他走到广场的入口处,停下来点燃了一支烟,抬头望望天空,星光在顶上闪耀着,一直延展开去,降落在广场北面矗立着的“主席台”上,和“主席台”前面牌楼上的各种彩色的电灯光交溶在一起,把“主席台”衬托得更加雄伟壮丽。顾群信步进了广场。在广场上,有一些父亲们和母亲们领着男女小孩,在那里东走走,西望望,还有一些从乡下来的老大爷和老大娘们,在他们城里的年青的亲戚们引导下,指指点点地观看着这十分美丽而雄伟的检阅人民力量的地方。“主席台”下面伫立着一个持枪的公安战士,在他的旁边有一个抱着大约两岁幼儿的年青母亲,指着毛主席的画像教她的儿子喊:“毛主席!万岁!”顾群望着,想着,心情激动起来。这是多么难以形容的动人而庄严的情景呵!北京的天安门前该又是多么壮丽安伟的情景呢,不难想像,“五一”那天,会有多么伟大的场面在那里出现呢!难道人民容许暗藏的敌人破坏我们伟大的节日么?不。无论在什么地方,顾群心里向“主席台”上伟大领袖像起了誓:绝不容许!
在出了广场的路上,顾群快乐地又深深嗅了一下槐花。“好香呵!”他奇怪地喃喃地自言自语说。真奇怪,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槐花竟是这么香。槐树在自己的家乡是很多的,幼年时候对它已经很熟悉了,可从不记得槐花有这么可爱的气味。他现在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很美丽,很和谐,很亲切。街灯在夜色里照亮了一切,道路两边机关门口扎着彩楼,五颜六色的小灯泡闪闪放光。街道像一个美妙的姑娘身上挂满了发光的珍珠似的那么灿烂可爱。
“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容破坏,都不容许从我们手中失去……”顾群走进了已经安睡的无人的街道上,默默地想着。
……顾群回到自己的亦公室,拧开电灯,刚刚坐在沙发上。他的助手好像是随在他身后似的,跟着也推门进来了。顾群望他一眼,注意地听着他的报告。助手按着次序将顾群交代过的一些工作简要报告了之后,说到一个新情况,使顾群的眉头微微发起皱来。
“……有人看见,下午九点多钟的时候——我想就是你和张德理谈过话以后——赵建成从张德理家里出来,拿了一个花布包,看样子包着的是圆东西,约六七寸直径,提在手里很小心的样子。以后,不知他到哪里去了。过了二十来分钟,又看见他走进自己的家,花布包已经空了,手里拿着那块花布,好像用水湿过的。……”
顾群一动不动地沉思起来,眉头皱得紧了,半晌没有说话。忽然抬起了头问道:
“局长有新的指示么?”
“局长说敌人并没有放松他的活动,要你很快把这个情况弄清楚。”
“旁的呢?”
“让你按原计划进行,他已作了必要的措置。”
局长的这个指示,使顾群刚才那种有点波动的情绪又镇定了下来。他对他的助手说道:
“好。那咱们动手办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