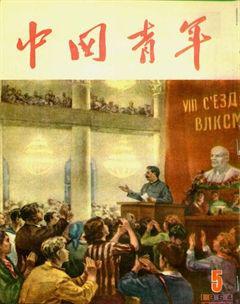北欧印象
陈家康
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早上,丹麦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处从哥本哈根打长途电话,通知设在巴黎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秘书处,通知里说:法兰西、波兰、不列颠(英国在欧洲的通称)、南斯拉夫的青年代表业已到达、捷克斯拉夫、匈牙利的青年代表已在经过波罗的海赴芬兰的途中,苏联青年代表业已启程,丹麦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处并要求担任这个几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的中国解放区青年代表立即首途,以便原定访问日程不致耽搁。对于丹麦驻巴黎总领事签发入境证的多方留难,可以置之不理。六日下午,天气晴朗,我登上由巴黎开赴哥本哈根的飞机,开始了访问丹麦、芬兰、瑞典、挪威的北欧征途。
北欧留在我脑筋中的,是一幅饶有特徵的印象。四个小国:丹麦的人口四百万,芬兰四百万,瑞典七百万,挪威三百五十万。其中丹麦、挪威、瑞典都是王国,又都是社会民主党组阁。社会民主党岂不是一个自命代表工人的政党吗?为甚么在资产阶级底政权之下,由社会民主党来组阁呢?在挪威,一次晚饭后的谈话中,有一位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说:“这就叫做伟大的民主。”大家说要听取东方友人的意见,我就说:“这叫做伟大的骗局。”
我说这句话是有些感触的。原来,先一天,有位糊涂天真的白发如银的女作家,充满了受委屈的情绪,用法文和英文夹在一起向我这样申诉。她说:“她感觉挪威总有一点甚么东西错了,但不知道甚么东西错了。”她又说:“她想政府是决不会错的,因为十二年来挪威并没有资产阶级的政府,都是由社会民主党组阁,这是劳动阶级的政府啊!难道还会错吗?”她最后请我不要把这番话告诉她那自由主义者的儿子,因为他不同意挪威有什么东西错了,除了自己家里渐渐没有肉吃而外。一九四八年五一节,我们仍在挪威的京城奥斯陆。这一天照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分开进行,参加社会民主党行列的工会和工人,并不少于参加共产党的行列。在社会民主党的行列中有人高举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标语,再加上一幅六肚皮资本家和工人同舟共济的水彩画。替我们做翻译的一位挪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气愤地说:“要不是社会民主党替资产阶级效劳,挪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比现在要好一万倍。”苏联的青年代表是少共真理报的总编辑布尔柯夫,他坚持要和挪威社会民主党青年头儿们谈判一次,我们委托挪威青年去约他们,都被拒绝了,布尔柯夫于是更加保持,他说俄罗斯有句俗语:“麻汉麦不肯朝拜山,山只好去朝拜麻汉麦。解放的中国和苏联总算得两座山,让我们去看他们吧。”结果几国青年代表团就去会见挪威社会民主党青年运动的几位负责人。见面之后、我就说明来意。接着布尔柯夫责问他们为甚么背弃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伦敦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约言,公然从世界民主青年战线中分裂出去。挪威社会民主党方面有一位青年老爷打起英国议会中的腔调,转湾抹角地说了一通,害得布尔柯夫底英文翻译听不懂他所说的究竟是些什么意思,要我解释。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表明不顾意和世界民主青年运动合作,理由很明显,因为马歇尔是挪威社会民主党底朋友,我们恰巧就反对马歇尔计划,因此,他们不能与反对他们底朋友的人们合作。布尔柯夫一直望着这位社会民主党青年工作负责人。这次会议也就至此而止。我在丹麦所看见的社会民主敖与在挪威所见到的都是一邱之貉。丹麦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几国青年代表团安排了两次约会,都在丹麦议会中,与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工作负责人见面。有一位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工作负责人叫做霍夫曼的用低沈的声音说出如下的话:“我们不顾意合作,合作必须有根据,而这一根据在我们看来是没有的,因为你们已经超出了西欧传统的“民主”范围之外。”在斯托哥尔摩,瑞典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我们安排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一位工人教育专家举行了一次座谈。这位先生大谈了一阵民主教育之后,我问他:“社会民主党代表甚么阶级?”他说:“代表无产阶级。”我又问他:“社会民主党讲甚么理论?”他说:“马克思主义。”我又问:“是否承认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发展呢?”他说:“当然不承认,”
我又问:“然则你们是否主张打倒资产阶级呢?”他说:“逐渐推倒。”说时并用手作慢慢推的姿势。我再问:“多少时候才能推倒呢?”他说:“不能太急。”坐在我旁边的一伙瑞典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说:“再推两百年,也不会倒。”也许在这次出访中,最富于戏剧性的还是关于民主制度的问答。我问这位瑞典社会民主党底工人教育专家,“你对民主制度作何解释,”他还未回答,几国青年代表团底英国代表,那是一位出身份牛津大学而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小人物、就插进来说:“何不问我?”我说:“请教。”他讲:“民主制度的精髓并不在于少数人愿意服从多数底决议。,而在于多数人愿意保护少数人底自由权利。”那位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教育专家连忙应声说:“对,对。”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是一位资产阶级的少爷和一位名叫社会民主党的家奴站在我们底面前谈话;又好像是路易乔治和叛徒考茨基站在我们底面前谈话。我想我该逼他们一下。我说:“例如法西斯残余份子这种少数人应不应该有自由权利呢?”于是他们两个人都有点尴尬,不知如何对答。说保护吧,说不出口,这就等放说保护世界人民底公敌(尽管他们心里在想保护法西斯残余势力);说不保护吧,所谓“保护少数”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不免当场破产。总之,所谓自由主张者不过是一部份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份子底高雅称号,而社会民主党则是资产阶级底狗脑子和代理人。北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目前欧洲沸腾的政治斗争中的死角。因此,社会民主党问题,还不能像人民民主国家那样迅速的获得解决。躲在这个死角当中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暂时是会洋洋得意的。然而北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目前新的国际形势下比从前任何历史阶段更为觉醒,消灭这个死角,也就为期不远了。我总记得有一位匈牙利的共产党员由中国回到布达佩斯,报告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情况,讲完之后,听众提出问题:“目前中国社会民主党底活动如何?”报告人笑了,并解答说:“中国并没有像咱们欧洲老乡们所见的叫做社会民主党的政党。”听讲的群众立该鼓掌欢呼。有位朋友把这故事告诉我,并说:“你们真的这样幸福,没有社会民主党吗?”我说:“在中国,是否有人沾染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是另一个问题,至于像欧洲社会民主党这种分裂工人阶级的组织,我们的确没有。我们中国工人阶级,自有职工运动以来,就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底领导之下。”这位朋友紧紧地握着我底手,用庄重的表情喊了一句:“毛泽东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