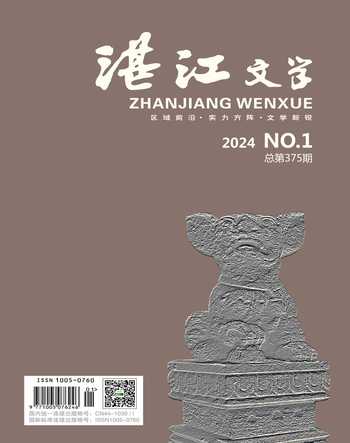狗尾草,随风摇
邵婷
春风洋洋洒洒,肆意慵懒地轻吻大地的时候,山间田野里便布满了绿色甚至于那生冷硬横的水泥路闭塞狭窄的缝隙间,也丛生出星星点点的绿来。那是初生嫩芽的鲜绿,是原始木林的深绿,是贵如玛瑙的翡翠绿,是摇曳在我童年时光里的狗尾草的绿。
狗尾草,学名狗尾巴草。顾名思义,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形状与小狗的尾巴相似,一杆杆,一丛丛,一片片,毛茸茸软乎乎的。风过处,炸开的穗子高高地翘起,悠悠摇曳,翩翩起舞,让人禁不住产生想要抚弄的冲动。它翠绿狭长的叶子向上生长、向四周散开,好似少女那被俏皮的微风撩拨而起的裙摆,托起轻盈纤细的身子,随风扭动着腰肢。狗尾巴草的身影,与春风掀起的婀娜多姿的柳枝一齐,蓬勃在我家乡的土地上。
因着特定的地理环境,土壤灵性与植物的生长习性,我家乡的食粮主要以春小麦为主。依稀记得我七岁那年的春天,与母亲一同在田野里播种小麦。远山浩浩汤汤,绵延的山势起伏不定,这一块高高的,耸入云天,那一段又谦卑地伏下身子,放低了姿态。山与山相连,起承转合,农民们难以寻到一块平整的原野,以开垦播种,只能在陡峭的山间行走劳作,步履不息。于是,高原之上,一块块一洼洼平展整洁的梯田应时而生,如悬挂的天梯,层层叠叠。母亲和我就是在这样的田里劳作的。说是“母亲和我”,其实干活的是母亲,我只是摇晃着脚丫坐在地头,欣赏着暖阳晴空下飘浮在对面山头的流云,放空,遐想。身后是家中那头衰老的黄牛缓慢而沉重的呼吸声,母亲“不近牛情”,扬手挥下的长鞭落在黄牛身上的响声以及崇山峻岭间此伏彼起的吆喝声。
碧空下,永远孤独的山风行云般游走,吹起贴在我稚嫩脸庞上的碎发,空灵中夹带一些难以琢磨的声息。屏气,凝神,仔细品味,我似乎听到了千万滴汗水跌落进泥土的声音。书上说,挥洒汗水,收获希望。年幼的我告诉自己,那是千万颗希望迸发时生出的动静。
温煦的和风悠荡,云彩飘移,圆蓬蓬的一大片忽地泛起涟漪。彼时,风的形状是那鸳鸯戏水的湖中盛景,从山的背面飘来……美景不容辜负,我睁大眼睛,纹丝不动。对面地里的农人又一次扬起了手中的长鞭,落下,啪。古老的群山颤栗着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啪……我惧怕看见那双眼角带泪、无奈地浸着苦水的黑色眼睛,极快地收回了漫散的目光。远方的风光是不清晰的,模糊的,看着看着就蒙眬了双眼,脚底的风景才是新鲜的,真实的。地头,高高隆起的田埂上,龟裂的土地裂缝里生长出一片绿茵茵的狗尾巴草。新生出来的叶子,细,绿,娇,嫩。修长的茎秆拔节生长,孕育而出的花穗,绽着极细、极小的绒毛,像是刚刚满月的婴儿滑嫩脸庞上细软的茸毛,令人不忍触碰。
芳草萋萋,渐迷人眼。我终究是没按捺住掌中难耐的痒意,伸手,向上提,狗尾巴草的草穗与围绕着上支的叶丛分离,弯着头颅,站在一张它无法抗拒的手中,沉默着,臣服于自身生命之外的力量。
掌中的狗尾巴草轻灵,地上的狗尾巴草美丽,它们都随风摆动。花穗灵动着跳入我的眼眸,梦幻,轻盈,我不忍眨眼,生怕错过它被微风撩拨而起的春光。慢慢地,它在我的眼中变了模样。烟雨朦胧,雾气缭绕,它成了书纸扉页上温婉秀丽的如画江南,我仿若置身其中,在河边岸畔古老的青石板路上漫步,转入小巷,不经意抬眸,便会遇见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思绪纷飞,母亲已经播种完毕,收拾好器具准备回家。我方才回过神来。狗尾巴草细密的绒毛间镶着雨滴,晶莹圆润,玲珑剔透。原来是落雨了。毛毛细雨,连成丝密密地织了起来,濡湿草尖。我拿着那株狗尾草,快速地跑到母亲的身前。走出地头,踏上乡野的荒径。小径幽长,蜿蜒,崎岖,宛如披着青绿外衣的长蛇,逶迤着爬向不知名的远方。
刚刚能没过脚踝的青草,摇晃着,扫落栖身在我裤脚的灰尘。那是一条有坡度的,略微有些倾斜的小路。我玩心大发,张开双臂,顺着小径从坡顶飞奔而下。路两旁植着的稀疏的树木,直逼我而来;扑上脸颊,拥我入怀的风中带着一种呼啸的声音,我的心里有一种要呼啸的欲望。然而我最终没有呼啸,只是放肆地、豪迈地大笑。笑声清澈,穿透尘石堆积而起的大山,悠扬回荡。小时候的我喜欢那样一种令人屏息炫目的速度与豪情。
大约每个生命在最初的数载光阴里,都曾这样狂妄猖獗,肆意地奔跑过,大笑过。
“乐极生悲”这个成语,真是上帝信口说出的咒语,灵验,禁不起世人一丝一毫的挑衅。斜坡的尽头,我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殷勤地拥抱住春雨润泽过的土地。四脚朝天,衣物沾泥,膝盖破皮,嘴衔青草与湿土,手中的那杆狗尾巴草也不见了踪影,惨不忍睹!
沙石刺入皮肤,身体经受的剧烈的疼痛支使着我大脑的神经,就这样,一动不动。抬眼,身前是一片从闷热的泥土里滋长出来的荆棘丛林,弯曲着向上,生长攀爬,缀满尖刺,堵住我的去路,张牙舞瓜,随时准备着啜饮我血管里流动着的液体。后方响起母亲匆忙奔下的脚步声,人还未到,饱含着怒气的责怪声急走而来,其威之大,生生将横亘在我眼前的荆棘丛林震得稀碎。小路露出它本来的面貌,峰回路转,一片清明。我赶忙从地上爬起,麻溜地拍去衣服上的泥土,抹净脸上的秽物,站在山脚,静静地等待着母亲,或者是,静静地等待着母亲的数落。
许是我的惨状逗笑了母亲,料想中的责怪并没有袭来。母亲走到我的身前,抬手,抚上额头,从我梳起的马尾间掂出一杆狗尾巴草。嫩绿的花穗,沾染了些深褐色的污泥。原来在我踉跄摔倒的时候,它聪明地藏进了我浓密的头发里,只不过还是没能躲过与泥土擦身而过的命运。
我看母亲的思绪被这株狗尾巴草占据,旺盛的好奇心又开始蠢蠢欲动,向母亲询问起了狗尾巴草的历史。
回家的途中,母亲侃侃而谈。据传,狗尾巴草是仙女下凡时,从天上带下来的爱犬化作的。仙女在人间和一位书生相恋,但遭到王母娘娘的阻挠,仙女和书生为了在一起,不惜反抗王母娘娘。在对抗的最后的时刻,仙女的爱犬为了救助人而不惜舍弃自己的性命。最終仙女和书生化作了阴阳两块玉佩,在人世间流传。相传相恋的两个人,如果分别获得这两块玉佩,便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仙女的爱犬死后则化作了人间随处可见的狗尾巴草,世世代代,传承着对爱情的见证。
天空中,密布的乌云散了开来。春日温暖的阳光,似母亲慈爱的目光般铺散开,斑驳,折叠,云端闪现一弯长虹。长虹映射下,雨后空气中飘浮的尘埃,是梦幻的彩色。我不禁叹气,顺手摘了一株路边的狗尾巴草。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细细想来,自人类文明伊始,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大都有着梁祝化蝶的京婉凄清。有幸相遇,千帆过尽,终是难以再续前缘。机缘巧合,因果轮回,无尽思念,我们耿耿于怀,久念在心的,竟全是哀啭久绝的旷古悲情,破镜难圆的悔恨之泪,是遗憾,不甘,执念。人们试图从生理,心理,甚至是神学等诸多角度探索爱情所蕴藏的奇妙奥义,成果似乎还不错,不是一无所获,却也并非大获全胜。于是,一棵草,一滴云,一片羽毛,都可以与爱情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天,我问母亲,你和爸爸之间,有爱情吗?母亲沉默良久,埋着头将狗尾巴草编成小狗的模样,插入我的发梢,说:“我和你父亲,过的是生活,不是婚姻。”
七歲的我,懵懵懂懂间也觉察出母亲语气里的失落,识趣的不再追问,被编织成小狗模样的狗尾巴草,也不再随风摇晃身子了。
山脚下的小路是平缓陡直的,尽头是一条淌着涓涓细流的小河,几块岩石稳稳地立在河中央,高高地凸起,裸露出溜平的表面,充当水上桥的角色,截住了流水的去路。我酷爱联想,行走在桥上,常常会产生这是一座狭窄细长的岩石小道,左右两边皆是万丈之深的悬崖的错觉。我深知这是错觉,然而那种孤立无援的感受,出乎意料地真实。
我就是在这儿,在这条小河边,遇见我的第二只小狗的。第一只小狗,是母亲为我用狗尾巴草编织的。
它虚弱地跪卧在河边的一棵柳树下,伸着粉红色的舌头,贪婪,吃力地舔舐干净的河水。灰扑扑的狗毛,浑身上下沾满泥土,使人疑心它应是才从泥潭里爬出来。从它的身形外貌,不难推测它是被山里人家遗弃的小狗宝宝。那年月,农民们圈养的鸡、鸭等牲畜总是莫名的不见了踪影,拔葵啖枣之人更是畅行无阻,人们对此深恶痛绝,于是各家各户的门口多了犬类的踪迹。
月华初上,公鸡打鸣时,犬吠最为热烈,表明忠心似的,号叫着赶走那些蹑手蹑脚,摸着黑,苟到人家门前的心存侥幸之人。渐渐地,梁上君子少了。人类惯行千年的法则,用则养,无用则弃。初生的小狗被视为累赘,丢到荒山野岭,成了在荒群中的孤狼的美味珍馐。人们毫不在意,夸夸其谈,自豪地说,人类的道德良心战胜了一切。
它大抵是累了,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恳求母亲允许我将它带回家。若是让它继续留在这儿,毫无疑问,不久它就会成为一堆招惹虫蝇的腐肉,臭气熏天,遭人嫌恶,变成那棵柳树的养分。母亲也不忍一个可爱的生命就此湮灭,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很开心,手舞足蹈,一路小跑着,奔到它的身边,拔了些生在河畔的野草,小心翼翼地揩去了它身上的灰尘,抱着它回了家。
回家的路途并不长,像是黄土里冒出的青草的一生,在一场又一场春雨里,伸展着柔软的骨骼,噼里啪啦地生长,倏然而逝,一下子就到了头。生活不经意泄露的春光流入眼眸,幻化成一棵参天的大树,枝丫繁茂,彼此纠缠,在无数飞扬的尘土与时光的洗礼中,变成了那印证光阴流逝的年轮,一圈,两圈……无数圈,被安放,被搁置,但不曾被遗忘。记忆是宽容的,长大了的人,总爱追忆往昔。狗尾巴草婆娑过的童年时光,是入了诗的。
它是条可爱的斑点狗。酷似巧克力的棕色斑点零星地散布周身,是落在素白雪地里的诱人的奶酪。在我的家乡,它和大地上俯拾皆是的狗尾巴草一样普通。小狗熟睡时,我爱用狗尾巴草那招人喜爱的花穗,轻轻摩挲它的鼻尖,逗的它哈欠连天。一日,我突发奇想,激动地向家人宣布,我们为它取个名字吧,就叫“狗尾巴”,怎么样?父母对这事一向不重视,只有一年级的弟弟捧腹大笑,挖苦我给小狗取了一个这样土的名字。我不服,冲他科普。“狗尾巴”这个名字,取自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具有清热利湿,祛风明目的作用,是个宝贝,可金贵呢!弟弟半信半疑,我使出撒手锏:书上就是这样说的。弟弟信了,欣然接受了这个土得掉渣的奇葩名字。然而他不接受也无妨,又不是给他起的。
村里的小学,离我家很近,穿过水泥路,再下个坡就到了。清晨,曙光初现,青草尖上的露珠还在酣睡,做着甜美的梦,幸福地裂开了嘴巴,破碎。狗尾巴晃着脑袋,在潮湿的路面嗅来嗅去,跟着我到了学校门口。我训它:快回去,你不能进学校。它果真听懂了我的意思,吐着舌头,端坐在校门前,不动弹了。天气闷热,讲台上,老师妙语连珠,开合的双唇像是玻璃水缸内不断地吐露着泡泡的鱼的嘴巴,一张一合,让人脑袋发昏。许久,喻示着下课的电铃声响起,同学们蜂拥着跑出教室,与称霸整个操场的野草一同撒欢。
我注意到狗尾巴仍然坐在校门前,闭目,等待着它的主人。操场上的其他同学也注意到了狗尾巴的存在,瘦弱的胳膊伸出,握住狗尾巴的前爪,一托,一拉,狗尾巴轻易地穿过了有着巨大缝隙的铁门,即将售出的拍卖品般,局促地暴露在这许多视线中。狗尾巴的毛很光滑,在阳光的照射下,白得发亮,摸起来也很舒服。毛茸茸的脑袋,圆溜溜的大眼睛,蠢萌蠢萌的。眨巴两下眼睛,便俘获了小孩子们的芳心。他们把它抱上膝盖,互相争着抢着,给它投喂从家中带来的美味,泡馍,大肠,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还拿出了珍藏已久的干脆面。偌大的操场上,他们领着它,疯狂地奔跑,摸爬滚打,清早还算干净的衣物顷刻间沾满尘土和杂草,以及青草爆出的鲜绿的汁液。
当他们得知狗尾巴是我家的小狗时,惊异地哇出声,纷纷向我投来艳羡的目光。七八岁小孩子的思维大概就是:只有有趣的人,才配拥有这样有趣的小狗,仿若五角星永远填不满的长方形容器,直观,不懂嬗变。
套用世俗的观点,我确实不是一个有趣的人,沉闷压抑,不爱说笑,绷紧的脸皮像一面被卸下的发黄的鼓皮,巨石抛在上面也难闻其声。校园里那只可爱的小狗是我的。这个消息彻底散播开时,小孩子们间衍生了些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变化。他们绽着比花儿还要璀璨数倍的笑容,将藏在背包中的零食递到我的手上,心安理得地揉搓狗尾巴脖颈处绵软的柔毛。
狗尾巴们到来让我成了焦点,一种陌生的、被关注的快感刺激着我的神经,虚荣心潮水般围住了我,我洋洋自得,嘴角弯上耳根,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在不断涨起的潮水中重获新生。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或许生而为人,最忌讳的就是大喜、大悲。那日,上帝脱口而出的咒语又一次灵验。班里最调皮的小孩子,拿着从小商铺买来的一块钱的小刀,揪着小狗的尾巴,切,划,割。嘴里还念念有词,它的毛这么顺溜,切了做毛笔,一定很不错。几只胖手牢牢地嵌住狗尾巴的身子,狗尾巴无力反抗,无望地呜咽着,像北风卷起的枯叶瑟缩着吼出的悲鸣。我愤怒地夺过小刀,推开他,将狗尾巴护在身后,死命地瞪着他。锋利的刀尖戳破掌心,鲜红的血液,顺着指尖滴落,啪嗒,啪嗒……荒唐的闹剧,最终以鲜血喷发出的蛇信子般醒目的警告结束。人性中最原始的恶念、自负、轻视、盲从,组成了那日的我们。那是夏天,狗尾巴草毛茸茸,花穗间嵌着不太饱满的籽粒;狗尾巴毛茸茸,依旧可爱,只是它不再,在我踏足过的小路嗅来嗅去。我没看见它的眼泪,可是我所站立的地方,分明是一片泛着咸味的汪洋,任凭我在其中寻觅,跌宕,发霉。
“绿树浓荫夏日长”的暑假,大伯家来了一位精致的城里姑娘,齐肩长发,桃腮杏眼,甜美而讨人喜欢,乃至鬓边微微蜷曲的碎发,也是俏皮又不乏可爱。我家与大伯家挨得很近,仅隔一步之遥。大伯外出农忙时,总会将她带到我家,命我陪她一起玩。我是极内向的,而她似乎也很慢热。于是,我们俩就像两个要事缠身的外交官,相隔数米远,正襟危坐,点头致意,相互谦让,尴尬如同蛰伏在老墙根的爬山虎,攀缘而上,密密麻麻,相互缠绕,让人喘不过气。院子里,在外面疯够了的狗尾巴带着一身的杂草,躺在水泥地上的阳光里打滚,使劲地摇晃脑袋,几杆葱绿的狗尾巴草跌落在地。她大概是很喜欢动物的,瞥见狗尾巴的身影,便忘了矜持,大呼小叫地跑到院子里,与狗尾巴玩闹了起来。
我学着母亲的动作,捡起掉落在地的狗尾巴草,变戏法似的,将它编织成小狗、小兔子、小老虎、花环、戒指、蝈蝈、笼子……她看着不起眼的狗尾巴草在我手中变换着不同的形状,圆睁的杏眼里满是不可置信,仿佛我同那射日的后羿般,也怀揣着什么讳莫如深的神秘力量。
曾在一位作家的书中读到过,越长大,越喜欢孩子。深以为然。命运恩赐的,没有经过深生熟虑的思想角逐的简单友谊,只有在孩提时,才遇到过。不出几日,团子与我,便亲密地如同一个娘胎里挤出来的似的。她极度偏爱《熊出没之雪岭熊风》中白熊山的山神团子,大张旗鼓地向身边人宣布:从今以后,你们就叫我团子。那时,温柔地拥吻乡村的东风已经流失散尽了,团子和我急切地想要抓住夏天的尾巴,在一片广阔的原野上放风筝。偃卧在青草尖的蛐蛐,用力地扯着嗓子,吼出嘶哑的鸣叫;阳光下,缀满枝娅的早熟苹果,也长到了爱美的年纪,偷摸着在腮间染上红晕。风筝的尾巴变得长,风中有了秋天的味道。
秋天,原野上的狗尾巴草,变成了神奇的紫色,一下一下,随风摇晃,像极了仙女遗落的裙带,在时光的最深处摇摆。孩童的注意力总是难以集中,飘入云端的风筝很快被我们遗忘。那段时间,团子和我近乎偏执地迷上了一种奇妙的昆虫——磕头虫。它暗褐色的身子狭长扁平,表面略光滑。它的样貌并不迷人,甚至可以说是丑陋,然而令我和团子着迷的并非它的外貌,而是它胸腔里发出的那一声声清脆的叩头声,似关节断裂的声响,刺激着人发麻的脊背,那原始的冲动与快乐。我们比赛着谁抓的虫子多,打算带回去沖家里人炫耀。回家的途中,遇到了位上了年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她望着我们,说:知道磕头虫为什么向你们磕头吗?它是在求你们放过它,给它一个生存的机会。每个生命,都有其生存的法则,切莫干扰,尊重即可。我和团子听得稀里糊涂,但还是放了它们。
如今想来,老人那融合进了一生的哲思的话语,意在教会我们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如野草丛中的狗尾巴草一样平凡的生命。宇宙不会穷尽,历史也是,哪个生命不是沧海中的一粒肉眼琢磨不到的尘埃,我们,一粒尘埃,又何必瞧不起另一粒尘埃呢!
“自古逢秋悲寂寥”,原来秋天,是适合告别的。临近开学,团子回到城里上学,临走前她说,我还会回来的。那时我们都觉得,回来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到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诺言。但它确是一个诺言,一个在时间里荒芜了的诺言,被锁在了年轮的最里层。村里的青壮年离去后,小学生们也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我的人生轨迹也按着社会既定的规律前进,从乡里,到镇上,到城里,到市里……渐渐地,离家越来越远了,狗尾巴被我丢在了老家的门前,守望,等待,老去。
前几日经过幼儿园门前,紧闭的大门内传出小孩子们稚嫩的歌声:小狗尾巴摇摇,小草尾巴摇摇,小狗尾巴翘翘,小草尾巴翘翘。摇啊摇,翘啊翘,摇啊摇,翘啊翘,变成一棵狗尾巴草。
你说,童年的那株被编成小狗模样的狗尾巴草,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