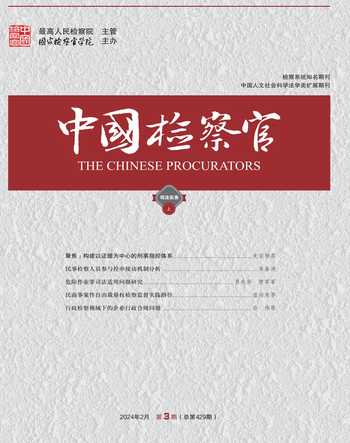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机制探析*
张国仓等
摘 要: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鲜明的社会公益性质,将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纳入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合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之理念。通过拓宽案件线索收集机制、确定案件范围标准、明确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以及合理设置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四个方面构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机制,增强执法司法合力,为加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
关键词:新业态劳动者 检察公益诉讼 劳动公益
新就业形态是指伴随着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依托新技术而出现的去雇主化、平台化的新型就业模式,具有就业方式灵活化、组织方式扁平化、用工范围扩大化等特征。[1]2023年,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统计表明,目前全国新业态劳动者达到8400万人。[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2022年最高检首次发布典型案例指导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要求“切实维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3]本文拟结合自身实践情况,论证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引入检察公益诉讼之必要性,提出构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机制,为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升级提质”。
一、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理论依据
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符合弱者保护和公共属性的公益诉讼理念,构建检察公益诉讼机制具备法理基础。一是新业态劳动者属于弱势群体。平台经济时代,数字权力高度聚集于大型平台企业,新业态劳动者的权利和地位相较于传统用工模式更为弱势。平台业务运营的基础是算法,平台业务模式的核心则是对新业态劳动者的算法管理,对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成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平台算法私有化使得平台权力不受限制,平台算法设计与开发存在责任主体模糊、监管空白的难点,平台企业单方面通過技术手段设定算法、制定规则和协议,新业态劳动者则缺乏规章制度制定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危及新业态劳动者程序上的参与救济权以及劳动保障的实体权利。另一方面,平台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依靠平台垄断地位、算法优势和信息的不对称,在管理上不断强化新业态劳动者对平台的从属性和依赖性。[4]二是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具有公共属性。一方面,新业态劳动者并非某个或某些少数特定群体,符合公益诉讼“不特定多数人”的要求。另一方面,算法作为体现了平台意志的一种公共力量,具有广泛的控制能力。在平台算法数据的驱动下,如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通过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来缩短配送时间,在高劳动强度下坚持疲劳送单的现象普遍存在,对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产生严重隐患。
二、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引入检察公益诉讼之必要性
(一)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立法存在不足
新业态劳动用工关系呈现出灵活化、碎片化甚至多元化等特点,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难以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致使新业态劳动者游离于劳动法律框架之外。整个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律框架体系存在以下短板:一是劳动立法相对滞后。我国现行劳动法主要调整稳定单一的劳动关系,而新就业形态突破了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范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再作为“单位人”来就业,主要通过网络技术与数字平台互动连接,来实现个人与工作机会的对接互动,基于传统用工模式制定的劳动基准制度则存在制度缺陷。[5]二是政策法规位阶较低。在新业态劳动领域,国家近年来出台的政策法规效力层级较低,缺乏法律应有的强制性、权威性和统一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刚性。
(二)传统劳动监察模式无法应对新业态用工模式
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劳动关系的变化给劳动监察增加了难度。一是平台企业的运作核心是通过算法和定位对劳动者进行工作分配和远程监管,所有用工都在线上完成,而相应的精准化监管模式目前尚未形成,以线下为主的劳动监察措施与线上用工的流动性和共享性不相适应,无法实现精准监管。二是平台企业往往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规避监管,致使劳动监察部门无法对其进行劳动监督。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为新业态用工模式下的劳动监察提出了新要求,但只是进行了宏观部署,缺乏具体的可执行性。因此,传统劳动监察模式在应对新业态劳动模式中的权益纠纷时就显得捉襟见肘。
(三)“一裁两审”的私权救济机制尚不健全
新业态用工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难以适用现行劳动法律制度调整,导致劳动关系认定困难、法律关系定性模糊,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受到系统性挑战。一是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弱化致使司法裁判处于从属性理论适用性供给不足和实践性需求扩张的矛盾之中,劳动者权益无法保障。[6]二是我国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采取仲裁前置的方式,“一裁两审”处理周期长,维权成本高,这既不利于快速解决争议,也使新业态劳动者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动力不足。同时,民事诉讼多从侵权责任角度入手保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在举证责任方面一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新业态用工模式下,证明责任要求高,取证困难。
(四)检察公益诉讼介入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存在独特优势
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介入新业态劳动关系进行监督存在制度优势。一是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公益诉讼的价值目标相契合。劳动法是以保护劳动者作为其价值理念,而公益诉讼存在保护公共利益的目标,两者在我国的理论和现实语境下具有极高的契合度。作为人权重要内容的劳动权,具有以公共利益为本位、适用“倾斜保护”原则的特点,建立新业态劳动保障公益诉讼机制,不仅符合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解决我国目前突出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理想选择和最佳司法路径。二是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具备实践经验。2023年最高检针对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侵害问题,专门指导多地开展专案办理外卖平台算法侵害新业态劳动者权益案件[7],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此可见,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以“专案办理”的模式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的有益探索。
三、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机制构建
(一)拓宽案件线索收集机制
由于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侵害行为大多发生在劳动者工作过程中,相关工作机制、奖惩制度等并不对外公开,侵害行为存在一定的隐蔽性,这为检察机关获取案件线索带来一定的困难,拓宽案件线索收集机制就成为检察机关及时介入的关键。因此,检察机关应采取多元化方式鼓励劳动者积极维权,加强相关线索举报途径的宣传,同时构建劳动行政部门、工会和检察机关三方信息交流和案件信息抄送机制来扩展案件线索来源,探索多样化的线索发现机制。
(二)将“劳动公益”作为案件范围确定的标准
在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引入检察公益诉讼的前提必须是存在“劳动公益”。所谓“劳动公益”是指不特定多数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并为劳动基准法强制保护的利益。[8]在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平台企业通过规则制定和算法监控,违反劳动基准法,造成新业态劳动者群体的劳动报酬权、休息权被侵害,并由此引发连锁性不利后果,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基于此,平台企业的违法行为不仅直接侵害了不特定多数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国家经济秩序和弱势群体保障等社会公共利益也造成了损害。因此,以新业态劳动者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作为确定案件范围的标准具备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三)确保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权的谦抑性
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就决定了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检察机关有职责进行监督和提请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判予以制止和纠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既包括检察机关还包括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因此,检察机关在行使公益诉讼起诉权时,要秉持谦抑审慎的原则,只有劳动行政部门或适格的社会组织在规定期限内不作为或不起诉时,方可提起公益诉讼。
(四)合理设置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为了有效的配置司法资源,合理发挥司法的政策引导和威慑功能,在公益诉讼启动之前应当设置诉前程序。关于诉前程序如何设置,当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将支持起诉和督促起诉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二是将行政机关对侵害公益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9]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劳动行政部门对违法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只是证明侵权事实的存在,不宜将其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第一种观点较为适合,因为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基准属于国家以立法形式确立的强行性法律规范,体现了国家对劳动条件的干预,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在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领域,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应通过听证、磋商等方式督促劳动行政部门履职,同时可以以检察建议、跟踪监督等作为辅助方式增加法律监督的刚性;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并支持起诉,在诉前程序无法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可提起检察公益诉讼。
*本文系2023年度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劳动者权益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研究”(GSJC2023-39-02)阶段性成果。
**课题组负责人:张国仓,甘肃省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741000]课题组成员:郭毅玲,天水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张楚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生;邓净元,甘肃省天水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洲芳,甘肃省天水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四级检察官助理[741000]
[1] 参见莫荣:《新就业形态的概念、现状与协同治理》,《新经济导刊》2020年第3期。
[2] 参见《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7/content_5748417.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月24日。
[3] 参见于潇:《精准监督,促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检察日报》2022年12月14日。
[4] 参见余少祥:《新就业形态的特征、挑战与对策建议》,《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16期。
[5] 参见王群:《数智时代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之反思》,《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6] 参见黄振鹏、张强、邵永强:《劳动关系理论视角下我国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7] 参见《“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最高检关注外卖骑手权益保障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NkmUyom34xBWSkwN5T4mhg,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月31日。
[8] 参见王兰玉:《劳动公益诉讼:劳动公益权保护困境的出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9] 参见林嘉:《劳动基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