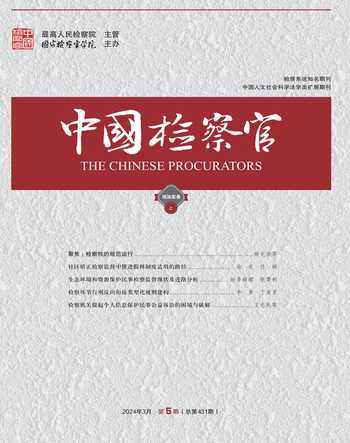轻罪案件公益服务考察机制的实践与完善*
金士国 卢冰茹
摘 要: 在轻罪立法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引导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后予以宽缓处理的宽缓机制应予以重视。以醉驾案件公益服务考察机制为例,实践中存在公益服务功能定位、制度适用范围的争议,存在考察时限过短及考察内容过于简单、监管评价难以全面真实反映情况等问题。为此,建议将公益服务作为品行纠偏的悔改表现情节纳入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保证一定期限的考察时长,强化深度考察评价,并通过行刑衔接强化问题治理。
关键词:轻罪案件 诉前公益服务 悔改表现 考察时长
在我国现有刑事制度语境中,参加社会公益服务大多用于社区矫正制度。而实践中的审查起诉环节引导行为人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是行为人在自愿接受教育矫治的前提下,以实施特定时长公益服务为表现形式的品行纠偏型的制度设计,即将原本类似于刑罚执行阶段的社区服务,移至定罪量刑之前。应该说,该制度实践顺应了当前轻罪案件增多、通过教育引导促使行为人改恶从善的形势要求,有利于推进轻罪治理。但在实践中,该制度面临如何规范、如何有效运行的问题。有必要对此研究分析,进一步予以完善。
一、公益服务考察机制的实践探索
2001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受港澳地区“社会服务令”启发,要求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社会有益的无薪工作,再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对其作出不起诉处理。[1]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陆续开始探索社会服务制度。如2010年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安排一名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做交通协管员,以考察其悔罪表现,再决定是否不起诉。[2]再如2018年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检察院、2020年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检察院、2021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醉驾案件社会公益服务均属于这种类型。[3]可以说,诉前犯罪嫌疑人参加社会服务并接受考察,有利于轻罪犯罪嫌疑人从公益服务中受到教育,也为检察机关对轻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作轻缓处理提供了事实依据,符合“三个效果”的价值导向。这也是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推行该项制度的实践原因。
自2017年12月,温州R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局、司法局和志愿者协会出台了《关于“醉驾”案件实行购买公益服务落实不起诉的若干意见(试行)》起,截至2023年底,温州检察机关共有8个县市区院出台了相应的轻罪案件适用公益服务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个别地方将案件类型从醉驾案件拓展到盗窃等案件,但大多仍属于情节较为轻微的情况。二是将公益服务的内容从参与道路交通安全维护,拓展至参与大型公益活动现场组织等。三是考察后的激励措施从予以不起诉处理,拓展至采取非羁押措施。四是绝大多数被考察对象通过考察,最终得以宽缓处理。如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共办理适用公益服务案件909人,除1件案件当事人中途退出故对其起诉外,其余均作不起诉处理,即不起诉908人,占同期醉驾案件中不起诉人数的81.94%,占醉驾案件总受理数的39.64%。五是大部分采取的是诉前考察模式,即将犯罪嫌疑人参与公益服务表现作为检察机关是否作不起诉的考量因素。D区人民检察院2020年曾探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以检察建议形式提出参与社会服务的要求,类似于国内的从业禁止令,其当时明确: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同时要求在1个月内完成公益服务,根据服务结果对被不起诉人的个人信用进行评价。但因为不起诉后自行悔改效果不佳,2021年该院又开始采用改前考察模式。
二、诉前公益服务考察机制运行问题分析
(一)诉前公益服务功能定位尚不确定,公益服务考察案件适用范围有争议
根据目前情况看,诉前公益服务大多是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宽缓幅度有限,故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挑选那些依据现有情节也能作相对不起诉的案件来作为公益服务考察的对象,以求能最终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有些基层院将诉前考察机制适用于各类轻微刑事案件,有些则适用于所有的醉驾案件。但若这样,诉前社会服务将失去意义,这也导致一些案件中公益服务时限较短、考察走过场。如在W县检察院办理的胡某某涉嫌危险驾驶案中,其公益服务的内容是发微信朋友圈宣传酒驾危害,亦有将公益服务流程虚化的倾向。
但也有一些基层院只将原本作不了不起诉处理的轻微刑事案件,或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或再犯可能性的犯罪嫌疑人,作为需要适用公益服务程序的对象,用公益服务来考察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悔改表现,经公益服务考察通过后才作不起诉处理。如R市人民检察院曾将悔改考察程序适用于有中等程度情节的案件,如:一是发生事故,造成轻微人身伤害或5万元以下财产损失,但已赔偿;二是或有酒驾劣迹超过3年或前科判刑超过5年的;三是认为应予以教育考察再决定是否作相对不诉的其他情况。但2019年采取此理念的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醉驾社会公益服務免刑制度引发“行善代刑”的质疑,需要进行理论回应。 [4]
(二)部分案件设定的考察时限过短,个别公益服务内容过于简单
实践中常见的刑事和解、补植复绿、增殖放流、退赃退赔等是可以即时履行的,检察官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与考察这些非刑罚措施完成情况能同步进行。而引导轻罪犯罪嫌疑人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明显具有过程性特点,效果方面需更注重考察品行纠偏与否。司法机关对参与公益服务的轻罪嫌疑人进行从宽处理,实质是通过司法激励措施引导行为人进行品行纠偏,也需要一定的时长。
因此,一些基层院的醉驾案件诉前社会服务考察也尽量拉长考察时间。但实践中,一般要在1个月内完成,包括教育学习和公益服务实践,服务时长从10小时到30小时不等。D区人民检察院2021年实施的文件也提出服务时长一般不得少于10个小时,次数一般不得少于3次。2021年T县人民检察院对未被羁押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设置社会教育相应考察期限时,一般定为3至6个月,强调考察期的长短应当与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性质、情节和主观恶性的大小相适应。
但即使是这样的考察时长,在实践中也难以有效发挥考察功效,甚至难以有效落实。原因在于:一是醉驾等轻微刑事案件倡导简案快办,力争在侦查羁押期限内办结。但按照公益服务考察重在通过一定时长公益服务进行品行纠偏、以体现悔改的制度原意,在正常参与的情况下要5、6天甚至10多天才能完成服务,那就占用了醉驾案件办案时限的大半,这必将影响审结率。二是由于个别犯罪嫌疑人距离较远、个人事务繁忙等情形延期参加志愿活动,或因服务质量不达标被延长服务期,或由于交通引导公益服务岗位有限等原因,导致公益服务常常未能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三是引入社会服务后,检察机关承办人需要经历提起—对接—审核—结论等一系列环节,给其增加了不少工作量,无法简案快办,也反过来导致一些地方倾向于选择案情更加简单的案件或公益服务时长更短、服务内容更为简略的考察模式。
(三)受委托监督考察机关对公益服务的监督流于形式、评价较为抽象
因对公益服务情况的考察增加了办案工作量,故检察机关通常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主要有两类合作模式。第一类是有偿模式。温州检察机关8个基层检察院中有3个院实行购买公益服务的模式,即由检察机关支付一定费用后委托相关组织对公益服务进行监督考察,再由志愿者协会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公益服务进行监督,并就公益服务的内容、时数、行为表现等方面情况形成评估报告供检察机关参考。但公益服务组织出具的公益服务报告内容往往比较抽象,监督过程中对懈怠行为没有进行监督及惩戒,检察机关对公益组织的再监督和检查具有偶然因素。第二类是无偿模式。5家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社区服务组织单位等机构合作,如醉驾案件犯罪嫌疑人参与交通文明倡导服务,一般志愿服务路口有监控视频,交警大队视频监控人员可对嫌疑人参与公益服务情况进行实时抓拍。检察院、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可根据监控对志愿者的开展情况进行评估,并决定是否延长志愿活动时长。但从实践效果看,监管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倾向。
三、诉前公益服务考察机制的发展方向
社会公益服务作为悔改情节,其定位尚不明确,制度运行难以维持,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罪后悔改行为如何激励、适用范围如何界定、考察标准如何确定等问题,都需在实体法、程序上更为体系地构建。
(一)明确公益服务情节功能定位,将需进行公益服务考察的案件纳入扩展后的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
诉前参与公益服务,体现了犯罪嫌疑人的悔改意愿和具体行动。将其作为宽缓事由的依据一般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事后悔改行为对被害法益的恢复程度。如犯失火罪后实施补植复绿措施,在犯非法捕捞罪后实施增殖放流措施,是一种直接弥补;而醉驾案件后参与交通安全引导,则是一种间接弥补。因为报应的需求主要来自于被害人。法益恢复对被害人的补偿更为直接、具体,相应地,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得以降低乃至丧失,因而适用报应刑的必要性也会降低乃至丧失。二是犯罪人再犯可能性降低。行为人主动实施法益恢复行为,显示其已有悔悟心理,再犯预防必要性不大,因而从特殊预防角度考虑,适用刑罚的必要性也降低。[5]如在我国刑法37条的但书条款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在犯罪情节轻微时,“确有悔罪表现”也被视为出罪的条件之一。
有观点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不起诉优先级应当为“法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递进式适用,也称为“阶梯适用论”。当前,附条件不起诉案件范围限于1年以下,都符合相对不起诉标准,已造成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混用、惩治力度较重的附条件不起诉侵占相对不起诉案件范围的情况。[6]因此建议:一是将附条件不起诉案件范围从“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提高到“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与相对不起诉案件刑期范围相同。二是在构成危险驾驶、交通肇事、故意伤害(轻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具备法益修复条件、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中,确有必要接受一定时期监督考察的,在诉前公益服务并经考察通过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其中的监督考察必要性,一般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辩解、主观恶性、前科劣迹、罪行情节、再犯风险等情况进行判断。三是在上述案件犯罪嫌疑人中,犯罪情节更为轻微,无监督考察必要性的,无需设置社会服务考察期,可以在直接作相对不起诉后责令自行悔改。
(二)对需要适用考察监管来判定行为人是否已经悔改到位的案件,要保证一定期限的考察时长
正所谓“习惯成自然”。实践证明,社会公益服务只有保证一定时长的考察期限,才能实现行为矫正、对悔改成效形成保障并体现一定的惩罚性。建立在一定时长基础上的、有效的悔改结果,才能成为涉案主体获得更大幅度宽缓处理的法定依据,而不仅仅只是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来对待。如荷兰的检察官有权对认罪且法定刑为6年以下的犯罪分子发出处罚令,让其参加不高于180小时的社区服务,考验期最长为1年。[7]因此,一是对需要适用考察监管来判定其是否已经悔改到位的相对严重刑事案件,要设置较长的考察期限,且不同的犯罪行为,对其的考察内容、考察时长也应有所不同。二是参照鉴定程序等制度设计,将诉前考察期限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只有这样,诉前考察期限才不会受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的时限要求限制,才可以設置一定时长的考察期限,确保通过公益服务督促品行纠偏的监督考察效果。
(三)完善诉前考察评价体系,规范督促检查
诉前考察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考察、如何评价。
一是明确检察机关在诉前考察环节的主导地位。目前,醉驾公益服务评价是寻找第三方或者行政机关来做评价主体,体现了集社会之力推进社会治理的理念。但实际上,有责任才能有压力,有需求才会有动力。检察机关是最终作出宽缓处理的决定主体,本着对决定结果负责的立场出发,其最有动力、最有积极性去保证考察的公平公正和有效。故应强调检察机关在诉前考察评价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强化对考察结论的审查权,可以根据证据情况对考察结论作出采信或不采信的决定,推动第三方监管人或接受监管任务的部门履职尽责。二是建立考察报告依法开示、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制度。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确保监管意见客观准确,就要让利益对立方来监督。故要探索建立整改考察报告依法开示制度,赋予被考察人、辩护人及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权利,确保考察报告公开公正。三是明确第三方监管责任。对第三方组织严重不负责任,出具与事实严重不符情况的,应取消其考察评价的资格或提出检察建议。
(四)强化行刑反向衔接,推动加强行政监管
醉驾等轻罪案件的治理,必须要强化梯次衔接治理理念。即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对于确有悔改、且经公益服务考察通过后作不起诉的行为人,应受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要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提出监督意见,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防止简单地将不起诉等同于不处罚。
* 本文为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浙江省法学会2022年度法学研究重点课题“宽严相济政策下悔改考察激励机制研究”(2022NC16)的阶段性成果。
**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四级高级检察官[325105]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检察官[325014]
[1] 参见《全国第一道“社区服务令”》,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s://www.spp.gov.cn/spp/zhuanlan/201810/t20181011_39481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0日。
[2] 参见《宁波试点“附条件不起诉” 浙江省政法委:少说多做》,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0/08/id/42330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0日。
[3] 参见陈铁夫:《台江区检察院创新推出 轻刑案件诉前考察机制》,福州新闻网https://news.fznews.com.cn/dsxw/20191227/
5e0548c59a65a.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0日;刘立新、康锦:《亮点|河南郑州二七区:对轻微危险驾驶犯罪行为人适用社会服务评价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s://www.spp.gov.cn/zdgz/202111/t20211107_53469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0日;雒呈瑞、周賽、秦雪:《江苏南京江北新区:探索醉驾案嫌疑人参与公益服务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s://www.spp.gov.cn/spp/dfjcdt/202104/t20210419_51602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0日。
[4] 参见《广州醉驾也能从宽免刑引热议 反对者:变相纵容酒驾》,金羊网https://gd.sina.com.cn/news/2019-06-30/detail-ihytcitk861524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2月10日。
[5] 参见刘科:《 “法益恢复现象” :适用范围、法理依据与体系地位辨析》,《法学家》2021年第4期。
[6] 参见蒋秋玲等:《未成年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选择适用——基于观察方法的实证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2023年第5期。
[7] 参见王超:《荷兰检察制度精要及其启示》,《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