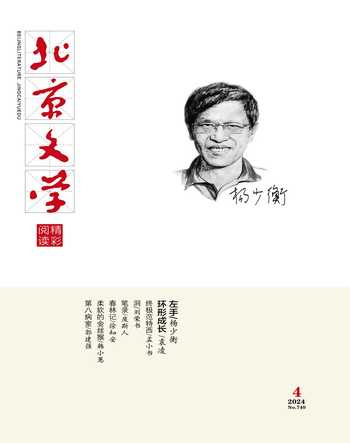春林记 徐知安
父亲因欠款而外出躲债,母亲到春林巷打工卖服装,“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与面馆老板王姨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小说展现了女性在落难时的友情与互助,行文有萧红《呼兰河传》之风。
一
父亲因为欠款逃离江北的那一年,我将将七八岁,从临河的自家厂房里搬出来,跟着母亲钻进了没有窗户的储藏室。墙角落里都是幽绿色的苔藓,白日里如果不开灯,跟地窖没什么区别,里头漆黑一片,总感觉从那嘎吱作响的木柜里会钻出什么不好的东西来。
房东是对中年夫妻,在菜市场卖鸡,每天早出晚归,三轮车的铁笼子里终日传来“咯咯咯”的叫声。浓重的鸡屎味被三伏天烘得像是炸了锅,祸害了邻近好几户人家,连母亲的自行车都未能幸免,几根鸡毛干成一片,黏在车座和车轮上,怎么都抠不掉。
男人出去躲债,那群债主又怎么肯罢休,受灾的自然是我们娘儿俩。我们像是地窖里的灰毛老鼠,只敢躲在黑暗中,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探出头来,摸两把米回去过活。天塌了大半,但日子还得过,母亲死死攥住将断未断的麻绳,颤巍巍地替我撑出条喘息的口子。
太潮湿了,床上的麻将凉席都发了霉,冒着深绿色,一块块密密麻麻地挤着,如同夏日里田间的水稻,一茬连着一茬。
“你爸赚了钱就回来了,你别瞎想,好好学习知道不?”母亲热得满头大汗,拿着把刷子,躬身跪趴在凉席上,吭哧吭哧地在院子里洗刷着,还不忘回头监督我写作业。我趴在凳子上,手里的铅笔在本子上画出一条竖线,像极了母亲发梢的汗水。
“会好的,你妈我是谁!别愁眉苦脸的。”她冲着我挥了挥沾着肥皂沫的刷子,笑着蹲在阴凉里,“写完了没,写完了过来帮我刷刷,累死你老娘了,再不刷完,今晚你就没得睡了。”
家里是不能待人的,无论是潮湿得恨不得拧出水来的被子,电灯产生的电费,还是只要见到门缝有光就来砸门的债主,都让我们惊恐不已。
为了还债,母亲拼了命,踩着她那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蓝色永久牌自行车在夜幕中穿梭来往。但就算生活已经糟糕成门前那摊臭水沟那般,母亲依旧会把自己收拾利落,衣服洗得一尘不染,坦然地骑上她的老“永久”,吱吱呀呀地往前走。
母亲在商场里替人家卖衣服,店铺不大,拢共几平方米,坐在塑料凳子上盼着来往的客户。这些小店一排排像是狭小的火柴盒拼凑在一起,连人都瞧不清。
本地人都喊这里是春林巷,算是这座江北小城的市中心。
这儿的物价很便宜,类似的商户不少,想要把从外头精挑细选的衣服卖个好价钱,母亲就得想法子吸引客人。每晚打烊后,她就坐在塑料凳上,一边拿着发小广告的送的廉价扇子给我扇凉,一边拿着小剪刀,眯着眼睛给那些新衣剪线头。
这一年,桌上“庆祝跨越新时代”的宣传海报还未褪色。夏日蝉鸣开始聒噪的时候,棚户们就陷入了巨大的难挨的境地。江北的苦夏是灼热且沸腾的,时刻冒着幽蓝色的火星子,将所有人包裹在巨大的铁锅中炖煮,连外头的柏油马路,踩一脚都能留下个印子。
太热了,汗湿了干,干了湿,最后生生沁在衣服上,留下了发黄的暗渍。
母亲卖的衣服质量好,款式也亮堂,对待客人更是十足的耐心,因此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她的工钱也涨了些,披着夜色载我回家的时候,偶尔还会哼歌。
“妞妞,脚抬起来,小心车轮子卷了去!”
“好!”我坐在车后座,仰头望着天上的繁星,右手環抱住母亲的腰,靠着她瘦削的脊背。深夜里母亲的短袖被风吹得鼓起来。
“下坡了,抱紧哦。”热风裹着蝉鸣,呼啦啦从我耳边呼啸而过,空气中都是啤酒烤鸭和炸串的味道,“饿了吧,回去给你做凉拌莴笋!”
母亲很喜欢张信哲,这是她自少女时代就喜欢的歌手,我也只听过她寥寥几次哼唱过《白月光》,只有这时,她才会露出少女的模样,眉眼里都是欢快。
她是北方姑娘,辽阔天地里开出来的花,在这片湿润土地上并不适应。江北的方言口音很重,哪怕我长到这个年岁,母亲也做不到完全听懂。父亲这边的亲戚并不接纳母亲,这方水土对母亲向来不友好,自父亲离开后更是愈演愈烈。而我能做的,就是坚定地同仇敌忾,仿佛只有这样,我才能用自己的法子捍卫她的尊严。
这座江北小城不大也不小,但我们也只来往于春林巷和家两处地方。春林巷不仅仅是一条服饰街,它背靠着市中心的幼儿园,纵深开去,分布着不少餐馆。每每到了午饭时刻,四面八方飘来的香气总能勾走我半个魂儿。母亲的饭都是起早做好带到店里的,一般就炒个蔬菜,垫巴在米饭上了事,但就算是这样,她也能做出极香甜的味道来。
衣服卖得多的时候,母亲会偷偷给我六块钱,让我去春林街后头去吃面。
我兴冲冲攥着钱,走几步就数一数,生怕弄丢。母亲应该也是很想去的,毕竟那家的大排面着实很香。
这条巷子很是繁华,小城的老饕们都知道,无论是陈记的鸭血粉丝汤,还是老张家的雪菜肉丝面,抑或是物美价廉的宣堡小馄饨,都是这酷热时节最好的慰藉。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春林面馆,那牌子更是响当当的。
与别家不同的是,春林面馆其实是个很小的店面,门头的牌子褪了色,远远望上去总感觉像是“日木面馆”。玻璃门上贴着几张食物图片,门口是个巨大的军绿色棉被做成的门帘,为的是不把空调的凉气漏出去。我用力推开那扇玻璃门,就是那股熟悉的酱香。
面馆其实不大,加上后厨统共也就几步路,六张桌子拥挤地摆放着,桌上也就一瓶镇江香醋和王姨自家熬制的辣椒,却能与那锅面碰撞出活色生香。
“来啦,找个位置自己坐,还加份素鸡对不对?”王姨的声音隔着送餐的栏杆远远传来,我忙不迭地点头,将手中的六枚硬币递给她。她笑着收起来,我就找了个离发黄的立式空调最近的位置,踮着脚感受昂贵的凉爽,恨不得打开裤兜,装两股捧回去送给母亲一道凉快下。
王姨的年纪比母亲大些,因为长期接触锅灶,身材并不纤细。她穿着万年不变的脏兮兮的围裙,热得脸都涨红了,单手叉着腰,用手拿着一米长的红木筷子搅动着锅里的面。沸腾时就舀一瓢凉水浇下去,蒸腾的热气撞在被油沁得发黑的玻璃上,化为一摊雾气。
厨房不大,几个一人高的大锅里咕噜噜翻滚着酱香味的大排和素鸡,还有熬煮着的鸡汤和雪菜肉丝、榨菜肉丝等浇头,等到水面下锅,酱汁打底,一把绿油油的小青菜,浸润着香油,放上浇头,点缀几根榨菜丝儿,一碗大排面就成了。
我早早备好碗筷,眼巴巴地望着里头。王姨不让我端碗,将面放在了我的位子上:“你别动,快吃吧,面不够再加!”说完,她顺手扯过一旁挂着的毛巾环着脖子绕了一圈,用力擦了擦脸上的汗,缩在收银台后头的矮凳子上,抱着磨损严重的搪瓷杯,舀了勺面汤吸溜吸溜就开始喝。
店里的空调是王姨不知转了几手买来的,空调叶片都掉了个七七八八,跟地头间劳作了一辈子的老汉一样,嗬嗬地喘着粗气。浓香滚烫的大排面一下肚,我头发丝里都是汗,拧一把能贴脸上。
王姨的本名,如今我不大记得了,只知道是江北本地人。她自己一个人撑着店面,做了许多年,慢慢有了些名气,用的食材都是顶好的,也没见怎么涨过价。她很喜欢小孩,总是纵着我们在她的店里蹭凉气儿,店里客人多了的时候,还会给我们买冰棍吃。
过了饭点,店里没几个人了,扒拉完碗底的最后一根面,我帮着王姨把碗筷放进池子里正准备离开,就见一个晒得快蜕了皮的棕黑色中年男人掀开帘子进了店。他的解放鞋踩在地上嘎吱作响,右脚破了个洞,露出的大拇指也脏兮兮的,啥话都不说,汗水从他的頭顶灌下来,脖子下方湿了一大片,活脱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伴着股馊味儿。
“找到了吗?”王姨猛地站起身。
“不曾。”
他摘下草帽,露出张国字脸来,满脸疲惫,走到最靠门的桌子边趴下就开始睡。
王姨也不赶人,回厨房煮了一大碗面,浇头码得高高的,端到了男人面前,招呼男人吃面。他动作迟缓地爬起来,将碗推给王姨,声音干得像破锣车:“你多吃点,我自个儿煮个青菜面就行。”
我离开春林面馆的时候,他抱着一海碗的青菜面,闷头倒了些香醋和辣椒,大口往嘴里塞。王姨含着泪,颤抖着从自己碗里把大排夹进了男人碗里。
屋里只剩空调的呜咽声。
这一年的梅雨季节尤为漫长,暴雨骤降,像有人端着盆子兜头浇下,整个屋子都无比闷热,如同廉价桑拿间,呼吸都被人捏住了嗓子似的,喘不上气。
人在逆境中总会想出许多法子来,母亲尤甚。
储藏室潮湿黑暗,母亲就用铁丝穿着废弃的被单挂在墙壁上,花色清新,权当窗帘。暴雨接着小雨,几乎没有停的时候,久而久之,储藏室的天花板都被泡囊了,青灰色的交界处很快渗透出水,淅淅沥沥的,越来越大,我和母亲便拿着各式盆放在下头接雨水,满屋都是噼里啪啦的声响。
外头下大雨,里头下小雨,我和母亲蜷缩在床上,头挤在一起仰头寻找“漏网之鱼”,别有意趣。
二
隔了几天再去春林面馆,熟悉的玻璃门关得死紧,一张白纸贴在上头,写着“有事闭店”的字样,我只好打转。
母亲给的钱虽不够吃鸭血粉丝汤,但足以去馄饨店买碗小份馄饨。后厨忙活着的夫妻很是和善,老板娘瘦得连围裙都松咧咧的,挂在脖子上直晃荡,手腕上的细银镯子微微泛黑。
“今儿吃点啥子?”
“一碗小馄饨,阿姨,能不能分成两份我带走呀?”
“成!你妈呢,咋不直接过来吃,塑料袋装过去都散掉了。”
“她忙哎,店里头都是人。”
“那你路上跑快点儿,泡沫碗柜子那里自个儿拿。”
角落里,白色的泡沫碗码得整整齐齐,一摸满手的塑料味儿。头顶的风扇慢悠悠地旋转着,细电线上都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因为房顶很矮,总有那一瞬间觉得这风扇会径直坠落砸下,顺道削掉我的头发。店里人不少,有男人吃舒服了,抬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抓起桌上的镇江香醋就往汤里倒。
“哎哟!你别倒太多嘛!酸不死你。”老板娘拎着俩被热汤快要烫化的塑料袋从后厨走出来,看到男人的动作,心疼得直皱眉头,却也不好多说啥,将塑料袋装好的馄饨递给我:“小心烫啊,那边有榨菜丝儿,要辣椒和醋就自己用塑料袋装。”
说罢,老板娘走到男人身旁,晃了晃半空的醋瓶子,拎到后厨往里头兑了点凉白开,她男人上前想说些什么,被老板娘一手推开:“包你的馄饨去!”
“听说了么,那面馆家的找到了?”
“啥子时候,我咋不晓得?”
“就昨儿嘛!说是苏州来的消息,有人撞见了,他家面馆子都不开了,买了票就去了。”
“侬说,能找着么,这都多少年了?”
“哎哟,算下的话,也得十三年了……”
我顾不得再听,小馄饨不能久泡,没几步路就变得囊兮兮的,除了那一口指甲缝般的肉,面皮都会化在汤里头。路过春林面馆的时候,玻璃上贴着的纸不知何时被人扯掉了半拉,残破地贴着滚烫的地面,上头还有个黑脚印,在风里发出脆响。
回到店里,我献宝一样将塑料袋盛着的小馄饨放进泡沫碗里。母亲放下正记账的笔,什么话都没说,塑料勺子捞起那晃荡的已经快散开的、可怜巴巴的几颗馄饨:“今天怎么买了两碗?”
“阿姨说今天馄饨店打折!可便宜了,我还装了榨菜!”
母亲笑着拿起桌子上的湿毛巾给我擦汗,什么都没说。
外头的世界飞速发展着,我和母亲的时光却是根燃烧着的蜡烛,缓慢往下淌。手机买不起,母亲巴掌大的小灵通被磨损得按键都看不清,她舍不得换,就那么糊弄将就用。处处都得用钱,每天晚上回到家,母亲就坐在床边一遍遍按着计算器。
“能还一分是一分,总有一天会还清的。”
江北的教育向来严苛,哪怕只是小学,家长们为了给孩子谋求老师更多的关照,也纷纷掏钱掏物,一时竟成了风气。一个学期总要交几次学杂费,有的老师还会定向要求我们购买资料当作业,价格都不便宜,十几张卷子就要三四十,还得统一交给老师来采买。
掏不出钱,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向同学借来资料,去学校门口的打印店,复印下来最多几块钱,我得意地抱着怀里发烫的试卷,凯旋回家。
久而久之,老师便对我有了意见,那个脸上冒着大痣的中年女人,指着我的鼻子就是一顿臭骂:“别人都买,就你特殊!用不起正版就别做,天天手抄作业才是你本事。”
那天,当着全班的面,女人拉扯着我的胳膊走到了外头的走廊上,书桌被撞出“哧啦”的声响,浓烈的阳光晒得我生疼,混合着教室里同学们注视的目光,搅得我无比仓皇。
“你妈手机号多少?给她打电话,让她把之前的费用都补齐!”
“我妈没有。”我嗫嚅着。
“什么玩意儿?大声点!”
“我妈没有!只有小灵通!”我仰头冲叉着腰的女人大喊,心里的委屈到达了巅峰,她明显没想到我会如此,眼角抽搐了两下,将手机递给我:“小灵通又怎么了,因为你我们班学杂费交不齐,侬个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把你家长找来!”
拨通时间尤为漫长,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温柔响起:“哪位?”
“妈妈。”我绷不住哽咽,心脏一阵发酸,“老师说,让我补教材费……”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每一秒都是她的为难。
“多少钱啊?哎呀没事,你跟老师说,明早给她,别哭了啊,好好上课。”
那天晚上,母亲回来得很晚,一脸疲倦地进屋,看到我醒着时笑了笑:“怎么还不睡?”
那只从地摊淘来的廉价包放在桌子上,她从里头掏出用黑色塑料袋包好的一沓零钱,坐在灯下细细数了好几遍。收拾完一切,她绑好钱,放进我书包的夹层中,借着昏黄的灯光翻开作业开始检查。
“妈妈,这钱你咋弄来的啊?”
“你王姨,还有小馄饨家的老板娘借我的,过几天我就还回去,你莫管了,快睡。”
次日的自行车上,母亲将防晒帽盖在我头上,大得像是个斗笠:“妞妞,咱不偷不抢,不丢人!该掏的钱妈妈掏得起,你好好读书就行,记住了没?”
“嗯!”防晒衣在日光里翻飞,我的心也腾跃起来,自由快乐地乘风而上,委屈一扫而空。
然而,这样的平静总是稀罕的。很快,那群人不知从哪儿知道了储藏室的位置,时常上门讨债,其中不乏我们的亲戚。明明是最亲密的血缘,此刻却蔓延成能绞杀树干的藤蔓,将母亲团团困住。
争执声嘶吼着,从夜深攀爬到了天明,母亲将我推出门,我懂她的意思,便摸着黑上了天台。头顶的瘦月都泛着冷色,并没有凉快多少。晚风都是烘热的,从左边的袖筒撞进来,又闯出去,蛮横得同下面那群人一样。
“他人呢,死哪儿去了?你不可能不知道!”
“今天不给个说法,谁都别想好过!”
“还钱!”
我躲在天台的墩子后面,向下望去,母亲被众人围在中间拉扯咒骂,她垂着头,眉目间都是疲惫和倦意,双手攥紧了衣兜。邻居终于忍无可忍地打开了门,母亲表情难堪,侧过头自欺欺人地用微弯的脊梁反抗着,她的视线与我撞在一块儿,蓦地偷偷朝我弯了弯眼角。
她依旧在笑着。
和日渐下沉的泥潭一样,母亲用尽气力扯著我,挣扎着妄图去够岸边的杂草,泥潭里一切可以支撑我们的,她统统不要命地抓过来,顾不得自己,垫在我身下,试图阻止我下沉,一遍遍告诉我:“会好的,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姑妈单手撑着腰,一如既往穿着她儿子的校服,在地里刨食刨了一辈子的庄稼人,脸上的晒斑又黑又红,她卷起宽松的裤脚,露出穿着黑袜子的解放鞋:“老五家的,我们也不想,可是他卷了钱拍拍屁股就跑了,屎谁擦?我和你姐夫也有俩娃,也得过日子啊!”
她抬起手背擦拭红着的眼角,我却看到她朝一旁的姑父使了使眼色,夫妻俩唱戏般,从母亲的包里扯出些零钞,嫌弃地撇撇嘴,走之前还不忘从兜里掏出印着超市名字的塑料袋,把桌上母亲为我做好的饭菜打包带走,电饭煲都倒了个空。
等人全走了,母亲才招呼着我下楼,笑着从公共厨房的柜子里掏出一袋子新鲜蔬菜:“我聪明吧,明儿给你炒新鲜的,电饭煲闷得都黄了!”
她全然不在意那群人的刁难,冲我晃了晃皱巴巴的塑料袋,昂扬怒放,跟野蔷薇一样,在所有人都加以恶意的岁月里,在我面前她都未曾萎靡过。
储藏室过于潮湿,自打住进来我就老生病。没过多久,母亲就带着我搬了家,新家是个毛坯房,沿街自建的“筒子楼”里最不起眼的一间。虽然面积小,一天最多能晒几小时太阳,但我们都很喜欢。
直到放学遇到骑着三轮车回家的王姨,我才知道原来她住在隔壁,连新家都是她推荐母亲租的。
三
因为春林面馆的生意,王姨每天天不亮就摸黑跑到郊区的菜市场,趸最新鲜的一批菜,再从城的最西头蹬四十多分钟车去春林巷开门,风雨无阻。我没见过她男人,曾听邻居饭后纳凉时讲闲话,说她男人姓周,在外头怕不是有了别个,只能守着个面馆讨口饭吃。
我不信那些谣言,偷偷告诉母亲那个不舍得吃大排面,自己煮了青菜面的汗淋淋的男人,母亲摸了摸我的头,侧头望着窗外淡淡地叹了口气:“都是苦命人……”
没多久,江北遇到了百年难遇的沙尘暴,铺天盖地的黄黑色倾覆而下,说句话满嘴的黄沙。水乡人哪见过这阵仗,慌得抱头鼠窜。母亲还在上班时间,我不指望她来接我,只好自己眯着眼睛跌跌撞撞地往回跑,像只被拦住去路的迷路小蚁。
路上的人站都站不稳,抱着头往前窜,往日十几分钟的路硬生生磨叽了许久。快到家的时候,我听到王姨隔着沙帘冲着我远远地喊:“妞妞!慢点跑,侬妈在找你!”
她的三轮车叮叮咣咣晃动着,她男人眯着眼,蹬着军绿色解放鞋,草帽被狂风吹得勒着脖子四处乱飞。王姨探出头,扯着用来盛菜的透明塑料布挡沙子,冲我用力挥手,越来越近。
“王姨,你望见我妈了?”
“望见了,她刚在校门口等你呢,人都走光了也不见你人,侬妈要急死了!”
“你这孩子咋自个儿闷声瞎跑咧!”王姨跳下车,将塑料布披在我身上,双手卡着我的胳肢窝,将我抱进了车厢里,“我先送你嘎去,等到了给你妈打电话让她嘎来,坐稳!”
三轮车晃悠悠地往家走,在天地的昏黄中,我焦急地够着脖子寻找母亲的身影,她应当只有黑豆那么点大,我总能听到她在呼唤我的名字。
撕心裂肺的呼唤声,沿着东城新村旁那条翻涌着恶臭藻类和死鱼的河,汹涌地穿破厚重的沙砾。
“妈!”我大声回应着。
母亲到家时,老“永久”都看不出来底色了,晃一晃,从车筐沿着把手,扑簌簌地像条沙蛇,一股脑倾泻在了地上。看到我安生坐在凳子上写作业,她脱了鞋,倒扣在垃圾桶里敲得“哐哐”响,哑着嗓子,兜头朝着我的后脑勺来了一巴掌:“下次还瞎跑吗!吓死你老娘!”
“不跑了,妈妈你别生气。”我从门后拿下毛巾,踮脚给母亲擦脸,她明显还在后怕,手颤得厉害,“饿了吗?给你做饭,蛋炒饭行不行?”
次日,黄沙席卷了一夜后终于消停下来,卷着无数枯叶厚厚地覆在目之所及的角落里,踩一脚都是“沙沙”声。母亲专门买了水果和牛奶领着我去王姨家道谢,大门是个灰白色的卷帘门,上头用红漆涂了个大大的“拆”字。
这边的房子普遍都是临街而建,前两年就传出风声要拆迁,刚开始,家家户户都开心疯了,掏家底摸裤兜地拿出血汗钱加盖,后头不知怎的成了泡影,拆迁没了音信,居民们也就歇了心思,徒留着一排没有被封顶的破破烂烂的水泥建筑。墙都不刷,反倒便宜了那群燕子,找到了闲地儿落了不少窝,时不时几条男人的裤衩被风吹得干巴,连带着衣架一同在天台的铁丝上晃荡,被烈日炙烤得几近褪色。
王姨满脸疲惫地弓着腰,向上猛提了下卷帘门,“哗啦”一声巨响,她半蹲在阴暗中,单手往上推着,眯着眼看到门口拎着一堆东西的我和母亲,“怎么这样早就来了,快进来!”
王姨她知晓母亲是北方人,便张罗着做顿饺子,砧板剁得震天响。与我和母亲租住的房子一样,王姨家也是个毛坯房,水泥凝固的粗糙,像是大片的磨砂纸,不小心撞上还会刺啦出一条血口子。屋里并不整洁,衣服和被子凌乱地团在床上,竹席都是滚烫的,枕头下散落着卷了边的厚厚一沓印刷的黑白照片。
“这么客气干啥,你带着妞妞生活也不容易,还买这多东西……”王姨的叹息声从外头飘过来,我没听清母亲的呢喃,紧接着就是一阵碗筷轻碰的脆响。
直到看到王姨家墙上挂着的那张被红笔圈了大半的中国地图,我才恍然意识到母亲话里的意思,比苦夏更苦的,是无望的等待。
王姨的儿子是在夏天丢的,那时他俩在国庆菜场里卖河鲜,蹬着黑色塑料鞋走在血污里,满身都是鱼鳞、鱼泡跟鱼鳃,腥味跟炸了锅一样波及一旁卖肉的摊子,引来密密麻麻的苍蝇。
夫妻俩忙着杀鱼,儿子还没铺位高,一崴一崴地踩着小三轮的脚踏子在菜场里晃荡。意识到孩子丢的时候,王姨和周叔刚杀完最后一条黑鱼,客人要求很多,王姨把鱼刺都剃了个干净,冲着外头喊了好几声儿子的名字都没应答,夫妻俩这才慌了。
王姨和周叔兵分两路,打了蹦蹦车沿着大路小路喊了无数遍,喊到整座城市的灯光亮起又熄灭,依旧找不到儿子的身影。也曾有几个人看到有人抱着孩子往外头去,但线索断了又断,最终也没个结果。
这次去苏州,夫妻俩兴冲冲地跑到男孩家中去望人,养父母自然不肯,王姨找人心切,強行闯进了家门,周叔更是和养父母吵嚷起来,差点大打出手,闹到派出所,王姨拉开男孩的短袖下摆,在男孩哭闹声中一寸寸白了脸。
他们的孩子依旧没能找到,只好蹬着三轮车,心灰意冷地离开了苏州。绕到兴化的时候,天边泛起鱼肚白,王姨盘腿坐在三轮车里头,眼前是缓缓后退的泥泞的路,一边是村庄,一边是荷塘,早起的男人戴着草帽,撑着船,硕大的舀瓢冲着芋头地泼水,哗哗作响。
王姨缓缓抱住头,冲着小路号啕,惊起了芦苇荡的鸬鹚。
这些年,王姨和周叔被命运反复捶打着,逐渐麻木,找寻成了既定的习惯,一口气儿吊着不上不下,人生仿佛只为找儿子活着。
王姨开面馆赚钱,周叔则负责拿着这笔钱去外头找儿子,哪儿有消息就骑着三轮车去哪里,钱舍不得花,几十块钱的廉价酒店更舍不得住。春秋还好,三轮车骑到巷子里,盖上被子幕天席地就能将就一晚,冬夏则分外难熬,只为了微弱的一丝可能。
吃完饺子,母亲跟王姨坐在卷帘门灯下聊了很久,时不时飞来苍蝇蚊子,王姨点了个蚊香放在她俩脚边,猩红的点缓缓褪成灰烬。说到伤心处,母亲搂住哽咽的王姨也落了泪:“姐,会好的,老天爷看得到,好日子会来的。”
自那天起,母亲跟王姨的关系就密切了许多,我去春林面馆“蹭饭”的机会也多了些,六块钱的大排面总会多点偏爱,还会有一小碟子的雪菜肉丝作为加餐,偶尔还能蹭上王姨做的扬州炒饭,搅上老干妈,吃完盘子里都是红油。她满足地坐在收银台后,笑着看我吃得一干二净才会放我走。
我再没见她哭过。
“妞妞,要笑,嘎懂啊?笑得好望,日子才能过下去。”
四
父亲逃离小城的第三年,一个个子很高,剃了寸头的男人敲响了我家的门。这个男人我是认得的,他跟我的母亲是本家,父亲还没出事的时候,他时常来家里做客,还让我喊他干舅。
“姐。”
母亲错愕地打开门,看到是他,忙跑去厨房给他做了碗疙瘩汤。母亲对他是有些愧疚的,一晚上聊了很多,最终在一沓合同上签了字。
这沓合同究竟代表了什么,时至今日我都不清楚。
梅雨季节即将过去,天气一寸寸凉下来,一场秋雨一场寒,人家院子里的葡萄都紫了,我扒拉着铁丝围墙,跳着摘下一串,兴冲冲地往回跑,母亲最喜欢吃葡萄了,我想给她尝尝鲜。
家里门大敞着,母亲不在,邻居看到我连忙探出头冲我喊:“妞妞,你妈被弄去法院了!”
我来不及思考,锁好家里的门,哭着往王姨的店里跑,天阴得厉害,我氣喘吁吁地冲着店里喊:“姨!借下三轮车!我去找我妈!”
王姨握着锅铲冲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踩着脚踏子往法院的方向去了。我个头很小,坐在上头是够不着脚踏子的,只能站起来握着车把,上下腾跃着在雨幕中骑得飞快,耳膜里都回响着剧烈的心跳声。好不容易到了法院,我通身都湿透,撂下三轮车就去找母亲,却见她坐在法院的台阶上团缩着脑袋发呆,我怯怯地站在保安室的屋檐下,隔着大雨望着她。
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我猜她在哭。
那时的我将将十岁,却平白生出了无数自责来。如果没有我,母亲不用这么拼命讨生活,她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本应拥有光明的未来,而不是在这异乡默默咀嚼吞咽着苦难,只为了给我一个未来。
她在成为我的母亲之前,首先是她自己。
生命有的时候是个顶奇怪的事儿,我简陋局促,仓皇得流不出眼泪。我潜意识里不敢让她知道我在这儿,转头蹬着三轮车晃回了春林面馆。
王姨着急地给我端了碗热汤:“喝了再走,不行我送你回嘎。”我冲着王姨道谢,淋着细雨走回了家,母亲面色如常,一如既往地给我煮了碗大麦粥。
粥的碱味很重,连同我的心一道沉在碗底。
母亲辞了她服饰店的工作,在房间里盘算了好几天,兴冲冲地跑去打印店打了不少传单,她眼里冒着光,兴奋地冲着我叽叽喳喳:“妞儿,妈有个好主意!”
那时江北学业紧迫,学生驿站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母亲大学毕业,给小学生补习绰绰有余,因而背地里做了不少功课,暗访了几家驿站后便带着我换了房子,买了些二手的桌椅板凳,拉个横幅,开始了她的老师生涯。
刚开始并不顺利,母亲不气馁,开始了“催泪大甩卖”,我也成了她的“童工”,一放学就背着书包站在学校门口,晃着传单嗷嗷叫喊。我学习很好,混上了大队长的职位,课间操检查各班卫生,便偷着把传单压在书本下,无形中也为母亲拉了不少人。
人多了,书桌磨损得厉害,夜深人静时,母亲便拿着木棒叮叮咚咚地维修,我坐在地上帮她递钉子和榔头,仰着头看她噘着嘴用力敲,满脸都是对命运的不忿和蔑视。
驿站越做越大,俩姐妹时不时冒出个想法,母亲也支持王姨把春林面馆做成招牌,在小城里开家分店。
“妞妞,你说,要是有一天,我儿能吃到我的面,他会有印象吗?”
“会!因为是妈妈。”
王姨什么话都没说,望着雨静默。
过了好些年,我们的日子才有了些起色,等把债务还完,我们便离开了江北,往北方去了。有了手机,小灵通被母亲收在了包里,后来再想打开,已彻底报废了。
与王姨便断了联系。
西北有着与水乡不一样的明丽,我在江北长大,度过了压抑的孩童时光,却在母亲的故乡得到了快乐,逐渐长成了少女。
再回江北,祖辈都已去世,我怀念那口酱香,跟着父母在回西北的前一天找到了春林面馆,老板已然不是王姨了,面也不是当初的味道,大排糊兮兮的,筷子一夹掉了个粉碎。我沉默地吃完这碗面,回头望着漂亮的门头,不由得想起了王姨。
也不知道她最后找到孩子没有。
责任编辑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