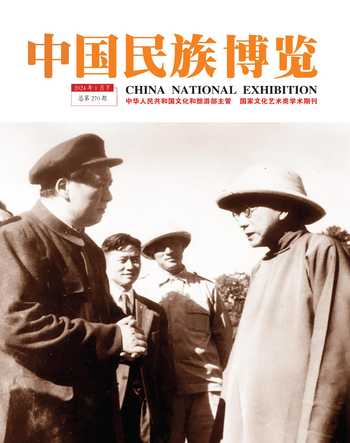站在“贴切”这一边

【摘 要】中国新诗是西方现代性在汉语环境中的本土表达,而汉字本身背负的历史语义和诗人难以磨灭的文化背景,使得新诗与古典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悠悠》与《好的故事》之间具有多重指涉的互文性,作者借古典文化中“境界”的概念,在幻想与现实的对比中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新诗批评的标准应当是内在的精神法度和自觉自律,在综合各种美学观点的基础上探索“每一首诗的标准”,也就是检验汉语对人生经验所进行的立象呈现,在“言—意”与“象—意”两方面是否贴切。
【关键词】《悠悠》;解析;批评标准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4)02—008—03
长期以来,古典与现代的美学观点一直是笼罩在中国新诗之上的结构性话语,尽管有不少诗作被指认为流露出了明显的古典气息,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两者的二元对立。尽管有部分学者曾提出过所谓“中西融合”的批评标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往往是将两种不同的解读视角随意组合。这不仅忽视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本质差异,也未能成功建立起一套合理可行的新诗批评方法。事实上,新诗的古典性与现代性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辩证关系,而1997年发表的《悠悠》,则通过多重指涉的“互文性”,形成了一个十分开放的阐释空间,或许可以为探究这一问题带来一定的便利。
一、站在虚构这一边
2001年,《站在虚构这一边》从暧昧性、诗学原理、诗意表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悠悠》。时至今日再读这篇文章,其“过度阐释”的嫌疑则越发明显。第一,文章认为“语音室”里的声音是一种“由无人在无地所说的一种无母语的配方语言”,是一种“来自设计和组装的、没有地方性和生活的超声音”[1]。不是说他所归纳的这些特征完全不存在,而是这些话语似乎可以描述任何一种音像制品。此外,诗歌中能表现“超声音特质”的只有“磁带”一种物品,但现实中的磁带录音并不是像文章所宣称的那样,能够将“所有与个人原貌、特质有关的东西都过滤干净、阻挡在听觉之外”[2]。作者本意应该是想通过超声音与原声之间的对立关系,来批判某种意识形态话语,但过于鲜明的主观性显然扰乱了他的理性逻辑,使其无时无刻不处于另一种反面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中[3]。第二,文章认为《悠悠》中的声音词(耳机、磁带、织布机)多以机械性来强调物的硬品质,时间词(秋天、怀孕、晚报、夕照)则多是虚化的、不及物的、非机械性的。而作为例外的“晚报”,经由他巧妙的逻辑转换,则成了“既指涉时间,又传出声音”[4]的现代性的“结合词”。不难看出,这种解读方法具有很明显的随意性和直线化,如果我们也采用这种牵强的分立策略,同样可以说“晚报”是时间和声音的“解构词”,因为它能同时进入双方的范围,又不受拘束地跳出。
欧阳江河善于对诗歌文本进行多角度的解读,认为《悠悠》“既是诗,又是理论”,但其过于强烈的理论意识也阻碍了他对这些视角的有机统一,而更多是一种模式化的分析。在他看来,《悠悠》中有两个互相背离的诗学方案被整合在一起:一个是“站在虚构这一边”,把诗的语言与意指物区别开来;另一个是“不用思想而用物说话”,把词投射到物体之中,并听任物象将自身穿透。欧阳江河还以此展示了笼括诗歌史的雄心:“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诗歌写作都是由上述两个诗学方案支配的。”[5]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悠悠》本身,可以发现这种雄心恐怕不是作者自身的抒发,而更可能是欧阳江河借以表达的个人诗学主张。从某些角度来说这种“怎么解读都行”的姿态很动人,但也难免让我们感受到其中话语的强硬和理论的刻意,甚至很容易沉溺于消费理论的快感之中。
二、互文性与虚构性
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采用西方的现代性逻辑来看待中国新诗中“情”与“理”的关系,则“前者很容易在反理性的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而后者也时常要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和灰色模式”[6]。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悠悠》的内涵,就不得不对中国新诗的身份归属和批评标准进行一定的探讨。如果略微了解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会知道对新诗的责难一百多年来都没有中断过[7]。即便是被作者视为“新诗开创者”的鲁迅,在1936年5月与阿德加·斯诺的访谈中,还对当时已发展了二十年的新诗嗤之以鼻。一些古典主义学者认为,对民族文化的广泛认同和深入了解,是进行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但当代新诗在形式和思想两方面都充斥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刻意追求。这导致新诗创作陷入“越是生产,越是缺乏创造”的怪圈[8]。
中国新诗创作存在着对西方理性文化的大量接受,这是个毋庸置疑的命题。事实上,尽管中国当代新诗在客观上与古典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能因此将其看成从旧体诗词中分离出来的支流。因为与诗、词、文、赋等具有内在演变关联的传统文体不同,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和巨大政治变革的催化,中国本土社会基本不可能诞生“新诗”这个与传统审美模式大相径庭的的艺术门类。因此,要将其看作西方现代性在汉语环境中的本土化表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诗批判就应该采用纯西方的美学观点。因为作为长期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的产物,构成新诗语言的汉语文字不可能完全剔除身上所背负的道德意识和历史语义。他认为诗人的使命在于“发明一种新的汉语体系”,以此保留古典文化中那种“圆润流转与精神气度”[9]。《悠悠》这首诗也充分体现了汉语“离心力与向心力的统一”,是以“洋气”的姿态来呈现“古典”美学的优秀尝试[10]。作者力图超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熟练使用古典与现代杂糅的诗学手法,使得整首诗作既充斥着光怪陆离的诗境,又坚守着古典文字的清纯唯美。
此外,尽管消除附加在诗歌物象上的抽象语义是90年代诗人的集体意识,但人类思维终究无法跳出固有的文化背景,有些诗人甚至对古典文化怀有某种崇敬之心,他将鲁迅视为“诗歌现代性”的先驱,认为《好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诗意的视景”[11]。欧阳江河也提到了《悠悠》中“好的故事”与鲁迅文章的互文性,可惜出于理论话语构造的目的,他未能对这种互文性进行深入的阐释。事实上,鲁迅的《好的故事》中并没有生动曲折的情节推演,而更像是集合了发生在家乡绍兴郊外的古驿道——“山阴道”上的一些梦境片段。文中提及的《初学记》引《舆地志》云:“山阴南湖,萦带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镜若图。故王逸少曰:‘山阴上路行,如在镜中游。”因“兰亭修禊”的缘故,“山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源远流长的民俗性”[12],并在杜甫、陆游、王义山、袁宏道等后世文人的笔下不断流传与发扬。而鲁迅在《好的故事》对“山阴道”的诗性改写,无形中又完成了典故形象的现代性转变,使其逐渐成为人们心中代表江南美好风物的一种历史积淀符号。到了《悠悠》这里,抒情的文化主体被降格为虚构的语言主体,且进一步抽离了其中的特殊内涵,最终只留下了四个字“好的故事”。对于作者来说,他无意于追求古典文学中“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境,而更像是用魯迅的“好的故事”来填充诗歌的虚构性,以此完成一场“虚构文本的个性表演”[13]。
三、“每一首诗的标准”
以往关于新诗批评标准的讨论,之所以很多时候会沦为两种诗学话语权的争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古典”与“现代”更多被看作两种相互对立的诗学体系,并在各自的理论范围内探索知性概念下的理性标准。事实上,这些以知识形式存在的标准,虽然具有衡量诗歌表达形式和表现对象的功能,但其本身确是非决断性的。新诗批评的标准应当是其内在的精神法度和自觉自律,也就是在综合各种美学观点的基础上探索“每一首诗的标准”的可能性,检验诗歌在“言—意”与“象—意”两方面的贴切[14]。例如,“用典”可以成为诗歌的一个参考标准,用来衡量诗中用了哪些典故、如何使用这些典故等。但不能仅仅以“用典”来判断一首诗的优劣,更不能让“用典”经由某些所谓的权威而进入主流批评话语。因为无论设立理性标准的理由多么充分、动机多么纯良,对于新诗的创作而言,事实上都会构成一种外在的限制。
欧阳江河认为《悠悠》“意在描述某种意指中心的空缺和扩散”[15],这一解读虽然根植于现代语言学理论,但却并不能令人耳目一新,只有对那些不太熟悉西方理论的读者才会有醒目的效果。事实上,从诗人柏桦所作的《张枣》一文中可以得知,《悠悠》写于1977年德国图宾根森林的边缘,是作者“在回忆中写他15岁读大学时的良辰美景”。再结合其旅居国外的人生经历,我们或许可以把这首诗看作是他以现代生活经验对中国古典文化中“境界”一词所作的诗性阐释。与《好的故事》一样,它们都有一个“现实——幻想——现实”的精神远游,都在美好幻想与生硬现实的对比中,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其实鲁迅对于故乡的态度本身就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对古典文化中的凋敝、落后、愚昧持有否定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在都市漂泊中将“乡愁”作为抵挡社会黑暗的精神家园。很难说那个时候的作者会否认自己与鲁迅在情感上的共鸣,他们都写下了无法治愈的“好的故事”,且都发生在“黄昏”这样一个夕阳无限好的时节。
中国诗歌的“古典性”与“现代性”是个很值得探究的话题,而张枣的诗融合了中西诗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考察对象。但可惜的是,如今的新诗批评似乎陷入了某种怪圈:从内部来看,对批评理论纯正性的追求,使得新诗批评越发成为一种专业化和小众化的行业;从外部来看,当前学界对古典与现代的辩证关系思考甚少,抑或被两种诗学流派作为“不言自明”的问题而忽略。本文无意于提出一套诗歌批评的正确方法,但如果我们将古典与现代的美学体验看作诗歌的共同内涵,或许可以将批评的标准大致表述为:汉语对人生经验所进行的立象呈现是否贴切。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短暂、特殊、过渡的美,而从中提取出的某种永恒性,又会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经典的美,这就是波德莱尔所提出的“美的双重性”。再看《悠悠》这首诗,作者将风尚、道德、情欲等因素压缩到了最小,现代性仅是为故事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场所。而古典性则更多成为一种共时性的表达,与现代性一起以并列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歌的神秘难解。
参考文献:
[1][2][4][5][15]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一边[J].读书,1999(5).
[3][14]杨金彪.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D].南京:南京大学,2015.
[6][8]刘士林.“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7]朱钦运.汉语新诗的“百年滋味”——以来自旧体诗词的责难为讨论背景[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8).
[9]万夏,潇潇.后朦胧诗全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10]赵飞.“言志”工夫合一——论张枣诗歌的语言本体观[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1).
[11]张枣.1919年以来中国新诗对美学现代性的追寻[D].图宾根:图宾根大学,2004.
[12]王东东.中国新诗的古典性与现代性——以张枣《悠悠》为例[J].东吴学术,2019(5).
[13]于川.试论张枣诗歌中词语的暧昧性——以《悠悠》为文本[J].大众文艺,2017(3).
作者简介:季钰(2003—),男,汉族,江苏泰州人,本科,蘇州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