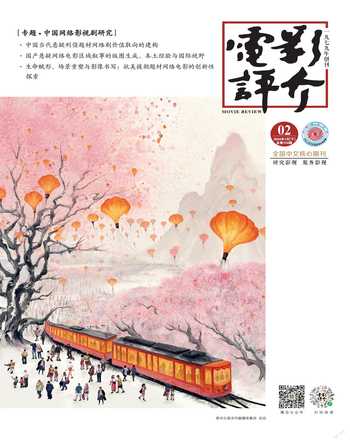城市电影“风物”修辞下的隐秘叙事
章龙 张仲阳

城市对于电影意味着什么?通常情况下,城市仅仅是电影叙事的发生空间,就如戏剧舞台上的布景一般,总是承担一种辅助的功能。然而,在建筑研究中,对“风物”的关注却为人们理解电影中的城市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学者马援指出:“‘城市风物是打开一座城市历史文化意义的标签,它刻录着一座城市远古今朝的发展过程。城市风物是活在当下的历史,是时空叠加的沉积;它不是孤立的、无结构和无序的,而是被一串串联动的空间隐喻符号以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或是艺术的方式相互交织而凝结在一起。某种程度上,从风物层面叙述城市,实现了多层次、立体化复原城市的真实风貌。”[1]在这一视角下,城市不再是冷漠的布景,而是时刻通过风物,诉说着在它身上所发生的历史与故事。电影对城市风物的表现,也不再仅仅是作为叙事背景的呈现,而是企图通过城市风物的独特意蕴,打开重叠在城市之上的爱恨情仇。由此,城市风物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德勒兹意义下的“褶子”[2],而城市电影则旨在通过镜头蒙太奇的呈现,重新以电影再现的方式,打开褶子覆盖下潜在的情感现实。
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维托里奥·德西卡,1948)为例,该片呈现了大量描绘城市街头景致的镜头,但这些镜头对城市的表现,仍仅仅停留在对一种现实主义的追求和需求上,即力求树立真实的城市面貌,为叙事的发生和上演提供空间和场域的情境。与此不同的是,城市风物是通过生活在这里的人,来展现城市空间环境与精神风貌的融合,将人物作为城市的背景,以表现城市当下生活中的过去与未来。从这一角度来看,城市风物便是通过呈现城市中的人,发生在城市中的事件与城市中的风俗之间彼此交织而缔结的关系,建立起传统叙事之外的充满隐喻和想象的叙事关系网。由此来看,城市电影在这个基础上表现出强大的内在能量和驱动力,体现了与当下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联系,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根植于城市文化特质的叙事结构。因此,在这一视角下重新审视日本导演今泉力哉的电影,自然而然也便可以开启一个全新的理解纬度。
在今泉力哉的镜头之下,作为东京文化地标的下北泽成为《在街上》(日本,2019)叙事中的“隐秘主角”。纵横交错的小道,琳琅满目的各式店铺以及三三两两穿着奇装异服的年轻人等,共同在镜头中构建出下北泽的日常图景,这也体现出金泉力哉一贯性的导演风格,其所展现的并非是一种固定的叙事主题,也不是就典型事件所展开的叙事内容,如今泉力哉在《爱情是什么》(日本,2018)和《一首小夜曲》(日本,2017)中表现的一样,是一种充满“城市风物”感的都市氛围。注入风物的城市电影将城市中的不同结构以符号化的文本形式注入叙事当中,当“叙事”与“城市风物”相互作用时,不仅突破了影片叙事中的时间限制,更进一步展现出作为城市而存在的历史记忆的别出心裁的活力感,从而赋予影片内容更多的人文情怀与生活气息。在这一视角下,叙事不仅是以城市风物作为叙事空间的承载考量,更重要的是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为视角展开故事。具有风物姿态的电影叙事不仅赋予情节以更多活力,更是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感知,最终呈现出一种与电影文本并行的人文景观和视觉文化图景。
一、城市电影中风物的叙事视角
影片《在街上》的叙事主体是对生活在下北泽的年轻人的情感关系的讲述,并用出轨的主题构成叙事的主要线索。从叙事角度来说,这一对情感关系的表达并不成功。镜头大量地描绘了玲琅满目的古着店、奇装异服的年轻人、破败的小酒馆等城市生活景观,并没有清楚的线索交代几个青年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影片如散文一般,大量生活场景的描述置换了本该作为行动主体的人。正如影片题目所提示的那般,影片人物更多不是为了表达都市青年的情感主题,而是企图通过都市青年日常生活的情感,重构下北泽的城市空间。由此可见,空间从原本背景的位置转而成为情感的主要载体。“人”的故事被“城市”的故事替代,今泉力哉由此展开城市电影内风物的独特叙事视角。
从定义上来讲,城市风物不仅意味着城市中的空间延展,而且也是展现城市人群长期生活方式的手段,由此传递出城市发展中人与空间的二元关系。显然,在当今的城市电影中,已经离不开对于城市风物的描述,围绕着城市的叙事已经不能离开人而言物,也无法脱离物而状人,人与物之间已经成为互相填补意义的生活共同体,承载着难以言喻的情绪意义,成为搭建城市电影内在的聚合系统。相聚、离别、欢乐与悲伤,这些城市人群在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情感皆以内嵌的方式蕴含在城市风物符号化的表达之中。通过这一叙事逻辑,以《在街上》为代表的城市电影铸造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即通过叙事构建起城市風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从符号文本上实现对于城市结构的解读,也为观众认识城市文化搭建了一条途径。综上,以城市风物为切口构建的电影叙事主要有以下三层叙事视角。
(一)城市风光:城市结构与延展所体现的城市外貌
城市的地貌与风光往往是影片自最浅显层面所要呈现的。以《在街上》为例,镜头跟随着主人公行走的轨迹,将下北泽的街道、商铺、娱乐场所、局面住宅等城市外貌一一呈现出来。以影像直接再现的形式,摄影机“机械的眼”如实地记录着下北泽的城市样貌。通过蒙太奇的形式,观众可以借影像场景的直观表现,再现下北泽的生活样貌。于是“电影”以观看的形式,带领观众以“缺席的在场”[3]的方式,领略下北泽的城市风光。
(二)城市物产: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所生产的特殊物品
城市物产是影片呈现的空间关系所带来的。下北泽因其众多的二手古着店与独具特色的小酒馆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成为日本的“亚文化天堂”。在影片中,穿着各异的年轻人与他们相遇的酒吧、商店、街道,共同构筑了这一“亚文化天堂”的特色地域景观。下北泽也因众多的展演空间而被冠以“戏剧之城”的名号。影片开场不久,有一组镜头是主人公荒川青看完演出后在街上夜游,逛至小剧场海报前发呆,随后与闯入的警察进行一段没头没尾的对话,这个片段对于叙事而言似乎仅仅是路边街头的陌生人之间没有意义的搭讪,但本质上这段叙事既是以象征性的影像符号营造出那一时期日本青年的理想和对现代生活的愿景,又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对文化层面的新型社会空间的呈现和生产,表现出日本现代社会文化的角力与变迁。
(三)城市习俗:特殊的人际关系缔结与维系方式
这种特殊的表现内容展现了现代城市电影中叙事方式的转向,从单一性的城市描述转向内嵌式城市景观的具体显现和与之相配的文化叙事逻辑。[4]所以,将人物行为逻辑与城市风物联系在一起可以展现出独特的叙事视角,并有效地将城市特质中的风土人情进行连接,实现具有历史沉淀感的空间生产,由此彰显城市与城市产生的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街上》以男主人公荒川青的步伐与视角作为主线叙事逻辑,从家中到古着店再到咖啡馆,随着男主人公步伐的不断前进,下北泽在电影中的全貌也在不断地展开,在其中生活的各式男女的故事也得以体现,从相识到分离,从交集到离散,最后又全部随下北泽的人流而去。这些若有若无的人际关系随着下北泽不同城市空间的叠加,错落有致地分散在电影叙事之中,带有一种模糊而又难以言说的观感,就如同下北泽街头无缘由冒出来的奇怪路人。从中来看,《在街上》的城市风物叙事视角形成“城市风物”与“人”的互动关联所缔结而成的符号意义集合。
今泉力哉在电影中将“城市”与“风物”相联系,使之成为一种可以通过观感产生认知的结构,更是一种可以以符号所展现的隐喻叙事视角。下北泽在今泉力哉的镜头下不仅体现出独特的空间布局和结构秩序,更是展现出在区域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传递和延续着城市空间与居住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一种独特风貌。这种风貌不仅仅是作为叙事背景单独存在,而是融入电影文本之中成为叙事之内的叙事。从《在街上》来看也是如此,这部电影几乎没有叙事主题,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叙事的主题是依靠下北泽的独特城市风物才得以建構。音像店、古着店、咖啡馆、小剧场以及形形色色各类小店形成下北泽独特的气氛与气质,同时也为电影中的叙事做托底,成为影片中各色男女人际关系的注脚,实现物理意义上真实空间的再现和生产。因此,这也让电影中人物关系、场景以及话语文本的反复拉扯和试探有了新的形状,在此之上构建出的男女关系显然充满了颇具微妙的魔力,为观众的观感给予难以言说的赋形。
二、城市电影中风物的叙事方式
利用符号化的表征展现城市风物是城市电影独特的叙事表达方式,《在街上》的镜头中呈现的咖啡馆、剧场与小酒馆不仅作为叙事场景,还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征物和一种独特标记来展现城市生态与城市文化的精神,同时,也是叙事中人际关系表达的补充。因此,《在街上》也自然地呈现出三种叙事表现的特点:
(一)去中心化的叙事表达
随着全球社会的发展,巨型都市纷纷拔地而起,但从现在的城市电影叙述表达来看,原先对城市的恐惧或者自闭式的表达精神已经出现转向。以城市电影的特质为出发点进行追溯的话,无论是从城市空间表达来讲,还是从城市文化记忆的角度来讲,均会发现一种去中心化的表达逻辑。[5]也只有在去中心化的叙事表达过程中,城市风物所展现出来的独特姿态才能够一步步地体现出来。这种表达方式打破了原有的电影叙事框架,转向一种多视角的叙事方式——他者视角下城市生活的多姿多彩。所以无论是伍迪·艾伦的“欧洲三部曲”(《午夜巴塞罗那》(西班牙/美国,2008)、《午夜巴黎》(西班牙/美国/法国,2011)、《爱在罗马》(美国/意大利/西班牙,2012)),还是是枝裕和的《幻之光》(日本,1995)、《步履不停》(日本,2008)和《海街日记》(日本,2015)等电影,均从城市空间与生活实践的角度出发,构建出具有城市风物情节的叙事表达,这一范式也足以从叙事表达上影响城市电影的表达张力。在这样的创作方式中,城市风物一方面展现着社会进程下城市中人物关系的演进,一方面又以真实的城市文化为基础为影片注入交互式的叙事场景。《在街上》的镜头总是在一个又一个场景中穿梭。人物的对话与行动不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叙事线索而行进。与此相反,《在街上》调转了人物与场景的关系。人物在场景中的行动不再为固定的戏剧目的而服务,而是仅仅作为场景的注脚,是对场景的解释。该影片借人物在场景中穿行,场景与场景之间产生关联,制造了别有意味的去中心化的独特叙事效果。
(二)形象化的叙事呈现
从理查德·霍加特的角度来看,城市生活显然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需要从邻里关系、家庭和城市地域角度序列来进行考量。从公共舞台到幕后活动的空间化转换中,“邻里有爱”“温暖帮助”等诸多阶级品质也在场景的不断变化中得以展现[6],“物”与“人”也得以交互,共同勾勒出在城市中生活的文化景观。显然,城市电影中的人与物并非横平竖直般的整齐罗列,而是在交叠演进中动态前行,城市空间、城市物产成为叙事人物的灵感与对话文本的注脚,叙事也借由城市空间、城市物产的印象与记忆激发出全新的关系角度,由此产生全新的城市电影美学显现。借此,城市风俗得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也为城市电影叙事提供了帮助。由此可见,形象化的城市电影符号——不论是公共设施抑或是私人领域,均通过叙事的不断转变,成为情景合一的都市特征。在此,电影中的城市空间也脱离了原先外在物的特质,成为承载城市风俗的意义载体,形成叙事与城市之间的双向互动。因此,对城市风物的表达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城市电影中对于城市形象的单方面描写,另一方面则打破了利用城市渲染叙事的手段。当今的城市电影采用一种兼容模式,将情景与空间叠加结合在一起,建立了城市风物与文化生活图景式的形象化叙事。《在街上》通过对主人公生活场景的营造,以空间中的人物重新塑造了空间的独特形象。古着店的拥挤与零碎,小酒馆的温馨与逼仄,咖啡馆的文艺景致通过其中的年轻人,构建了自己的空间形象。
(三)潜在化的叙事表征
城市风物不仅仅是符号化的、物化的外在体现,而是联系着人们记忆、想象与对比的外在表征符号,构建了人们对于一座城市认知的整体。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城市中内涵多元的文化场景显然是对于历史痕迹的表征,在复杂的文化场景之中,城市内的多种文化符号不断冲击、聚合与叠加,产生了独特的效果。[7]城市风物构建起一套想象系统,这类系统通过内在联系立刻调动观众的感官,利用叙事中不断展现的城市风物,使观众可以将对电影中城市风物的感受与脑海中的城市记忆叠加在一起,进而联系叙事进行信息的接受、解码与反馈,形成对于叙事的不同理解和再表达。[8]从电影开端起,《在街上》便将城市风物与人融合在一起,男主人公是独来独往的古着店员,头顶乱发,背着大背包,朋友寥寥喜欢独来独往,在与女友分手的不甘心中,伴随着独特的背景音乐,一头扎入下北泽的街道丛林之中。在这个街区之中,他遇见了在人声鼎沸的餐馆中专心吃拉面的短发女孩、在转角处碰见了暗恋自己侄女的中年警察、从作家转行做演员的酒吧常客、总是陷入情感纠葛的打工少女……《在街上》的成功之处便是脱离了单纯指涉地理空间的城市叙事,而是使观众体察到如何言之有“物”且其“行”之有效地生活在城市生活当中,进而展现出下北泽独特的地域气息和人文情怀,为电影叙事的内核提供了潜在性提示。
三、城市电影中风物的叙事隐喻
颇具隐喻感的视角是创作城市电影的主要手段之一。城市电影中对城市风物的独特表述,并非仅仅是对城市规划的展现,更是以城市空间为载体体现城市气韵,让观众在通过隐藏视角观测敘事的同时,也可以体验到独树一帜的愉悦感。今泉力哉利用下北泽的城市风物建构起一种具备符号隐喻感的视角,从而展现生活在其中的各色男女以及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距离。
(一)情感想象与城市精神
随着男主人公不断游走在下北泽各种地标的过程中,男主人公与其他角色的关系得以建立与展开,所表现的也并非是对下北泽地理位置关系或者单一的城市中人物关系的描写,而是呈现出嵌入城市景观中具体的、直观的与具备体验感的文化叙事,进而将“人”与“风物”结合在一起。独特的下北泽风物也成为《在街上》人物关系发展的叙事内容,各色情感“怪相”也在其中得以展现——男主人公的女友理直气壮地喜欢另一人,女大学生明明喜欢前男友还投入一段新恋情,女顾客满怀怨气地帮助心上人挑选适合约会的服装……像电影中“感情的事情说不清楚”一样,在以男主人公为中心的感情关系中,弥漫着一种由下北泽这个街区所体现出的一种独特的不确定感,这实际上也表现出导演对于一贯以城市刻板印象作为叙事核心的创作方法的一种挑战。
从情感体验上来看,《在街上》展现了下北泽生活的普通年轻人,他们一边渴望与陌生人产生交际,渴望陈述表达,渴望被看见,一边又沉醉于个人的自我世界,同时也在一遍遍的实践中体会着希望反复落空的失重感。下北泽街道的光怪陆离,使得生活在其中的男女难免产生漫无边际却又期待实现的想象。细究之下,这般想象也仅仅是独居状态下的自我疏解与多余的心跳时刻而已。但今泉力哉所展现的这般细腻情感与下北泽的独特街道风貌联系在一起时,“人”产生的“情感”与“城市”诞生的“风物”便有了更多的共振,如同咖啡馆中一桌人谈论着维姆·文德斯,另一桌人却分享着漫画体验,今泉力哉镜头中所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由下北泽产生的迷离感,人物叙事与城市风物叙事一起成为一种单纯的风景,保留了当下青年人的敏感与自持,也展现了街道中转瞬即逝的瞬间和亘守的不变。包裹在城市钢筋混凝土外表下的隐秘情感,被镜头经由人的行动而打开。人与空间借“城市风物”共同营造了下北泽的情感空间,为潜在的城市情感与记忆,找到一种具体的、可见的载体与依托。
(二)景观人文与城市文明
在承载情感与想象的过程中,下北泽颇具城市意味的符号标记和现代人际关系交织在一起,强调着城市关系中的人情冷暖,体现了独特时代背景下的人文景观。城市电影中的风物将城市的街头巷尾和各色人群紧密联结,彼此观照,互为镜像。在镜头的切割和重组中,电影对城市进行记录和重塑。《在街上》的叙事隐喻中,今泉力哉将城市风物特质注入到影片人物关系上,利用人物与城市空间的构图,营造出城市中文化的展现方式与人文情怀。与此同时,《在街上》还利用叙事形式将城市特质与潜质进行详细表达,调拨传递了空间与人文的互动符号,以潜在叙事的方法展现一座城市颇具美感的形式主体,体现城市发展中人际关系变迁的母题,并从多种场景下人物对话文本与人物关系的变动中展现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总体风貌,由此完成对传统城市电影以地理坐标连接观众记忆的一次挑战。所以,《在街上》的“在街上”是一种独特状态,随着男主人公的兜兜转转,上行下行,情感与风物的结合带来了有趣的叙事观感——街道空间成为共享体验,对话随处可以展开,对峙随时可能发生……当相遇、相知与交流的展开完全嵌入到街道之中时,“在街上”所体现的更像是一种在独特城市氛围叙事下的寻找与希冀。
结语
需要强调的是,城市风物不是城市电影的展现主题,而是作为叙事内部的逻辑关系进行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人物在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与情感逻辑。《在街上》这部电影中,城市风物内化为一种沉浸式叙事表达手法,体现出下北泽居住者与这一城市区域的密切关系,强化了城市与居民在人文情怀之间的强烈羁绊。城市空间、城市物产与城市风俗共同作用,体现出独特人文精神与文化内涵,显现出一所城市独有的历史与文化气息。由此可见,城市电影离不开对于城市风物内化与表征的思考,在叙事中尤其需要体现城市精神风貌对于电影叙事视角与方式的影响,而城市风物正是可以将城市潜藏的文化底蕴与空间符号表征进行结合的有机体,从而形成一种颇具隐喻感的叙事风格,最终构建出美妙而又和谐的电影诗篇。
参考文献:
[1]马援.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 J ].探索与争鸣,2021(05):169-176.
[2][法]吉尔·德勒兹.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M].杨洁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5.
[3]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213.
[4]叶治安,张炜,许晓敏.日本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经验与风物观察[ J ].上海城市管理,2016(03):6-9.
[5]路春艳.城市电影:关于城市的想象与记忆[ J ].北京社会科学,2008(02):76-80.
[6][英]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M].许冠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4-40.
[7]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76-81.
[8][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1-13.
【作者简介】 章 龙,男,山东德州人,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电影叙事、电影跨媒介、戏曲电影研究; 张仲阳,女,河北邯郸人,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戏曲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