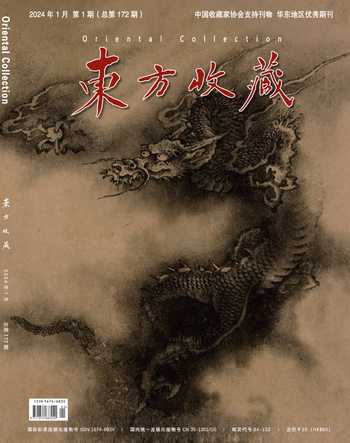从凭几看西王母仙境人间化
摘要:在以西王母为题材的汉画像石中,有许多具有神异性质的物象围绕着西王母,但也常常发现她凭几而坐。为什么会在西王母的神话世界中出现一件具有人间性质的家具?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凭几的使用、西王母的形象和地位等来探讨汉画像石上的西王母仙境人间化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凭几;西王母仙境;仙境人间化
一、凭几
《说文解字·几部》载:“几,踞几也,象形。”几有多种类型,既有放置物品的庋物几,也有供人凭坐的几,后一类通常称作凭几。凭几作为中国古代供人们倚靠使用的一种家具,其设计自然要符合人体工学,因此通常以形体较窄且高度与坐身相对侧靠或前伏为宜。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多为漆木几,一般由几面、足和底座三个部分榫接而成(图1)。
凭几的使用由来已久,其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成为重要场合中的必备之物。根据《周礼》的记载,在“大朝觐”“大飨礼”“大射礼”以及分封诸侯时的礼仪场合中,家具的摆放是非常有讲究的,黼依、席和几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都有各自的布设顺序。
此外,汉人重孝,有崇老习俗,儒学思想也强调孝悌观念和等级思想,这对汉代凭几的使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亲族宴饮聚会,为表示对年长者和身份贵重者的尊重,都会授其以凭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曰:“上赐淮南王几杖。”《礼记·曲礼上》记载:“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器物丛谈》中更是说几“非尊者不设”。贾公彦也说:“左右玉几唯王所凭,雕几以下非王所凭。”可见在汉代,作为“辩其位,与其位”的凭几,一般是身份尊贵的人或是年长者才能够使用,并非任意人家都可以使用,且帝王将相所使用的凭几在材质上也有区别,以显示使用者的地位和身份。
以上说明凭几自古便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至于汉代,凭几的陈设仍要分长幼尊卑,非尊者不能用。
二、西王母仙境
有关西王母的神话传说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成书的《庄子》,此时以长寿为主要特征的西王母信仰已经形成。
进入汉代,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逐步强盛,经济和社会生产力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此外,统治者推行以“孝”和“三纲五常”为主要思想的儒家文化,使得厚葬之风开始盛行。汉代人为使逝者能够继续享受生前的物质生活,也为自己能够得到先人的庇佑,于是给予其华丽的墓葬装饰,画像石这类丧葬艺术便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有利的发展机会。
在时人眼中,西王母已发展成为掌握不死之药的神灵,这恰好与汉代人渴望长生的观念不谋而合,于是便出现了丧葬艺术中大量以西王母为题材的场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画像石全集》中以西王母为题材的画像石就有88块,远远超过其他同类型题材的画像石。
在这些西王母画像石中,羽人、九尾狐、蟾蜍、玉兔等具有神异性质的物象围绕在西王母身边,共同构成了西王母仙境。
羽人即身长羽翼的仙人,其所拥有的羽翼使其能够自由地飞翔于天地之间,象征着长生不死。羽人是汉画像石上仙人的代表之一,其作为一种类型多变且行为多样的飞仙,既异于常人形态,又远离人世间。同时,在画像石上刻绘的羽人形象,反映的是时人渴求灵魂不灭以致升仙的愿望。
九尾狐的造型近似于常见的狐狸形象,体形修长,多九尾。东晋郭璞认为吃了九尾狐的肉就能远避妖邪、百毒不侵,具有辟邪的作用。此外,尾代表生殖力,九尾意味着子孙昌茂,所以古人将九尾狐视为象征子孙繁衍生息的瑞兽。
兔和蟾蜍虽保留着大部分原生形象,但后肢直立,前肢则常常呈现捣药状,兔和蟾蜍自古便与长生不死联系在一起。原始先民认为蟾蜍鼓起的腹部如同妇女怀孕时鼓起的腹部一样,具有繁殖能力,并认为蟾蜍的习性与月亮的阴晴圆缺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兔子的繁殖能力也很强,孕育周期则与月亮的盈亏圆缺周期相对应,二者皆为神性动物。所以才有了宋代诗人陆游《董逃行》描述的场景:玉兔捣药,由蟾蜍搓成药丸,服此药便可成神仙。
这些拥有神性的物象围绕在西王母身边,并在西王母仙境中承担着一定的职能,共同营造出了一个汉代人想象中的美好而神秘的西王母所居之所,并从侧面反映了西王母的神格属性,说是西王母仙境也不为过。
三、西王母仙境中的凭几
然而,在汉画像石所表现的西王母仙境中,除了上述各种具有神异色彩的随侍动物,还存在着具有人间性特征的家具——凭几。
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宋山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画像石,整个画面呈上下分布,上层第一格画像即为西王母仙境。西王母戴胜,凭几端坐于鱼麟纹曲形高台之上,左侧有一呈持杯跪坐状的鸡首羽人,右侧有一手持异形华盖的裸体羽人,还有六个手持仙草的羽人,曲形高台下有一呈捧盒状的蟾蜍和一呈捣药状的玉兔(图2)。
山东嘉祥县洪山村东汉时期画像石,整个画面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西王母仙境。西王母戴胜,凭几端坐于画面偏左处,两侧跪坐捧仙草的侍者,右侧为西王母部众,左起依次为持棍状物于头顶交叉的舞状蟾蜍、长羽翼且呈跪求状的鸡首人身者、捣药兔、带棍状物的三足乌和九尾狐。
山东孝堂山石祠西山墙东汉时期画像,整个画面按构图可分为三个部分,但都为西王母仙境。西王母凭几端坐于画面下层中间,两侧侍者对称分布。第二层似为贯匈国之人,顶部为持规的女娲形象和吹风的风伯形象,三足乌、白虎和捣药兔等神兽形象零星地分布其中。
此外,还有山东邹城市高庄乡金斗山祠堂画像石、山东微山县沟南石椁第4石、江苏徐州沛县栖山石椁东壁画像石、山东枣庄市山亭区冯卯乡画像石等。在这些画像石中,西王母均凭几而坐于仙境之中,但凭几作为一件具有人间世俗性质的家具,与仙境所代表的神圣氛围是有矛盾的。但这种现象不是个例,且分布于山东和江苏两地,可见并非工匠失误所致。
四、西王母仙境人間化的背后
凭几作为人间世俗生活中的家具,为何会出现在西王母仙境之中呢?笔者认为原因如下:
一是西王母形象的拟人化,从一个外貌肖兽的凶神逐渐蜕变为一个人形女神。
根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西王母的形象为豹尾、虎齿、蓬发。而根据学者袁珂的考证,《西山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说明在当时西王母仍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神形象,在外貌上与凶残可憎的野兽更为相似。
到了汉代之后,西王母形象有了较大转变,逐渐具有人的外貌。
西汉《大人赋》将西王母描述为一个白发苍苍的长寿者,这虽然是司马相如对西王母外貌的一种想象,但也代表了时人心中的西王母形象。河南偃师辛村壁画上的西王母图像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西王母为白发像,头上仅用一些墨线勾出头发的轮廓,然后以白色来填空,但同墓壁画中的男女形象皆填以黑发,这不禁使我们立即联想到前述的白发老者形象。《汉武帝内传》则将西王母描述为一个“三十许”且容颜绝世的大美女,较之《大人赋》中的白发老者已然年轻了许多。
可见在汉代,西王母的形象逐渐“拟人化”,并从白发老者蜕变为“三十许”的美女,外貌造型上已经趋近于普通人。此时的西王母形象更加符合时人的审美,较之《山海经》中的凶兽形象已相去甚远。
但拟人化并不意味着西王母神性的降低,民众越是信奉一个神灵,就越会将其美化。例如,传播狩猎放牧等方法的宓妃被曹植描述为“第一美人”,而会给人间带来灾祸的女魃等的形象就被丑化。所以,从一个神灵被美化的程度就可以推测出其被民众信仰的程度。
西王母神话作为华夏神话体系中典型的一部分,是民族文化和心理孕育下的产物,所以民众总是从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所处的客观世界出发去构思神灵及其所处的仙境。此时,西王母已经在某一程度上有了人的特征,比如白发。民众也自然而然地认为西王母和人一样也会累,所以将凭几刻画在西王母仙境中,供西王母凭靠。
二是西王母的地位具有崇高性,以凭几来供其依凭是相匹配的。
《荀子·大略》中提到的“禹学于西王国”,联系上下文語境来看,这里的“西王国”指的是一个人名,即我们所说的西王母。禹作为治水的圣人,还需要求学于西王母,西王母作为圣者师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了。
《淮南子·览冥训》中提及“西姥折胜,黄神啸吟”,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西王母”,但是其中所说的“西姥”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西王母。因为在古代,姥为尊,而称西王母为西姥,也正是说明了西王母在汉代的地位之高,极受尊崇。另外,黄神就是黄帝,和《庄子·大宗师第六》中一样将西王母与黄帝并列,可见汉代民众将西王母置于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的形象则与帝王之相十分接近,且地位极高,汉武帝在她面前都只能叩头跪拜、站立侍候。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会见西王母时,进献了“绵组”等贵重物品,说明此时西王母的地位等同于人间天子的地位,甚至西王母处于高位,这足以说明西王母的地位非同一般。
从这些典籍中看,西王母毋庸置疑拥有权威地位,那么我们再观察一下图像中的西王母,她的地位是否也同文字记载中的地位一致呢?
首先来看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石(图3),西王母处在山墙锐顶的中心位置,身边是捣药兔、羽人等,黄帝则刻绘在西王母的下层,这一层从右到左依次为:人身蛇躯的伏羲和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夏桀。从图像学的构造分析来看,西王母在这张图像中处于绝对中心位置,说明西王母在汉代人眼中已经凌驾于三皇五帝和伏羲、女娲之上。
还有山东微山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伏羲、女娲手执便面出现在画面两侧,西王母端坐在交缠的蛇尾之上,身形硕大,头顶栖息一只鸟,身边有榜题曰“田王母”。但据学者考证,“田”字为误写,应为“西王母”。从西王母占据整个图像的比例和榜题来看,西王母毋庸置疑是主角,伏羲、女娲只是西王母的侍从而已。
再看江苏滕州市官桥镇出土的一块画像石,西王母坐在画面左处的一座束腰高台之上,或为异形昆仑山;东王公则端坐在画面右侧的低处,处于画面中间的伏羲、女娲一前一后护送龙车。但从整体上看,伏羲、女娲的形象细长弯曲,与周围的装饰纹路极为相似,远不如西王母与东王公二神的形象鲜明高大,不具备独立意义,所以伏羲、女娲仍处于从属位置,地位不如西王母高。
综上,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出土图像两种材料来看,西王母在汉代开始拟人化,成为一位美丽的人间女神,但同时西王母又拥有显赫的地位。可以说,西王母在仙境之中的地位正如帝王在人间的地位,而凭几作为一种供尊者使用的家具,表现在西王母仙境中是恰到好处的。
五、小结
在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中,西王母信仰以其潜在而又深远的力量对民众的审美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这种审美观念又间接地反映在汉画像石艺术中。先民敬畏西王母,但同时又不断地尝试着和西王母近距离交流以求得庇佑,这一矛盾的心理也反映在汉画像石中,造成了西王母世界神圣性和世俗性的矛盾统一。
凭几作为俗世间中供尊者使用的家具,却在汉画像石中常常可以见到西王母凭几坐于仙境之中,这并不是汉画像石制作者的失误,而是有意为之的,是汉代人审美观念和信仰的间接表达,反映出西王母形象在汉代逐渐拟人化和她的崇高地位。
参考文献:
[1]陆锡兴.凭几源流 [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01):97-101.
[2]刘勤.西王母神格升降之再探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42-48.
[3]张影,邬晓东.西王母的神格发展与汉代西王母崇拜[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05):88-91+72.
[4]孙昕姣.汉画像石西王母仙境图中的蟾蜍图像探析[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17):83-85.
[5]樊睿信.汉代西王母形象演变——以汉画像石为中心[D].信阳师范学院,2022.
作者简介:
张奕(2000—),女,汉族,浙江金华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唐宋元明清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