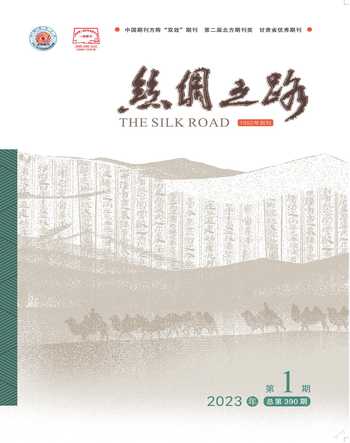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佛造像研究
张语晨 陈安道 郭海燕 张海宏 杨娟



[摘要]平凉市博物馆藏金铜造像中,明代金铜造像占比最大,题材丰富,造型风格多样。本文通过类型学、标准器物学方法,对馆藏明代金铜造像分类梳理,并结合明代纪年造像,分析其形制特征和时代风格,总结出平凉明代金铜佛造像风格上为汉式造像和藏式造像共存,其造型和工艺精美程度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降低,恰与明王朝逐渐没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互印证。
[关键词]平凉市博物馆;明代;金铜佛像;形制特征;纪年造像
[中图分类号] G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160-09
金铜佛造像作为佛像的重要门类,因其材质坚固贵重、利于保存,又小巧便携,方便膜拜供养,从而成为佛教徒开展信仰活动的重要载体。从汉魏、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一直延续到明清,各时代遗留了风格多样的金铜佛造像[1]。由于明代统治者推崇佛教,使得明代金铜佛造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空前高峰。平凉市博物馆藏金铜佛造像以明代造像最多,约占馆藏金铜佛造像的40%,这与当时入驻平凉的明韩王推崇佛事不无关系。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韩王朱松改封平凉,其嫡长子朱冲于洪熙元年(1425)七月到达封国平凉,平凉韩王时代由此开始,明韩王共传十一王,从就藩平凉到崇祯十六年(1643)末代韩王朱亶塉被执,韩王在平凉共历时218年,与明王朝共终[2]。韩王宗藩的入驻和发展对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有着绝对的影响力,韩恭王初到平凉,便奏请增造王府的同时在岷州营建广福寺[3],昭示了韩王家族佛教信仰的渊源,后历代韩王也多崇尚佛教,在平凉境内广兴佛寺,留下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本文将以平凉市博物馆藏的40尊明代金铜佛造像为研究标本,对其进行分类分型研究。
一、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佛造像题材类别
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造像其来源方式主要为征集和采集,其中大部分造像采集于平凉市佛道名山崆峒山。造像題材丰富,根据佛像坐姿、造型及结印手法,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佛造像
1.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在佛教里地位最高,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都尊其为佛祖,馆内藏释迦牟尼像共有9尊,根据佛像造型及结印手法,可分为成道像和说法像[4]。释迦牟尼成道像一般为结跏趺坐,左手手心向上置左足(膝)上,名禅定印,右手垂直指地,名触地印,将结此种手印姿势的佛称为释迦牟尼佛成道像,平凉市博物馆馆藏释迦牟尼成道像有4尊。释迦牟尼说法像手印为左手横置左膝上结禅定印,右手向上曲至肩或胸前,施说法印。平凉市博物馆馆藏释迦牟尼说法像2尊。
2.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三世佛中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坐像姿势为结跏趺坐,两手交叠,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结弥陀定印于腹前,掌心托宝瓶或莲台。平凉市博物馆藏阿弥陀佛坐像2尊。
3.药师佛
药师佛全称“药师琉璃光如来”,他能除生死之病,故名药师,能照三有之阇,故名琉璃光,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药师佛常见形象是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身披袈裟,左手执药器,右手结定印,或左手持药钵,右手拿药丸。平凉市博物馆藏药师佛5尊。
4.毗卢遮那佛
毗卢遮那佛是佛祖释迦牟尼显法所成的“法身佛”,一般双手举至胸前结智拳印或无上菩提印[5]。平凉市博物馆馆藏毗卢遮那佛3尊,其中1尊为铁质佛像。
5.弥勒佛
弥勒佛被释迦牟尼指定为佛的法定继承人,称为“未来佛”。弥勒佛造像庄严肃穆,凝神入定,常供奉于寺院中大雄宝殿,以三世佛形象出现,而千百年来,深入人心的则是大肚弥勒,因其善眉乐目,笑口大开而备受大众喜爱。平凉市博物馆馆藏弥勒佛4尊,均为大肚弥勒佛。
(二)菩萨像
1.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我国民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菩萨。观音菩萨种类形象丰富,造型复杂。平凉市博物馆藏观音菩萨既有三面三十六臂观音、十一面二十四臂观音、十面十臂观音等,也有手执莲花、杨枝的常见观音形象。
2.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释迦佛的左胁侍,造型多顶结五髻,表大日如来之五智,称为“五髻文殊”,手持宝剑和经卷,表以智慧利剑斩断烦恼,坐骑为狮子,比喻以狮吼威风震慑魔怨。平凉市博物馆馆藏文殊菩萨像4尊。
3.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是释迦佛的右胁侍,与释迦牟尼、文殊菩萨合称“华严三圣”。坐骑为六牙白象,手持如意,象征“愿行广大,功德圆满”。馆藏普贤菩萨2尊。
(三)金刚像
金刚是西藏密宗的护法神,经常手持金刚杵,象征能够摧伏外道、击败邪魔的力量。平凉市博物馆馆藏金刚像1件。
(四)韦陀像
韦陀是佛教的大菩萨之一,寺庙一般都会供奉,职责是护法安僧。平凉市博物馆馆藏韦陀像1件。
(五)罗汉像
在大乘佛教中罗汉是排在佛和菩萨后的第三等,历代较为流行的罗汉像有十大弟子、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平凉市博物馆藏罗汉像1尊,从佛像额头刻画的几条皱纹,表明为老者形象,推测可能为释迦佛大弟子迦叶。
二、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佛造像类型分析
明代金铜造像最大的特点是藏传造像和汉传造像融合发展。明初期,永乐皇帝为推行其宗教笼络政策,于永乐六年(1408)专门在内府下辖机构“御用监”设立“佛作”,铸造藏式佛像,赏赐给西藏上层僧侣[6],这些造像做工精细、风格统一,延续至宣德时期,因此,明代宫廷造像也专指明代永宣时期风格造像[7]。宣德之后,宫廷停止制造藏式佛像,袈裟和面容汉化明显的“汉式造像”开始兴起。为分析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佛造像风格特征,以下根据金铜佛造像的发髻、面相、衣饰、底座、比例等细节特征进行分型研究。
(一)佛造像可分为五型
A 型:有底座,底座为双层仰覆莲座,塔状高螺髻,顶严小,似一圆珠;着袒右肩或袒右胸袈裟,袈裟贴体,梵式面相,为明显的藏式造像特色。归为此类的造像有6尊:KTB669(图1), KTB670,KTB0671,PLB1208(图2), PLB0780, PLB1517(图3)。6尊造像发髻、袈裟和面相上风格一致,但在工艺上有所区别,KTB669和 KTB670的莲花台座下大上小,稳重大气,莲瓣分布紧凑精细,均有上下对称的九组莲瓣,莲瓣饱满,瓣尖翘起饰卷云纹,造像整体比例合理; PLB1208和PLB0780的莲瓣则变得大而宽平,莲瓣数量也减少为7组和5组;PLB1517莲瓣宽平,上下交错分布,莲座小而局促,造像头大身小,胳膊短,比例失调。
B 型:无底座,发髻相较 A 型变的低平,顶严大而圆滑;宽额丰颐,眼睑低垂、目光下敛,肩背宽厚,神态慈祥柔和,佛像皆着双领垂肩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腹部系带打结,衣缘錾刻精美纹饰,衣褶布排有序,衣纹流畅自如,厚重写实,极富质感,继承了汉地造像注重衣褶刻划的传统。其面相、衣饰都具有明代典型的汉式造像特征。归为此型的造像有6尊:KTB0634(图4), KTB0635,KTB0636,KTB0646(图5),KTB0631, KTB0689(图6)。
C 型:佛佩戴发冠,衣纹刻画厚重写实,整体比例精准,做工精细。可归为此型的造像有2尊:KTB0644(图 7)和 KTB0613(图 8)。 KTB0644大日如来像,佩五叶佛冠,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高腰裙系带,衣纹流畅,显示出匠人高超的写实技法。造型端庄、法相庄严、工艺精细、品相完美、体量硕大、气势恢宏。尤其莲花台座刻画精致,三层仰莲瓣座下一莲柱接于六角围栏座上,下再接一六足壶门底座。
D 型:整体做工粗糙,佛像瘦长,脸型瘦削,肩窄,溜肩,多边形须弥台座,上涂彩绘,佛像衣着及面容都有汉式造像特征。符合此型的有2尊:KTB0632(图 9)和 KTB0625(图 10)。KTB0632有“嘉靖十七年”的明确纪年,此像反映出嘉靖时平凉地区的佛像鑄造工艺已经开始变得粗糙。标本32KTB0625是一尊铁质佛像,佛像从面部以下,底座以上都有鎏金,鎏金灿黄色,螺髻和底座均涂饰彩绘颜色,其造像细节刻画比较粗糙,手极小,比例很不协调。背部铭文中提到“韩府”,应为明代韩王府后裔,铭文中未提及铸造日期。
E 型:弥勒佛。平凉市博物馆藏的4尊弥勒佛,皆为秃发、开口畅笑、大肚、袈裟坦胸露肚、左腿平放、左手抚膝持布袋、右腿曲支、箕踞而坐等相同特征,因此归为一型。符合此型的有 KTB0637(图11),KTB0638,KTB0639, KTB0621(图12)。造像 KTB0637着袒右肩袈裟,整体呈乌黑色,给人以古朴厚重之感。 KTB0638和KTB0639皆着双肩袈裟下垂袈裟,腹部系带。 KTB0621全身彩绘,袈裟整体红色,腹及手部皮肤均模拟肤色呈浅黄色,面部以白色腻子层打底,眉眼弯弯,五官彩绘,脸部似有腮红。
(二)菩萨像及其他造像
由于金刚、韦陀及罗汉像都仅有1尊,因此将其并入此类一起分析讨论。根据造像的发髻、面相、衣饰、底座、比例等细节特征,可分为四型。
A 型:面相方圆,高发冠,坦上身,披帛裹肩,佩戴璎珞,下身着裙,衣纹贴体,有莲花底座,具有明显的藏式造像特征。属于此型的有4尊:KTB0642(图13),KTB0643(图14), KTB0674,KTB0676。KTB0642十一面二十四臂观音铜坐像,KTB0643明四圆八臂金刚铜坐像和 KTB0674明“成化十年”十面十臂观音铜坐像,多面多臂,梵式面相,均属于典型的藏传佛教造像。
B 型:面相慈善悲悯,脸型长圆,外披袈裟,内着高腰裙,腰间系带,衣纹厚重写实,比例精准,造型大气精美,衣着和面相皆具有典型的汉式造像特征,归为此型的有2尊:KTB0645(图15)和KTB0619(图16)。
C 型:面容呆滞,趋于世俗化,刻画不精细,多着宽袖袈裟,具有汉式造像风格,头大身小,比例失调,造型拙朴。归为此型的有9尊:KTB0672(图17),KTB0673,KTB0640,KTB0675, KTB0677(图18),KTB0680(图19),KTB0681, KTB0902,KTB0657。此类菩萨造像较多,其造型和工艺均不够精细,神态呆滞,汉化特征明显。
D 型:造像全身使用彩绘装饰,皮肤使用肤色彩绘,仿出肤感,眉毛、眼睛用黑色描画,嘴唇用朱彩描画。归为此型的有4尊:KTB0627(图20), KTB0628((图21), KTB0630,KTB0622。 KTB0622的韦陀像,有“崇祯三年”的明确纪年,其面形、铠甲与首都博物馆藏崇祯辛巳年御用监造韦陀立像相似。而 KTB0627文殊菩萨, KTB0628普贤菩萨和KTB0630观音菩萨,在造型特征上除了表现菩萨身份的坐骑、莲花底座、手势不同用以区分菩萨身份之外,其他特征几乎一样,这3尊造像当时应为同时铸造,一起供奉的一组造像,银川出土的一组3尊菩萨造像与此供奉形式相似,这种供奉形式又称为观音三大士[8]。
三、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佛造像分期研究
(一)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纪年金铜佛造像
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纪年造像共5尊。
KTB0645,明景泰三年(1457)文殊菩萨铜坐像。此像头戴发冠,面相慈善悲悯,脸型长圆,外披双肩袈裟,内着高腰裙,腰间系带,衣纹厚重写实,衣着和面相皆具有典型的汉式造像特征。束腰仰覆莲座,莲瓣饱满匀称,上下联珠纹饱满清晰。莲瓣饰红彩,瓣间隙饰蓝彩。像座后及座面边缘錾刻“僧道之……景泰三年九月初一造……”等字(图15)。
KTB0674,明成化十年(1474)十面十臂观音铜坐像。像作坐姿,观音菩萨十面十臂,正面左右侧各一面,头戴高冠,冠分两层,上一面,下二面,下左右两侧各一面,冠后上下各一面,面神情各异,正面脸相丰圆,宽额白毫,棱眉垂鼻,双目丰启,硕耳坠珠,飘帛自首后缠肩绕臂,颈戴项圈,胸饰璎珞,正面两手叠握瓶于腹部,肩两侧各附四臂,或托日月,或持法轮,金刚杵,药丸等法器,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之上,座后两侧阴刻楷书“成化十年……”题记38字(图22)。
KTB0632,明嘉靖十七年(1538)药师佛铜坐像。药师佛螺髻,双耳硕垂,面相方圆,大眼长鼻,双目微睁,额间白毫,身着袈裟,胸部袒露,裙带于腹部打结,左右宽袖搭于臀部两侧,右手垂按右腿,左手握药丸,结跏趺坐于单层仰莲座上,座下须弥座,背部铸有“嘉靖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张重成”等楷书34字(图9)。
KTB0638,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弥勒佛造像。弥勒佛硕首方颅,张口大笑,着宽袖袈裟,袒胸露腹,右手握佛珠置膝上,左手放腿上握一布袋,右腿曲支,箕踞而坐,无底座。于身后铸“大明万历二十六年,孟冬吉日……陇州金火匠李登处造”等楷书阳文73字,铭文将纪年和铸造工匠都记载的很明确。其铸造地陇州即现在的陇县,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位于宝鸡市西北,与平凉市华亭县、崇信县、灵台县毗邻(图23)。
KTB0622,明崇祯三年(1630)韦陀铜坐像。韦陀头戴盔胄帽,脸庞丰圆,大眼高鼻,神情严肃,身着乳钉状短袖铠甲战服,披帛绕肩缠臂,右臂曲侧,手握钵,左臂曲于胸前,开腿坐于月牙形四足椅座之上,彩绘盔,涂蓝,甲染黄,袍施朱,座右侧刻“崇祯三年四月十八日造……”等残余120余字(图24)。
以上5件纪年佛像,年代从景泰三年到崇祯三年(1457-1630),时间跨度较大,可以很好地反映平凉地区明代各时期造像特征。如景泰三年(1457)菩萨像,比例精准,刻画细腻,整体大气精美,是明代汉传造像中的精品,通过此像可以反映出景泰年间,平凉地区注重佛像量度、仪轨,且铸造工艺精湛。成化十年(1474)十面十臂观音铜坐像为藏式造像,细节比例刻画合理,但其整体造型及工艺精细程度已大不如景泰年菩萨像。嘉靖十七年(1538)的药师佛,面相身形瘦长,世俗化明显,此时期的佛像风格相比前期变化较大,也可能与嘉靖帝尊崇道教有关。至崇祯年韦陀像,已完全丧失佛造像的庄严质感。以上5尊纪年佛像,随着年代递增,造型精细程度和工艺水平不断降低,这一现象恰与明朝逐步衰败的政治经济形势相互印证。
(二)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佛造像标准器分期研究
冀瑞在关于山西博物院藏明代佛像的研究中,梳理了明代纪年金铜造像后,根据其风格特征,将明代金铜造像年代分为四期:洪武时期,明洪武至建文(1368-1402);永宣时期,明永乐至宣德(1402-1435);明中期,明正统至弘治(1435-1505);明晚期,明正德至崇祯(1505-1644)[9]。但此分期中的明晚期跨度140年,造像的风格变化较大。本文根据明代历史、政治、经济的发展,参照平凉部分纪年文物形制特征分析,试将平凉明代造像时代分为五期。
1.明初期(1368-1402)
这一期的藏传佛教造像主要是束腰的躯体、西天梵相的面相、高耸的肉髻、薄衣贴体简洁的衣纹,承袭元代佛教造像的风格。汉传佛教造像仍承袭金元佛造像宽肩阔胸的风格特点,还残留着唐代佛造像的遗风,气宇轩昂,雄浑大气[10][11]。
2.永宣时期(1402-1435)
这一时期以藏传宫廷造像为主,特征鲜明统一,以面容有“西天梵相”特点,佛像衣纹简洁,菩萨装饰繁缛华美,束腰仰覆莲座莲瓣饱满精美,立体感强[12]。
3.明中期(1435-1505)
此时明朝依然处于中兴时期,政治严明、经济繁荣、社会有序。由于永宣之后,明朝停止制造宫廷藏传造像[13],因此衣着、面容汉化明显的汉式造像开始兴起,与传承永宣遗风的藏式造像同步发展,且在永宣宫廷造像比例严谨、造型精致的影响之下,此时期的汉式造像依然注重量度仪轨,细腻精美,颇具宫廷造像华美大气之风。
4.明晚期(1505-1620)
此时期历时最久,尤其嘉靖和万历帝统治时期较长,政治弊端出现,此期也是明朝政治经济走向没落的开始。由于此期时间跨度长,因此造像风格多样,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造像依然注重比例、衣着、面容等刻画,但是细节上已大不如前,部分造像神情呆滞,造型敷衍,工艺粗糙。
5.明末期(1620-1644)
此时的明王朝在经过200余年的统治之后,沉苛积聚,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已然走向衰败末年,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下,工匠技艺、审美制作标准必然也已衰退。此时期的造像,头身、手腿比例严重失调,面容刻画模糊,工艺粗制滥造,佛像造型已经失去艺术美感,可能更多是作为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寄托,且通过明代末期纪年造像,也可发现,此时的造像使用彩绘装饰全身,面容五官也是彩绘描画而出。
(三)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佛造像年代分期研究
平凉市博物馆藏的明代金铜佛造像,从形制特征和工艺来看,绝大部分造像都属永宣之后的民间造像,在造型、工艺及精美度上与明代永宣宫廷造像均有很大差距。
佛 A 型:此型6尊造像,据其工艺特征,推测为明晚期造像,莲座精细度可能随着年代推移而逐渐下降,尤其 PLB1517,比例严重失调,莲座局促,可能为明末期造像。
佛 B 型:5尊造像除KTB0689外,袈裟衣边都饰有花纹,头部略大,但整体身形流畅,手指修长灵动,刻画精细,做工精致,符合明晚期中雍时期汉地造像风格。KTB0689造像螺髻上乳钉颗粒粗大,皮肤上髹有红漆,头大身小,胳膊短,手小,整体比例极不协调,身形刻画呆板,不够流畅与同型其他几尊造像相比,做工明显较为粗糙,可能为明末期造像。
佛 C 型:大日如来像整体注重佛像的量度和仪轨,延续了永宣之风,但着汉式褒衣博带袈裟和高腰系带裙,其造型之周正、用料之殷、体格之大、鎏金之完美,均可表明造像来自皇室宗亲或雄浑大庙,因此推测其为明中期造像。 KTB0613药师佛身形比例合理,衣纹流畅,但莲瓣外形宽平,分布稀疏,仅在座前分布5组,座后光素。这种莲瓣与安徽博物馆正德十年(1515)佛坐像和安徽博物館隆庆十年(1576)佛坐像[14]的莲瓣特征相似。因此,推测其为明晚期造像。
佛 D 型:KTB0632有“明嘉靖十七年”(1538)纪年,为明后期造像。KTB0625从其为佛像通身鎏金以及铭文中“韩府”铸造,可看出供奉铸像者并不缺钱,但其造型粗糙,比例失调,不重细节,说明此时佛像铸造工艺已经衰落,应是明代末期所铸佛像。
佛 E 型:KTB0638弥勒佛有“万历二十六年”(1598)精确纪年,从4尊造像的形制特征和做工来看,KTB0637造型古朴,可能年代早于 KTB0638;KTB0639外观特征与 KTB0638类似,应该年代接近,属明晚期;而全身彩绘的 KTB0621则更符合明末期造像特征。
菩萨 A 型:KTB0642和KTB0643造型古朴厚重,比例严谨,细节繁缛,可能为明早中期精品造像;KTB0676虽衣着造型也有藏式佛像特点,但精细度相较降低,可能为明晚期造像。
菩萨 B型:KTB0645明景泰三年(1452)文殊菩萨铜坐像,精美大气有确切纪年,KTB0619明彩绘三面三十六臂观音铜造像在造型周正,工艺精美度上可比拟景泰三年(1452)文殊像,但是没有莲花台座,因此推测其年代可能为明晚期,接近明中期。
菩萨 C 型:其中 KTB0672、KTB0673、KTB0640在整体细节刻画和比例上较其他造像略微精细些,推测此4尊造像年代可能为明晚期。而其余5尊造像,比例失调,面容呆滞,更有可能是明末期造像。
菩萨 D 型:据其造型和彩绘面容的工艺特征,推测此型3尊菩萨造像的年代应该与同型的崇祯三年(1630)韦陀像同属于明末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造像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题材类型多样,以手印、法器、坐骑等特征区分塑造不同的佛陀和菩萨,体现了明代时期,佛陀菩萨种类划分细致,各司其职,寄托了信众不同的精神需求;二是汉藏风格融合发展,高螺髻、着袒右肩或袒右胸袈裟,衣纹贴体、梵式面相的“藏式佛像”和发髻平圆,着双领下垂式袈裟,面相世俗化的“汉式造像”同时存在,且“汉式造像”佛和菩萨在数量比例上相对较多;三是工艺水平参差不齐,仅有大日如来、十一面观音等少数几尊造像造型和工艺十分精湛,大多数佛造像工艺水平比较平庸,属于永宣之后的明中晚期和明末年造像,根据纪年造像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年代递增,造像的造型审美和工艺水平不断降低,可能与明代中晚期不断衰败的政治经济相关。平凉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铜造像类型丰富,数量众多,是明代平凉地区佛教兴盛的历史见证,也反映了明韩王入驻平凉后,大力推崇佛事活动,对民间宗教信仰产生了极大影响。
参考文献
[1]李静杰.金铜佛的文献考察[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01):51.
[2]吴通.明代韩王与陇东地區宗教的发展[D].兰州:兰州大学,2015:16.
[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18《韩王朱松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74:3605.
[4]吕凤涛.中国佛像收藏与鉴赏全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231-232.
[5]赖天兵.两种毗卢遮那佛造型:智拳印与最上菩提印毗卢佛造像探讨[J].中国藏学,2009,(03):177-186.
[6](明)刘若愚,吕瑟.明宫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7]黄春和.明代永乐宣德宫廷藏式金铜佛像(上)[J].收藏家,2003,(04):20-25.
[8]金申.金申观点:银川出土的铜佛像或为明初作品[J].东方收藏,2010,(04):42-44.
[9]冀瑞.山西博物院馆藏明代金铜佛教造像初步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9.
[10]金申.妙像梵音(一)5048尊洪武年鎏金佛像[J].收藏,2012,(11):132-135.
[11]陈露萌.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故宫藏明早期的汉传佛教金铜造像[J].东方收藏,2017,(02):18-23.
[12]黄春和.明代永乐宣德宫廷藏式金铜佛像(下)[J].收藏家,2003,(05):22-29.
[13]黄春和.元明清北京宫廷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及特征[J].法音,2001(06):31-36.
[14]金申,贾文忠.中国佛像真伪识别[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198-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