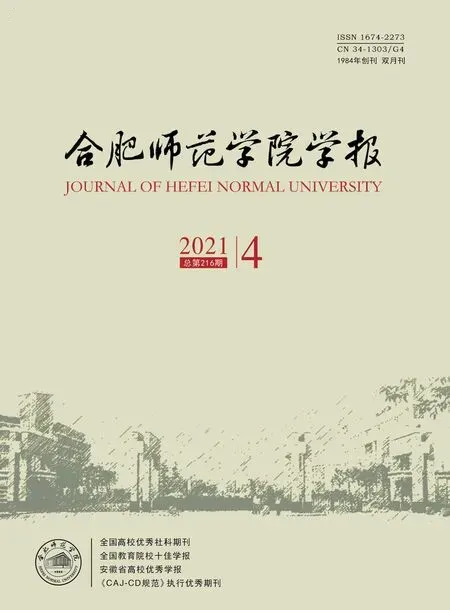精神分裂者的幻象与自语
——论余华《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的时间迷宫
陈佳冀,王 琳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在康德看来,“时间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也不是附属于物的客观规定,因而不是抽掉物的直观的一切主观条件仍然还会留存下来的东西”[1]。一旦抽离了主观条件,时间将不再留存,时间是主观条件和客观存在的统一。传统小说家们很少关注时间和生命主体存在的关系,也并不热衷于去追问人和时间的本质这一哲学命题,时间始终作为故事背景而存在、并保有线性自然的固有流动秩序,即便是倒叙和插叙手法的运用,时间内蕴其中也只是适时变幻了“出场”顺序而已。而余华早年发表在《钟山》1989年第4期的中篇《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则不然,这是一篇极具先锋性质、特立独行的小说文本,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结构最为复杂的作品。它彻底打破了传统叙事经验中对于线性时间、客观真实等的刻意强调,建立起对于网状时间、内心真实书写的极端推崇。余华所做出的创作努力,在今天看来无疑称得上是一场颠覆与突围,是对被经验、理性和逻辑围困的传统小说的反叛,余华将时间而非情节作为叙事架构的中心,巧妙地搭建起极具前卫、创新实践性质的叙述迷宫,迷宫中的时间错乱交叠、空间似真似幻、人物身份成谜、对话主体和时间的关系空前密切。在对迷宫出口的求索中,可以窥探到余华对人存在的本质条件、时间和人的存在关系等所做出的某些回应、解答与探究。
一、错综迷宫中的时间线索
“在作家们意识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心灵的世界不是一个时间维度时,便可以用自己强大的想象力,把故事结构中时间的线性逻辑关系打乱,让世界在作家笔下有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姿态。”[2]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是一篇错综复杂的小说,复杂性倒不在于情节,而在于时间错乱和重复叙述,这赋予了文本本身“更为丰富多彩的姿态”。这部小说共分为四大段落,余华所设置的每段标题是1234、1234、123、12,但发表时被改成1至13的形式。错乱无序、相互矛盾的时间构成了本文的迷宫和障碍,但也是重要指引和线索。要从错乱重复的人物叙述中寻求解释文本意义的出路,首先需按照时间线性顺序理顺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脉络,以求理清重要时间节点和人物关系。
第一大段: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3]89得出外乡人的所处时间是1998年5月8日。
“我感到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还没有来到。”[3]89得出“我”所处时间应当在1988年5月8日之前。
1988年5月8日,“意外”使得外乡人的视力开始衰退。
1988年8月14日,少女发生车祸,死亡后将眼球给了外乡人。
1988年9月3日,外乡人坐在驶往小城烟的汽车上遇到了老人沈良,听沈良讲炸弹的故事。沈良告诉外乡人小城烟埋有10颗炸弹。
此段中“我”所处时间是1988年5月8日前,据后文第二大段“我”的讲述,得出此时“我”的内心尚未出现少女,此段没有交代外乡人发生的意外是什么,但根据后文描述可推断出意外是外乡人内心出现了少女。此段留了两处空白,但可以通过后文的重复叙述推理出空白。
第二大段:
1988年5月8日,“我”的内心出现了少女。
几天后,“我”遇见了“他”,听“他”讲少女和炸弹的故事。“他”告诉“我”实际上已有9颗炸弹爆炸。
“十年前,他告诉我: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3]105得出“他”所处的时间是1998年5月8日。
1988年5月8日,“他”的内心出现了少女。
1988年8月14日,少女发生车祸,死亡后将眼球给了“他”。
1988年9月3日,“他”坐在驶往小城烟的汽车上遇到了老人沈良,听沈良讲炸弹的故事。沈良告诉“他”已有8颗炸弹爆炸。
第二段填补了上一段的空白之一:“我”在随后到来的1988年5月8日这天心中出现了少女。至此已令人产生怀疑:“他”的经历和外乡人的经历很相似,“他”和外乡人是否为同一人?根据二人几乎重合的经历可以得出:第一段中使外乡人视力衰退的意外是1988年5月8日外乡人心中出现了少女。
第三大段:
1988年5月8日开始,“我”的视力逐渐衰退。
1988年5月8日—8月14日之间的某天,“我”发生了车祸。
1988年8月14日,少女患白血病而死,将眼球给了“我”。
1988年9月3日,“我”在驶往小城烟的汽车上遇见了老人沈良和外乡人,沈良对外乡人讲述炸弹的故事。
此段进一步加深了怀疑:不仅“他”和外乡人的经历高度重合,就连“我”的经历也和“他”以及“外乡人”几乎一致,“我”、外乡人和“他”很可能是同一人。
此处还有一句意义模糊不清的话:“我发现自己和杨柳躺在同样的位置里,只是中间隔了一层。我问护士:‘三层靠窗的病床是谁?’她说:‘不太清楚。’”[3]117这又是一个叙事空白,余华设置了一个小陷阱。根据后文外乡人和“我”并排坐在汽车上,说明第三大段外乡人和“我”同时存在,且前文外乡人讲述接受了少女的眼球,推理“我”和少女隔着的人是外乡人,“我”和外乡人都于1988年8月14日接受了少女的眼球。余华在第三大段还安排了一个伏笔:“外乡人向一个站在路旁像是等人的年轻女子打听什么,于是我就一个人往前走去。”[3]120此处和第一大段中“他(外乡人)向一个站在路边像是等人的年轻女子打听了旅店”[3]92-93照应,暗示第三段出现的外乡人就是第一段里的外乡人,即“我”不仅和1998年5月8日的外乡人相遇,“我”还和1988年9月3日的外乡人相遇了。
第四大段:
多年后,“我”拜访了少女的父亲,少女父亲告诉“我”少女从没患白血病、也没发生车祸,她是在1988年8月14日自然睡眠而死。
后来“我”遇见了“他”,听他讲炸弹的故事。得知还剩1颗炸弹没有爆炸,且会在10个地点爆炸。
第四大段少女父亲的讲述和前三大段的讲述完全矛盾,然而并不能说明少女父亲的讲述推翻了前文结论,因为最后一遍被讲述的不一定比之前的讲述更加真实。“受阅读惯性的支配,我和许多人一样,常常会有这样一个幻觉:一个被重复讲述的故事,在它最后一遍被讲述的时候,更接近真实。”[4]这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无法判断出少女父亲、“我”、外乡人与“他”之中谁的讲述是真。高度一致的前三段叙述和矛盾丛生的第四段叙述为文本搭构出叙事迷宫。
此篇小说四大段的事件基本是重复叙事,时间无序错乱,“我”在1988年5月8日之前遇见了1998年5月8日的外乡人(第一大段)、“我”在1988年9月3日遇见了1988年9月3日的外乡人(第三大段),正如柏格森提出“有生命的地方,也就是有时间被记录的地方”[5],时间的意义依靠生命主体显现,柏格森将“存在、绵延和时间等同起来”[6],时间的绵延与生命存在密不可分,余华亦将人物间的关系与时间直接画上等号,时间和生命主体是彼此依存、难以剥离的一体,时间时而错乱、时而重叠,不同时间节点的人物相逢,并且人物间的经历高度相似,文本充满了变幻、怪异、流动的美感。如果抛开时间,“我”和外乡人的存在便无法被放置到合理的维度,二者间的关系更不复存在,文本迷宫将轰然倒塌、文本意义将走向空无。
二、走出迷宫与距离出口的“一步之遥”
理顺时间节点和人物的关系后,发现人物的行动、经历的事件高度一致,文本的情节由重复叙述的基本事件构成,接下来根据这些基本事件对小说的“母题”(源于传统的、反复出现的最基本的情节因素)进行划分,以寻求逃脱迷宫的钥匙。文中的“母题”故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而非文本叙述顺序来划分的话可分为四个事件:(1)1988年5月8日,“我”发现内心出现了少女。(2)“我”和少女杨柳就医于同一家医院,少女车祸死亡后将眼球给了“我”。(3)“我”在前往小城烟的途中遇到老人沈良,沈良告诉“我”炸弹的故事。(4)“我”听外乡人或“他”讲述少女和炸弹的故事。
第一大段,余华叙述了(2)(3)(4)三个事件;第二大段,叙述了(1)(2)(3)(4)完整的4个事件;第三大段,余华叙述了(1)(2)(3)三个事件;第四大段,余华叙述了(4)和(3)两个事件。通过对母题的拼剪和排列组合,余华重复叙述了四遍如上的母题故事。故事的发生虽然以(1)开始,最后以(4)结束,但是在母题中,如果抛开时间,会发现无法判定哪个部分是故事的开始,假如改变成(4)(1)(2)(3)的顺序情节依然连续。即文章首尾接连相续,形成了一个叙事循环。循环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我”、外乡人和“他”看似是三个主体,但在叙述中三者形象逐渐具有了同一性,即“我”“他”、外乡人似乎是同一人。
“我看到他的双腿抬起来时,与我的腿一模一样。……我看着他就如同看着自己在行走。”[3]103文本中的话语叙述暗示“他”就是“我”,“他”的居所、钥匙、走路姿势、隐蔽手段、关门方式和“我”完全一样,“他”和“我”一样都居住在临河的平房,“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完全一样,由此得出“他”就是“我”;“十年前,他告诉我:‘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3]105此句重复出现,外乡人也曾讲过完全一样的话,后文“他”的经历和外乡人的经历高度重合,暗示“他”就是外乡人。由此得出结论:外乡人、“他”“我”,其实是同一个人,是不同时间段的“我”相遇了。“我”是1988年的我,外乡人和“他”是1998年的“我”,都是十年后的“我”,外乡人的时间流动和“他”的时间流动是一致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外乡人和“他”不会同时出现。但无法解释“外乡人”和“他”的关系,即同一时间(1998年5月8日)为什么会有两个“同一人”。
是否可以就此认为“外乡人”就是“他”,只是两个称呼不同但内核相同的人。余华故意给同一个主体赋予了“外乡人”和“他”两个符号代码,其实主体形象是同一人。但笔者更倾向于存在“外乡人”和“他”两个主体,这两个主体虽没有同时存在或者对话过,但都在同一时空——1998年5月8日的小城烟。文本可以被理解为叙述者“我”遇到了十年后的两个自己,也可以被理解为两个自己遇见了十年前的“我”,即文本存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呈现三种时间交叠的状态。
余华此篇小说特点是以时间为结构和中心,把时间作为小说重要因素。时间交叠、时间并存,时间是网状而不是线状:“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7]在第一大段,“我”和外乡人同时存在,“我”听外乡人讲述少女和炸弹的故事;第二大段,“我”和“他”同时存在,“我”听“他”讲少女的故事;第三大段,“我”和外乡人同时存在,“我”和外乡人并排坐在驶往小城烟的汽车上,“我”和外乡人没有交谈,沈良向外乡人讲述炸弹的故事;第四大段“我”和“他”同时存在,“我”听“他”讲炸弹的故事。故事中始终存在的是讲述者“我”,而外乡人和“他”交替出现。和博尔赫斯不同的是,余华似乎把“你我”(对话的双方)都写成一个人。交谈的两个人似乎是同一个人,但后文又推翻了此结论。余华就像是狡猾的猎手,构建了迷宫也设置了走出迷宫的线索,但当猎物顺着线索即将走出迷宫时,迎面而来的是此路不通。迷宫的出口就在一步之遥,但难以走近。
三、通往迷宫的“钥匙”——虚构中的虚构
文本存在两个无法解释的悖论,这就是余华在迷宫出口设置的最大障碍,要寻求出口,必须解释横亘于前的悖论。
悖论1:根据少女父亲的回忆,少女也曾在想象中见到一个陌生男子,少女在铅笔画里把男子画了下来,“可我看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3]125。即少女想象中的男子不是“我”。第四大段“我”听“他”讲炸弹的故事,“他使我想起杨柳卧室里的铅笔画,画像上的人现在就坐在我对面”[3]127。即少女想象中的人是“他”。由此:“我”不是“他”。悖论出现:根据文本中的重复叙述和话语暗示得出过结论:外乡人、“我”“他”是同一个人,是不同时间段的“我”相遇了。但在结尾,余华推翻了读者的结论。于是文本变得不可把握、不可解释。
悖论2:前两大段交代了少女出车祸而死,第三段却说少女患白血病、出车祸的是“我”,第四大段又再次推翻前三段的说法,通过少女父亲之口交代少女既没出过车祸、也没患过白血病。有了少女父亲的回忆,前三段“我”、外乡人、“他”的讲述都很像精神分裂者的自言自语。
在文本阅读过后很难不产生这样一种质疑:外乡人和“他”讲述的经历会是真实的吗?余华的重复叙述是依靠外乡人、“他”“我”的讲述完成的,然而这种讲述是否值得被信赖?一切结论的基础是三个主体所讲述的自身经历是真实的。这是余华试图让读者相信的。然而如此充斥虚幻感的经历会是真实经历吗?以理性、逻辑和现实经验无法做出解释,只有从精神分裂、心理真实的角度才能解释悖论。小说是真实和虚构的统一,小说事件都是虚构的,但小说无不反映了真实、反映了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小说遵循“虚构中的真实”这一框架建构起来。但《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这一文本世界中只有“我”是真实存在的,“我”是虚构中的真实,而外乡人和“他”两个主体是“我”幻想出的人格、是“我”的副人格,这两个主体是虚构中的虚构,文本映射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人的精神世界;映射的不是真实,而是彻底的虚构。“我”与外乡人、与“他”的交谈其实是“我”在自言自语。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外乡人、“他”三个主体的经历是高度一致的。时间的交叠状态是小说发生在“我”的思维世界的最好证明。思维的跳跃性、混乱性恰恰可以解释时间的非线性。思维意识中,1998年5月8日才能与1988年9月3日同时存在;“外乡人”和“他”才能在同一时空——1998年5月8日的小城烟的临河的平房——居住着。
根据“我”的讲述:“我”居住在小城烟的临河的平房。小城烟不是中国任何城市的名称,长方形的平房结构在中国也遍地都是,无法根据讲述判断“我”居住的地点,即“我”存在的空间不是真实的现实意义的空间,讲述从一开始就是“我”的意识世界、是虚构中的虚构。景物描写亦给人似真似幻之感,“当微风掀动某一窗帘时,上面的图案花纹便会出现妖气十足的流动。这让我想起寓所下那条波光粼粼的河流”[3]85。现实世界的窗帘花纹是不可能流动的,意识世界中流动才成为可能。而“我”由花纹的流动联想到河流,这正暗含“我”意识的流动与转移。历史事件的引入如1949年国民党撤居台湾、国民党士兵埋下炸弹,使故事的空间看起来接近真实,但后文的讲述“这颗炸弹此刻埋在十个地方”[3]126将真实彻底瓦解,同一时刻同一颗炸弹将在十个地点爆炸,有力地证明了故事的开始就是混乱无序、非理性的意识世界。
对时间的解构也同样证明了故事的发生存在于意识世界。“他继续说:‘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我感到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还没有来到。于是我善意地纠正道:‘是一九七八年。’‘不。’外乡人摆了摆,说,‘是一九八八年。’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话,那是二十年前了。’”[3]89余华通过外乡人的讲述刻意以矛盾的、不存在的时间营造对现实的疏离,文本时间无法被合理放置到现实的线性时间的任何节点上,对话的双方所讲述的时间完全冲突,无法认清故事发生时间是哪一年。这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的,再次证明是非真实、非理性与非逻辑的意识世界。少女杨柳和少女父亲也是“我”的幻想,是虚构中的虚构。“我”在想象中甚至把少女当成了妻子,这是“我”性欲无法得到满足后在思维意识中的投射。少女捐献给“我”眼球,是“我”和少女产生交集、“我”能看见少女目光的原初动因,“我”在想象中和少女一起生活则是“我”爱慕少女的欲望被满足的直接体现。意识世界中,(1)“我”先是想象中看见了漂亮的少女并和她一起生活(结果),(2)然后视力衰退被送往医院、同时因车祸(或白血病)而死的少女将眼球给了“我”(原因),(3)最后“我”将少女当成了亡妻(结果)。结果发生在前、原因发生在后,逻辑顺序被颠倒,这显然也能证明故事的发生存在于意识世界且远离真实的现实世界。
从文本中不难窥见,“我”是个离群索居、内向寡言的人:“我拒绝一切危险的往来。”[3]84冷漠疏离的外表是一种自我保护和掩饰,“我”内心深处最幽茫难知的愿望仍是渴望和性格相投的人成为朋友:“我看到他的脸就在前面一尺处微笑,那种微笑是我在小城烟里遇到的所有微笑里,唯一安全的微笑。”[3]87渴望友情的愿望投射到思维意识中便有了外乡人和“他”,这两个经历雷同、性格相合的“朋友”。既然是朋友,首要条件是“他人”而不能是“自我”。所以在“我”发现两个朋友很可能和“我”是同一人以后,第三大段中“我”便出了车祸而少女则患白血病,这一经历区别于外乡人和“他”的经历,这看似矛盾之处是为了赋予“我”的朋友以差异。而借少女父亲之口得知少女想象中的男子是“他”而不是“我”,推翻了“我”和“他”的同一性、赋予“他”以“他者”的性质,到此,“我”渴望友情的愿望才真正得到实现。少女父亲否定的回答是为了顺应“我”的愿望、解除“我”的戒心。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外乡人、“他”、少女和少女父亲,都是“我”意识的产物,不具有真实存在性。
至此,两大悖论得到解释:经历的高度重合和前后文的伏笔照应能证明外乡人、“他”“我”确是同一人,看似匪夷所思但其实是同一人分裂出的两个人格主体,并且主人格与副人格经历了对话,在发现三个主体趋于同一人时,文本产生了两个悖论,这两个悖论推翻了“我”和外乡人和“他”是同一人的结论,对此的解释是寡言离群的“我”的潜意识中仍希望拥有朋友,而朋友要有“他者”的性质,即朋友不能是“我”本人,所以少女父亲否定的回答既解构了真实,又赋予外乡人和“他”以“他者”的性质,从而满足了“我”的愿望,这也证明人物或事件存在的意义都服从于“我”的意识和愿望。文本的两大悖论也只有放到“我”的幻想世界、虚构中的虚构这一背景中才成立。余华的高明之处也在于此。模糊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创造虚构中的虚构这一框架,放弃传统小说中虚构中的真实这一思路。传统小说在虚构中的真实这条路上走了太远,小说中的椅子依然不能在夜间飞起来、瓶盖依然不能自动跳起来、死去的人不能再以活人的身份出现、1992年过去紧接着是1993年。当人的视线离开物体后,物体还会维持原有的形状吗?1992年过后可以是1988年吗?我们是否太过于相信世界、太过于相信自身的经验?文学在“虚构中的真实”这个框架下运行了太久,拒绝接受新的违背经验的事物,作家局限在写实的屋子里,数十年如一日地描写车辆众多的街道、帆船众多的河流,却拒绝接受漂浮着帆船的街道和行驶着车辆的河流。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时间的顺序在一片宁静里随意变化。”[8]所以,余华想通过时间的错乱展示线性时间里无法展示的新的超出经验的东西,关于人的精神世界,关于人存在的本质条件,关于人存在的时空。“我居住的地方名叫烟,我的寓所是一间临河的平房,平房的结构是缺乏想象力的长方形。”[3]84其实从最开始似真似幻的空间中,余华就借“我”的叙述进入“我”的意识世界、进入虚构中的虚构了,倘若还用虚构中的真实解读余华,无疑会走向无法解释的悖论和对余华的误读。
海德格尔曾指出:“不是所有现实的、曾现实的或将是现实的人类,都实存着、曾实存过或将要实存。”[9]时间和空间是客观存在物,人之所以为人,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即时间和空间是人的本质的构成条件之一。余华曾指出对时间的迷恋:“在我开始以时间作为结构,来写作《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时,我感受到闯入一个全新世界的极大快乐。”[10]回顾余华创作生涯,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第七天》,《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是真正以时间为结构、为中心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虽也打破线性时间结构、首尾构成封闭圆环,但余华所改变的只是叙述顺序、时间仍是线性流动,没有改变以人物和情节为中心的叙事结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真正意义上消除了以人物和情节表达意义的传统叙事方式,通过迷宫般的时间探讨的是人的时间性问题,即时间中的人或者人存在的时间。即使是网状时间、会发生不同时间节点的主体在某一时刻相遇的情况,但依然是一个时间节点对应一个个体,人是时间中的人,无法抛开时间而承认人的存在性。当主体无法被安置到任何时间节点上,或者同一时间点上对应了两个主体,那这个主体真实存在性便值得怀疑。在同一时空——1998年5月8日的小城烟的临河的平房——存在着的两个主体就像是一阵风,或者一场梦,风过无痕,梦醒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