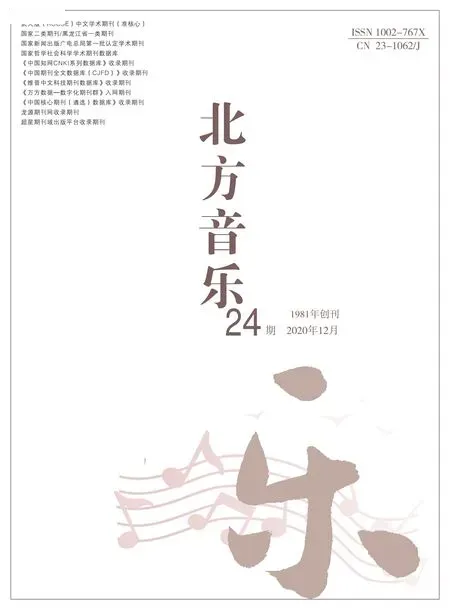苗族音乐在贵州高校中的教学改革探索
戚化怡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苗族音乐文化作为地方性文化,在苗族聚居区的学校教育中广泛地开展起来,且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在外来文化的挤压下,从民间的文化自觉到政府的统筹,无一不体现着贵州政府、学校正致力于保护与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虽然如此,并不代表苗族音乐这种弱势文化在当今物质、制度、精神全球化的传播氛围中具有实际的平等性。尤其在这种几乎完全西方化的校园音乐教学框架下,强势文化的冲击使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被挤压,在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大学阶段的少数民族音乐专业教育对贵州苗族音乐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对贵州省高校的民族音乐教育做了相关的调查研究。
一、贵州省高校教育中的现状及问题
(一)欧洲音乐中心主义影响下,教育模式的“同一性”怪圈
现代教育模式的“同一性”包含教学策略的“同一性”与课程设置的“同一性”两点。在对各大高校进行走访时发现,贵州苗族音乐的学校教育无一不是在欧洲音乐理论基本框架下进行的,在专业课程中使用的伴奏全部为钢琴。对于曲式、和声、视唱练耳等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苗族声乐、器乐学生同其他学习西洋乐器或中国传统乐器或声乐的学生一样,清一色接受西方音乐理论的教学。受“欧洲音乐中心主义”的影响,贵州苗族音乐所特有的韵律、调式感逐步被同化,仅仅在专业技能课所体现的民族特色而缺乏同一体系专业基础课程的苗族音乐犹如无根之花朵,在西方音乐知识体系的影响下逐渐被“同一”,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日渐式微。在走访贵州大学时了解到,现阶段避免这种“同一性”比较困难。第一,目前这方面还没有合适的教材,即使有了教材也没有合适的授课教师。第二,由于人才培养方案学分设置的关系,无法对通识课程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将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的理论课程列为必修。如果强行将课程添加进去,从目前学生已排满的课表上看也难以实现。
由此可见,目前,贵州各高校苗族音乐教育使用教材的情况,从国编教材到校本教材,均是欧洲音乐体系下的形态逻辑,既没有适合的教材,也缺乏能够进行授课的教师。同时,由于非音乐类专业院校无法进行自主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因,苗族音乐在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中同音乐学其他专业无所差异,少数民族特色课程只能加入选修课,选择性地进行学习。这也是当下学院音乐教育“同一性”的强制性表现。
(二)各高校音乐学院中有关苗族音乐的专业设置普遍单一,教材建设薄弱
在课题组走访的五所高校中有关苗族音乐的专业设置情况如下:
贵州大学:苗族声乐演唱、芦笙。
贵州民族大学:苗族声乐演唱、芦笙、三眼萧、反排木鼓、盲桶、木叶、铜鼓。
贵州师范大学:芦笙。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苗族声乐演唱、芦笙。
凯里学院:苗族声乐演唱、芦笙、牛腿琴。
这五所高校中除去苗族声乐演唱,所设置的有关苗族器乐专业共6种,除去贵州民族大学以外,其余基本只有芦笙一种乐器,然而,贵州省内实际苗族器乐共14种之多。学校课堂开设的课程种类与贵州民族民间实际的音乐种类比例为6:14,这个数字怎么看都难以承担我们对贵州苗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任务。由于教材建设的薄弱,校园内所学习的作品数量与民间传习的数量比例更加悲观,各学院中有关苗族音乐的专业设置普遍单一,教材建设薄弱,音乐学成果没有及时转化为教育资源,等等。都是目前学校教育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
(三)师资断层问题日渐严重
笔者在走访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时了解到,一些苗族乐器由于缺乏合适的授课教师无法在校内开设课程,或者一些引入高校比较优秀的民间老艺人由于过世等原因,教学内部出现了师资断层。如贵州民族大学孙婕博士在采访时所说:“现在传统艺人师资正在逐渐减少。很多老一辈的优秀传承人相继去世,如杨昌树教授,他确实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继续将芦笙音乐传承传播下去。但我们少数民族还有其他一些很多的传统乐器,这些传统音乐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承,一些精通传统文化的老艺人就去世了,可能他的一些学生学到了他的技艺,也有的学生还没有全部学习到这些老艺人的技法技巧,老人就走了,所以现在流失了很多原生态音乐。”
笔者在走访我国最大苗族聚居地黔东南地区时,凯里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潘晓芬副院长也说到:“凯里学院虽然目前还没有断层的现象,但的确我们也非常担心它的出现。我们有些教侗族音乐的老师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但接下来也没有合适的民间传承人招聘到高校。因为学历限制的原因,高校在招人时需要硕士或博士学位,民间艺人基本是没有太高学历的,本科毕业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们只能外聘,但外聘的课时费是非常低的,远不如他们在外边社会上的收入,也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可以说,很多外聘的民间传承人是怀着对自己民族文化传播的民族责任感而来。”
由此可见,苗族音乐在贵州高校传承教育中,对于师资队伍的建设还需进一步优化。
(四)学校教育“固化性”“再现性”特征,与苗族民间乐歌“开放性”“创造性”的冲突
学校教育的“固化性”体现在教材使用的时间与空间的“固化性”。经过调研,目前高校所使用的教材大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编写的,可以说,这些曲目已经固化那个年代以前。而经过实地调查表明,苗族民间乐歌的唱奏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创新。即便同一位演奏者演奏同样一首曲目,根据表演场合的不同,演出形式的不同,甚至表演者情绪状态的不同,都有可能演奏出不同的音乐文本,几乎不受时间“固化”的限制,而在学校教育模式开展下的“照谱唱奏”显然不符合这种艺术表演形式。此为时间上的“固化性”。以飞歌为例,在贵州黔东南、黔西北、松桃等地区对于飞歌的演唱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即便同一地区不同支系对于飞歌的演唱也会有所差异,而学校教育往往将其固化在某一个地区。此为空间上的“固化性”。
学校教育的“再现性”是指对教材内容这种相对稳定知识的学习,将对教材内容的再现作为主要的学习目的。这种“照谱唱奏”与苗族民间音乐“口传文本”的方式相悖。在欧洲音乐教育模式的影响下,东方音乐的“口传心授”“死谱活唱”难以存活,它与苗族音乐民间习得行为的“五缘”格格不入。[1]根据原定基、张应华等人的前期相关研究,苗族音乐具有“依景活用”“曲无定曲”等特征,具有“开放性”与“创造性”的艺术表演形式。
二、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建议
(一)借鉴西方理论技法,寻求“多样态”的教育模式
首先,有关“构建中国音乐理论基本体系”早已是许多学养深厚的前辈学者一直所殚精竭虑的事情。杜亚雄先生曾说过:“中国乐理充满了辨证精神,‘声可无定高’‘拍可无定值’‘死谱活奏’‘死音活唱’,中国传统音乐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表述系统。”[2]在苗族音乐文化中也强烈了体现了这一点。但完全脱离西方音乐理论框架也绝非是一个进步的行为,西方先进的理论技法值得借鉴。笔者认为,新时代下我们应当助推“民族特色”与世界音乐交流,既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全盘的西化。立足于传统,将“欧洲音乐中心主义的立场”转化为“借鉴西方理论”,摆脱学院模式对民间习得行为的同化,将民间习得的价值、意义以及功能等文化特征纳入到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教学设计及研究项目,寻求“多样态”的教学策略,才是让苗族音乐走向世界,传播苗族音乐文化的出路。
其次,为包含苗族音乐在内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专业争取自主招生的权力。因贵州各大高校通识课程的设置几乎完全一样,其中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理论的课程在必修课表中为零,只有为数不多的特色课程出现在选修课表中。然而综合类高校的限制,学校没有自主设置通识课程的权力,因此建议为少数民族特色专业争取自主招生与自主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权力。同时,优化使用教材,在乐理、视唱练耳、曲式等课程中加入苗族音乐“语汇”与“素材”,结合民族音乐理论,寻求课程与教材“多样态”的编排,从而避免苗族音乐中特有的色彩、韵律、调式调感被后现代学校教育过度化的“正规”。
(二)增设有关苗族音乐的专业课程,推进教育资源的转化,力争学校场域更加全面地进行苗族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
贵州民间的苗族乐器主要分为管乐乐器、弦乐乐器、打击乐器三大类。管乐乐器有芦笙、芒筒、夜箫、姊妹箫、笛、唢呐等;弦乐乐器有二胡、古瓢琴、月琴等;打击乐器有铜鼓、木鼓、和皮鼓等;此外还有板凳、木叶等,14种以上乐器。经过调研发现,除贵州民族大学在课堂开设6种乐器以外,其余院校有关苗族器乐的专业课程仅有芦笙一种,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悲观,甚至有些省直师范类院校在少数民族音乐专业建设上仍为空白。伍国栋先生曾说:“师范类大学对传统音乐教育的开展情况,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命运的把握。”同样,贵州省内师范类院校对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开展情况,也是对贵州省内少数民族音乐命运的掌握,缺少学校教育传承的少数民族器乐势必随着新时代文化生态的改变而逐渐消失。因此,应增设校园中有关苗族声乐器乐的课程开设,使其更加全面,尤其师范类院校务必重视对省内的少数民族音乐师资的培养。同时,加快教学与科研成果的转化,进行教学记录与利用创作,广泛收集民俗民间歌曲,推进苗族音乐教材的建设,更好地发挥高校的社会功能性,将我省的苗族音乐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三)重视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少数民族音乐师资队伍建设的接轨与契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非遗传承人作为自身民族音乐的局内人,能很好地洞悉其独特的风格与艺术精髓,同时,非遗传承人担负着传与承的双重任务,是高校少数民族音乐师资队伍建设的有益补充和人才资源库。但并不代表所有的传承人都可直接进入高校课堂教学。还应考虑课堂多媒体运用能力、课堂的调控能力、对成果理论性归纳和总结的能力、甚至普通话表达能力等各种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
而高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师因掌握更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更科学的唱奏方式可以很好地与之互补。作为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工作者,除了抓好自身教学以外,也应尽力帮助民间音乐传承人适应高校的相关教学,对非遗传承人进行分类指导。[3]依托现有的继续教育资源,如“国培计划”对民间传承人进行教学技能方面的培训,不断帮助民间传承人提升教学手段、更新教育观念,实现传承人与高校少数民族音乐师资队伍的有效接轨,是我们应当不遗余力探索的方向。
此外,我国非遗传承人具有年龄大、技艺高,但文化水平较低这种“两高一低”的特征。而高校的学历门槛最低都在硕士以上,民间艺人很难通过正常应聘渠道进入到高校当中。而以外聘的形式除收入较低以外,同时民间艺人,通常将其看作副业,对教学的效果质量难有过高要求,因此,在高校范围内普遍出现了师资断层的问题,或者成为将来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基于以上,建议高校在吸收民间传承人进校园时,放宽对学历学位的限制,灵活吸纳教师,避免师资断层或以外聘的形式聘请民间传承人。
(四)在原生态民族特色地区建立田野课堂基地,打破高校少数民族音乐课堂相对“封闭”的空间,实行“田野课堂+校园课堂”结合的教学新模式
尽管一些高校采用课堂教学与民间歌乐师传习的形式进行学习,尽可能多的参与民俗活动,但学生对民间苗族音乐的风格把握依旧远远不够,难以让学生对苗族音乐文化的“真实性”和“活态性”有切身体悟和身体实践。因此,将过去单一的课堂授课模式改为“田野课堂+学校课堂”新模式,从而构建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参与式研究性学习新模式,是我们将面临探索的道路。具体实施建议如下:
在田野上建立传统音乐课堂,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与当地的文化部门进行沟通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在原生态民族特色地区,如黔东南、黔西北等地,建立田野课堂实践基地,并将当地传承人、民间歌乐师请入课堂进行授课教学。应牢牢把握本科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大方向,将学生主体作为整个实训的核心,课程教学从大学课堂延伸到原生态地区再结合到校园课堂,力争将苗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学习构建成为一种更“接地气“的、不脱离民族民俗文化环境的文化传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