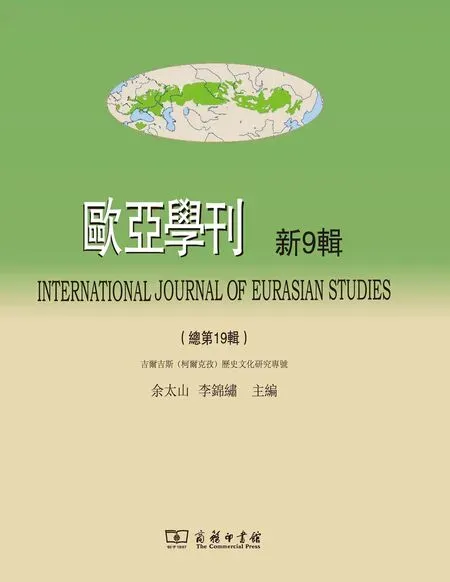黠戛斯“朝貢”考
朱蕭靜
黠戛斯與唐朝交好。據中文史籍記載,從貞觀直至咸通年間,黠戛斯“朝貢”多達十九次。本文以《冊府元龜·外臣部》中的史料爲主,輔以其他傳世文獻,從黠戛斯“朝貢”與漠北的政治軍事形勢、黠戛斯的貢物與唐的酬答之物、唐與黠戛斯的社會文化交流這三個方面展開,探討唐朝與黠戛斯的關係及其影響。
黠戛斯,兩漢時期曾稱爲“鬲昆”、“堅昆”,魏晉南北朝時期則被稱爲“結骨”或者“契骨”,至隋唐時期,則有“紇骨”、“居勿”、“堅昆”和“紇扢斯”等多種稱謂,後譯爲黠戛斯。黠戛斯主要活動在劍河(今葉尼塞河)上游沿岸,以及貪漫山(今唐努烏拉山東南峰)以北一帶。
近年來,學界對唐與黠戛斯的關係進行了較多的研究。內蒙古大學王潔的《黠戛斯歷史研究》是黠戛斯研究最全面的成果,其中探討了黠戛斯與唐、突厥和回鶻之間的關係。a王潔:《黠戛斯歷史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鄭元瓏《隋唐時代黠戛斯部與中原王朝關係初探》一文,論述了隋唐時期黠戛斯與中原王朝關係的發展變化。b鄭元瓏:《隋唐時代黠戛斯部與中原王朝關係初探》,《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4 期。甘長新《貢賜體系下的黠戛斯與唐朝關係》一文,提出了黠戛斯與唐之間的關係既有與突厥、薛延陀和回鶻之間的相似性,又有其獨特性的觀點;認爲黠戛斯和唐朝自始至終保持了和平關係是與地理環境和唐朝當時的羈縻政策有關,遣使和貢奉是二者貢賜關係的具體體現。c甘長新:《貢賜體系下的黠戛斯與唐朝關係》,雲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賀繼宏《黠戛斯汗國及其與唐王朝的關係》著重敘述黠戛斯擊潰回鶻以後與唐朝的交往。d賀繼宏:《黠戛斯汗國及其與唐王朝的關係》,《西域論稿續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187—198 頁。此外,日本、美國學者也多有研究。中島琢美對會昌年間黠戛斯使唐的資料進行了系統梳理a中島琢美:《會昌年間に於けるキルギス使節団の到来に就いて(一)》,《史游》10,1983 年,第5—16 頁。,齊會君詳細分析和考證了四份會昌年間由唐廷發給黠戛斯可汗的國書以及它們的起草過程b齊會君:《唐のキルギス宛國書の発給順と撰文過程》,《東洋學報》第100 卷1 號,2018 年,第1—31 頁。。Michael R. Drompp 以李德裕起草的四份與黠戛斯可汗書和黠戛斯使者會昌年間的四次來訪爲基礎,詳細分析了唐與黠戛斯的關係。cMichael R. Drompp,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pp.125-158.這些都奠定了唐與黠戛斯朝貢關係研究的基礎。
在唐與黠戛斯的關係中,朝貢始終爲一條主線,本文將在此基礎上,以《冊府元龜》的記載爲中心,參照其他傳世文獻,對黠戛斯的朝貢做進一步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請方家指正。
一、唐代黠戛斯“朝貢”史料簡析
《冊府元龜》爲北宋時期編纂的政事歷史百科全書性質的史學類書,其《外臣部》中有較爲詳細的黠戛斯與唐朝貢賜關係的記錄。現將這些材料按照年代整理分析如下:
史料一:《冊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貞觀]二十二年正月朔,結骨、吐蕃、吐谷渾、新羅、高麗、吐火羅、康國、于闐、烏長、波斯、石國,并遣使朝貢。”d(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鳳凰出版社,2006 年,第11231 頁。
史料二:《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入覲》:“[貞觀]二十二年二月,以結骨部置堅昆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以其侯(俟)e據《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 年,第6148 頁)、《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貞觀二十二年正月”條([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中華書局,1956 年,第6252 頁)改。利發失鉢屈阿棧爲左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初,結骨未嘗通中國,聞鐵勒等咸來內附,即遣使頓顙稱臣,并獻方物。至是,其君長遂自入朝見。太宗於天成殿宴之,謂群臣曰:‘往日渭橋斬獲三突厥,自謂多功,今致此人於席,翻更不以爲怪,可謂日用而不知邪?’結骨酣醉,歡甚,因謂曰:‘臣既一心歸國,願授國家官職,執笏而還。’故授以此任,并賚錦帛。”f《冊府元龜》,第11555 頁。這條史料中所敘述的朝貢,應與上一條的史料相聯繫,應爲同一次朝貢。
史料三:《冊府元龜》卷第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上元]二年二月,堅昆獻名馬。”g《冊府元龜》,第11233 頁。
史料四:《冊府元龜》卷第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景龍]二年春正月,吐谷渾,三月,波斯,十一月,堅昆,并遣使來朝。”h《冊府元龜》,第11234 頁。王潔認爲黠戛斯來使實際發生在景龍三年(709)。她指出《冊府元龜》敘景龍二年事時,首起月份就爲十二月,接著却是四月、六月、七月以及十月,月份排序混亂,而其記載的景龍二年七月丙辰突厥鼠尼施及突騎施來降之事,在新、舊《唐書·中宗本紀》均記爲景龍三年,因而她推斷《冊府元龜》景龍二年的史料應爲景龍三年者。由於《冊府元龜》中此段時間記載較爲混亂,茲據史籍及陳垣《二十史朔閏表》簡單梳理并考證如下:《冊府元龜》“景龍二年”條下記載:“四月己亥,右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濛池都護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加特進,祿料并依品給。”據《二十史朔閏表》,景龍二年的四月并沒有己亥,而三年的四月則有,則加封阿史那懷道的時間應在景龍三年。下條:“六月丙寅,吐蕃使宰相尙欽藏及御史名悉獵來獻,賜一書,帝御承天門樓,命有司引見,置酒于殿內享之。”據《二十史朔閏表》,景龍二年六月有丙寅,三年六月則沒有丙寅。《新唐書·吐蕃傳》記載:“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則這一批請婚的使者,很有可能就是《冊府元龜》中記載的景龍二年六月丙寅前來朝貢的這一批使者。下條:“七月丙辰,突厥鼠尼施首領參布,及突騎施領賀勒哥羅來降,命有司宴之,各賜帛五十匹。” 此事如王潔所論,當據新舊《唐書·中宗本紀》及《資治通鑑》定爲景龍三年。回到“景龍二年十二月丙申,宴堅昆使于兩儀殿,就其家弔焉”上來,據《二十史朔閏表》,景龍二年及三年十二月均有丙申,而且其他傳世文獻中也并沒有記載景龍中黠戛斯入貢的確切時間。因而此事是否如王潔所考證發生在景龍三年,還值得商榷。
史料五:《冊府元龜》卷第九七四《外臣部·褒異》:“[景龍]二年十二月丙申,宴堅昆使於兩儀殿,就其家弔焉。”a《冊府元龜》,第11275 頁。
史料六:《冊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褒異二》:“[開元十年]九月己巳,大拂涅靺如價及鐵利大拂涅買取利等六十八人來朝,并授折衝,放還蕃。突厥大首領可還拔護他滿達干來朝,授將軍,放還蕃。堅昆大首領伊悉鉢舍友者畢施頡斤來朝,授中郎將,放還蕃。”開元十一年時,堅昆再一次來朝:“[開元十一年]十一月甲戌,突厥遣其大臣可邏拔護他滿庭干來朝,授將軍,紫袍金帶,放還蕃。堅昆大首領俱力貧賀志頡斤來朝,授郎將,放還蕃。”b《冊府元龜》,第11281 頁。
史料七:《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開元十二年]十二月,越喜靺鞨遣使破支蒙來賀正,并獻方物。突厥遣使裴羅啜來朝。堅昆遣使獻馬。”c《冊府元龜》,第11239 頁。
史料八:《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天寶六載]四月,突厥九姓獻馬一百五十匹,堅昆獻馬九十八匹,波斯遣使獻瑪瑙床。十二月,九姓堅昆及室韋獻馬六十匹,令西受降城使印而納之。”d《冊府元龜》,第11243 頁。《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錄》記載:“天寳六載十二月,九姓堅昆及室韋獻馬六十匹,令於西受降城使納之。”(第1303 頁)但《玉海》卷一四九《兵制·馬政下》“唐八坊”等條引《會要》作“六千匹”([宋]王應麟輯:《玉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1988 年,第2729 頁)。
史料九:《冊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五》:“武宗會昌二年二月,牂牁、南平蠻、結骨國遣使朝貢,室韋大首領熱論等來朝。e會昌二年結骨來朝事,《資治通鑑》卷二四六記載爲會昌二年十月,其文云:“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第7968 頁)據李德裕撰《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143—144 頁),知此次來唐者有“踏布合祖達干遏悉禾亥義、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己時等七人”。《冊府元龜》所載二月不確。因《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云:“(會昌二年二月)牂柯、南詔蠻遣使入朝。”(第590 頁)“(八月)上御麟德殿,見室韋首領督熱論等十五人。”(第592 頁)則室韋并不是與牂柯、南詔蠻一樣,在會昌二年二月來朝。《唐會要》卷九六《實韋》云:“會昌二年十二月,上御麟德殿,引見室韋大首領都督熱論等十五人,宴賜有差。”似更準確。因而《冊府元龜》此條似可還原爲:“武宗會昌二年二月,牂牁、南平蠻遣使朝貢。十月,結骨國遣使至天德軍。十二月,室韋大首領熱論等來朝。”三年八月,黠戛斯遣使諦德伊斯難珠來朝。”f《冊府元龜》,第11252 頁。
《冊府元龜·外臣部》中總計記載了黠戛斯10 次朝貢的情况。
其他傳世文獻,也記載了一些《冊府元龜·外臣部》中未能收錄或內容不同的史料。
在《冊府元龜·外臣部》中,黠戛斯與唐朝在貞觀二十二年(648)第一次有了交往,黠戛斯的君長親自入朝,并被冊封爲左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但是其實早在貞觀六年(632)和十七年(643),黠戛斯與唐朝就已經有了直接的往來。《唐會要》卷一〇〇《結骨國》記載:“貞觀六年,遣王義宏將命鎮撫。”a(宋)王溥:《唐會要》,中華書局,1955 年,第1784 頁。又《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黠戛斯》記載:“唐貞觀六年太宗遣偃師尉王義宏使其國,十七年,堅昆遣使貢貂裘及貂皮。”b(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黠戛斯》,中華書局,2007 年,第3820 頁。此可補充《冊府元龜》之記載。
唐高宗在位時,黠戛斯一共朝貢三次,其中之一是前述《冊府元龜》所載上元二年(675)的“堅昆獻名馬”,一次發生在永徽四年(653),“永徽四年,又遣使朝貢,仍言:‘國內大有中國人,今欲放還,請一使受領。’高宗遣范強多齎金帛往仍處分,云但有人即須贖”c《太平寰宇記》,第3820 頁。。還有一次是上元三年(676),“(二月)乙亥,堅昆獻名馬”d(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中華書局,1975 年,第101 頁。。
关於會昌年間黠戛斯使唐,《唐會要》、《資治通鑑》可補充和修正《冊府元龜》所記。
《唐會要》卷一〇〇《結骨國》記載:會昌三年“二月,遣使注吾合索等七人來朝,貢名馬,且憑大唐威德,求冊命焉”e《唐會要》,第1784 頁。。《資治通鑑》记載更爲详细:“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十五日),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f《資治通鑑》卷二四七“會昌三年二月辛未”條,第7973 頁。。据《通鑑》,知注吾合索來唐時间在二月辛未(十二日)。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會昌三年(843)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g《資治通鑑》,第7985 頁。。此條《冊府元龜》未載,可为補充。據李德裕撰《與黠戛斯可汗書》,知溫仵合等“獻馬百匹,鶻十聯”h《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第83 頁。。
同書同卷又記載:會昌四年(844)二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并依回鶻故事’”i《資治通鑑》,第7999 頁。。諦德伊斯難珠來朝事,《冊府元龜》繫於會昌三年八月。齊會君考證四年二月應爲準確日期,因李德裕起草《賜黠戛斯書》中,有“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并存問之”j《冊府元龜》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第11350 頁。句,应爲二三月,故《資治通鑑》的时间準確。k齊會君:《唐のキルギス宛國書の発給順と撰文過程》,《東洋學報》第100 卷1 號,第11—12 頁。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賜黠戛斯書》中提到了黠戛斯可汗的書信中說:“溫仵合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l《冊府元龜》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第11350 頁。這說明會昌三年六月朝貢的溫仵合將軍已然歸國,之後諦德伊斯難珠才從黠戛斯啟程入朝,這中間僅相隔兩個月的時間,從當時的交通狀况來看是并無可能的,所以諦德伊斯難珠只能是四年二月入唐的。另據李德裕《賜黠戛斯書》,知諦德伊斯難珠獻“白馬兩匹”a《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第88 頁。。
會昌之後,《冊府元龜》記載闕如。實際上,黠戛斯仍多次遣使來唐。《崔鐬墓誌》記載:
先帝時,丞相龜從一日于便殿言府君之屈,即日擢拜權知鴻臚卿,久而得真秩。時黠戛斯遣使朝貢,有稱敕使者,府君曰:“是必重譯之失也。以此名號奏御,于理未安。”乃命舌人言覆,果曰隻,使聲之悮也。其爲精識,又如是。b《唐故朝請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守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鎮遏使上柱國博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左散騎常侍崔府君(鐬)墓誌銘并序》,《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403—405 頁。
崔龜從在大中四年(850)六月至大中五年十一月任宰相c《新唐書》卷六三《宰相表》,第1731 頁。,崔鐬“擢拜權知鴻臚卿”當在這期間,一段時間之後真拜鴻臚卿。黠戛斯的“朝貢”正發生在崔鐬任鴻臚卿期間。墓誌中并未記載崔鐬任鴻臚卿的時間,但從“久而得真秩”看,其“權知”的時間應該不短。據此推測,黠戛斯來唐的時間至少應在大中五年以後。黠戛斯這次來使,史籍中沒有記載,墓誌可補史籍之闕。
大中十年(856),黠戛斯再次遣使來唐。唐代詔敕中偶然提及了這次來唐的使臣之名。《請立回鶻可汗詔》云:
近有回鶻來款,朔方帥臣得之,送至闕下。又有回鶻隨黠戛斯李兼至。d(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一二八《議立回鶻可汗詔》,商務印書館,1959 年,第692—693 頁。此詔頒布時間,《唐大詔令集》作“大中十年二月”,《資治通鑑》卷二四九(第8059 頁)作“大中十年三月辛亥(八日)”。當以《通鑑》爲準。
可知大中十年,黠戛斯派使者李兼來唐,隨行的還有西遷回鶻使人。據此詔文和上引《崔鐬墓誌》,可知大中年間黠戛斯至少兩次遣使來唐。
咸通年間,黠戛斯遣使來唐的情况,《資治通鑑》記載了兩次:其一爲咸通四年(863)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e《資治通鑑》卷二五〇,第8107 頁。。此條史料雖未明確提及朝貢事宜,但黠戛斯遣使臣向唐朝上表求取經籍曆書以及提出了互市的要求,必然不會派遣臣子出使而不帶貢物。而咸通七年(866)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f《資治通鑑》卷二五〇,第8117 頁。,又一次使唐。《新唐書》記載,黠戛斯“逮咸通間三來朝”g《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第6150 頁。,據《資治通鑑》,只能補充兩次咸通年間黠戛斯“朝貢”的記載。隨著唐朝的力量越來越衰弱,“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a《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第6150 頁。,相關記載至此而止。
《唐會要》、《太平寰宇記》、《舊唐書》、《資治通鑑》補充了黠戛斯的9 次“朝貢”。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總結出黠戛斯来唐“朝貢”總計19 次。现将黠戛斯“朝貢”情况列表如下(見表1)。
二、黠戛斯“朝貢”與漠北的政治、軍事形勢
這19 次“朝貢”,大部分都集中在玄宗朝和武宗朝,其中玄宗在位時多達5 次,武宗在位時也有4 次。開元年間和天寶年間“朝貢”較多,一是因爲唐朝在這個時期正處於國力鼎盛的階段,“四方來朝”,周邊環境也較爲穩定,第二突厥汗國也向唐請和,黠戛斯通往唐朝的道路沒有阻隔,故可在開元年間連年“朝貢”。
而武宗會昌二年(842)十月的這次遣使來唐,與上一次天寶六載相距近乎百年,這百年間波折頻生。先是唐朝經歷安史之亂,國力不再,無暇再顧及四鄰諸國,甚至需要迴紇等出兵助唐平叛。另一方面,迴紇的實力不斷增強,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時就曾大破黠戛斯,之後黠戛斯甚至一度亡國。迴紇成爲漠北的實際統治者,阻斷了黠戛斯與唐朝交往的道路,造成了近百年的交流空白。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除唐朝與黠戛斯自身力量的消長以外,黠戛斯與唐朝的關係以及能否順利進行“朝貢”出使等交流活動,都與漠北的政治以及軍事形勢息息相關。a參見薛宗正:《黠戛斯的興衰》,《民族研究》1996 年第1 期,收入氏著:《迴紇史初探》,甘肅民族出版社,2012 年,第478—508 頁。
從南北朝時期開始,突厥就成爲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隋及唐前期均與突厥進行過激烈的博弈。武德三年(620),頡利可汗繼位,與唐朝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戰爭。武德九年(626),李世民甫一繼位,頡利可汗便發動戰爭,直抵長安西郊,唐太宗與其訂立城下之盟,才使得突厥退兵。在此之後,唐太宗勵精圖治,扶植鐵勒,分化突厥的勢力,終於在貞觀四年(630)消滅了東突厥汗國。
在東突厥汗國逐漸衰弱之時,薛延陀走上了歷史舞臺,并在東突厥汗國滅亡後稱雄漠北。唐曾利用薛延陀牽制東突厥,但在東突厥滅亡後不久,唐命已安置在河南的突厥餘部回到其原來的居住地,試圖牽制日益強大的薛延陀。薛延陀這個在貞觀初年建立的汗國并沒有存在很久,後薛延陀內亂,鐵勒諸部紛紛反叛。貞觀二十年(646),唐大舉反擊并滅亡了薛延陀汗國。同年八月,唐太宗至靈州,鐵勒諸部脫離了薛延陀的統治,紛紛歸附成爲唐的藩屬,唐太宗被奉爲天可汗,并於次年一月以鐵勒諸部置六都督府和七州,正式開啟了唐代建立羈縻州府的制度。
黠戛斯能夠在貞觀年間就與唐朝建立聯繫,很大程度就是因爲東突厥和薛延陀的滅亡。唐“貞觀六年,遣王義宏將命鎮撫”,正是因爲貞觀四年東突厥的滅亡,才使唐使者直達漠北,與黠戛斯建立聯繫。貞觀十七年(643),正是薛延陀強大之時,黠戛斯卻遣使進貢貂裘及貂皮,表明黠戛斯與唐的交往并未斷絕。貞觀二十二年(648),黠戛斯的君長親自入朝,被冊封爲左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并以結骨爲堅昆都督府,隸屬燕然都護。此事發生在唐太宗滅薛延陀、招撫鐵勒諸部之後,此時唐控制了漠北,建立了新的統治模式,黠戛斯也在唐羈縻體制之中。
永淳元年(682)第二突厥汗國復興,黠戛斯多數時間與之爲敵。突厥將政治中心遷到于都斤山後,得知唐、黠戛斯與突騎施想要聯合進攻突厥,便欲先發制人。景龍二年(708),突厥偷襲并一度征服了黠戛斯。a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101 頁。芮傳明認爲突厥西征黠戛斯發生在景龍三年冬季或翌年初春,見《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62—64 頁。但在東突厥復興的這幾十年間,黠戛斯一直與唐保持著親善關係,甚至助唐出兵攻打突厥,在《冊府元龜·外臣部》中就有關於黠戛斯在開元年間助唐出兵征討突厥的記載,“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等,弧矢之利,所向無前”b《冊府元龜》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討第五》,第11415 頁。,在《資治通鑑》中,也有關於開元六年(718)出兵征討突厥一事,但司馬光認爲五都督助唐征討突厥一事時間存疑c《資治通鑑》卷二一二“開元六年(718)二月”條《考異》,第6851 頁。,吳玉貴認爲此事應發生於開元八年(720)d吳玉貴:《第二突厥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中華書局,2009 年,第1039 頁。。但黠戛斯與唐之間通使之路并沒有被截斷。直至天寶年間,黠戛斯仍“朝貢”不絕。
黠戛斯與唐朝聯繫的中斷,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回鶻的從中阻隔。天寶四載(745)迴紇將突厥逐出漠北,取代突厥成爲了漠北的霸主。黠戛斯“乾元中爲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e《資治通鑑》卷二四六“開成五年(840)九月”條,第7946 頁。。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回鶻來朝,“九月甲申(十五日),迴紇使大首領蓋將等謝公主下降,兼奏破堅昆五萬人”f《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第5201 頁。。這時,黠戛斯已臣服於回鶻,回鶻封黠戛斯阿熱可汗爲毗加頓頡斤。另據《九姓回鶻毗伽可汗碑》記載,回鶻天可汗曾射死黠戛斯可汗,并大破其國,“堅昆可汗,應弦殂落,牛馬穀量,口械山積,國業蕩盡,地無居人”g林幹:《突厥與迴紇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440 頁。,然後回鶻又打敗了葛邏祿與吐蕃的聯合軍隊。《九姓回鶻毗伽可汗碑》記載的爲回鶻保義可汗在位時期的故事,故大破黠戛斯一事應發生在公元九世紀初。h林幹:《突厥與迴紇史》,第438 頁。
但是當回鶻衰弱之時,黠戛斯不斷發展壯大,阿熱自稱可汗,回鶻派遣宰相帶兵征討黠戛斯,卻屢戰屢敗,雙方交戰二十餘年不斷。至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回鶻將領句錄莫賀背叛回鶻,引導黠戛斯十萬鐵騎攻打回鶻,攻破回鶻牙帳,殺可汗以及宰相,并最終滅亡了回鶻汗國。i《資治通鑑》卷二四六“開成五年(840)九月”條,第7946 頁。黠戛斯則取代回鶻一躍成爲了漠北新的統治力量。
黠戛斯攻破回鶻之後,可直達唐北部邊境。唐武宗會昌二年(842)十月,黠戛斯遣踏布合祖將軍一行至天德軍,告知唐朝黠戛斯已擊潰回鶻之事,“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a《資治通鑑》卷二四六“會昌二年(842)十月”條,第7968 頁。,黠戛斯擬遷入回鶻故地,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大。之後,黠戛斯頻繁向唐朝進行“朝貢”,與唐朝的交往開啟了新局面。
會昌三年(843)二月,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兩匹,并向唐請求冊封。唐令黠戛斯自行帶兵尋求殺害使者的回鶻殘部以及討伐黑車子。b《資治通鑑》卷二四七“會昌三年(843)二月”條,第7974 頁。同年三月,唐武宗派遣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并命李德裕撰《賜黠戛斯可汗書》。c《資治通鑑》卷二四七“會昌三年(843)三月”條,第7975 頁。同年六月,黠戛斯再次遣將軍溫仵合入貢。d《資治通鑑》卷二四七“會昌三年(843)六月”條,第7985 頁。
會昌五年(845),唐廷準備正式冊封黠戛斯可汗。四月,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爲冊黠戛斯可汗使,詔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e《資治通鑑》卷二四八“會昌五年(845)五月”條,第8015 頁。但會昌六年(846)三月,唐武宗崩逝,派去冊封黠戛斯可汗的使者因爲國喪未能成行。f《資治通鑑》卷二四八“會昌六年(846)九月”條,第8026頁。後至大中元年(847)六月,唐宣宗終於派出鴻臚卿李業爲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g《資治通鑑》卷二四八“大中元年(847)六月”條,第8030 頁。
據《新唐書》記載,黠戛斯“逮咸通間三來朝”。但是我們現在只能看到兩次關於咸通年間黠戛斯朝貢的記載。隨著唐朝的力量越來越衰弱,“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資治通鑑》中最後一次記載黠戛斯和唐朝的往來是在唐昭宗大順元年(890)九月:“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h《資治通鑑》卷二五八“大順元年(890)九月”條,第8404 頁。參《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大順元年十二月”條,第744 頁。此時唐已近於名存實亡了。
黠戛斯與唐之間的交往與漠北的政治及軍事形勢息息相關,突厥與回鶻都曾是黠戛斯與唐朝之間通使的阻礙。但黠戛斯與唐從未兵戎相見,甚至在唐已然江河日下之時,稱霸漠北的黠戛斯仍希望得到唐的冊封。咸通後隨著唐朝日益衰微,黠戛斯與唐的關係也畫上了句號。
三、黠戛斯貢品與唐酬答之物
從黠戛斯的貢物中也不難看出,黠戛斯盛產良馬,貢物多以馬匹爲主。唐代黠戛斯朝貢19 次,其中提到朝貢物品的有9 次。而這9 次中,除了貞觀十七年黠戛斯進貢貂裘以及貂皮以外,剩餘8 次都是進貢良馬。其中天寶六載四月獻馬98 匹,十二月獻馬60 匹,會昌三年六月獻馬百匹,數量比較大。天寶六載“十二月,九姓堅昆及室韋獻馬六十匹,令西受降城使印而納之”i《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第四》,第11243 頁。。這次朝貢的馬匹,直接送入了西受降城,可能是用來充實邊鎮防禦了。
騎兵在唐初爲唐朝平定天下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a汪篯:《唐初之騎兵—唐室之掃蕩北方群雄與精騎之運用》,《汪篯隋唐史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第226—260 頁。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著手大規模地發展馬牧,改良馬種,并任命粟特後裔史訶耽負責馬牧工作,奠定了唐代馬政的基本格局b李錦繡:《史訶耽與唐初馬政—固原出土史訶耽墓誌研究之二》,《歐亞學刊》第10 輯,中華書局,2008 年,第261—276 頁。。開元天寶年間,即便唐朝處在國富兵強、“萬國來朝”的盛世之中,對外用兵也從沒有停止,尤其是在西域及漠北地區與吐蕃、大食和第二突厥汗國之間頻繁爭鬥,戰馬仍供不應求。
在平定安史之亂的戰爭中,騎兵的作用更不能忽視。楊炎撰《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和)神道碑》記載:
嗣子預,有霸王之略,好倜儻之奇。初以右武衞郎將見於行在,天子美其談說,問以中興。遂西聚鐵關之兵,北稅堅昆之馬,起日城,開天郎,特拜左衞將軍兼瓜州都督關西兵馬使,又遷伊西北庭都䕶,策茂勳也。c(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九一七《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中華書局,1966 年,第4829 頁。安史之亂期間,唐右武衛郎將楊預從黠戛斯徵調了大批戰馬作爲軍用物資,爲平定安史之亂貢獻頗多,故而受到唐肅宗的嘉獎。由此得知,唐朝對戰馬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黠戛斯進貢如此之多的馬匹,也是應唐朝的要求。而黠戛斯的良種馬,也應在唐代馬政的發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朝貢關係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史記》記載:“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慣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d(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中華書局,1988 年,第 3 頁。但是這并不是貢賜關係,而是單純的臣服與貢奉。一直到漢代,漢朝在獲得其藩屬國朝貢的同時,也會對其藩屬國予以冊封,贈以金印,這時貢賜才真正地完成。
在唐代,唐政府設立了鴻臚寺,專門管理外藩朝貢、通使往來之事。《唐六典》記載鴻臚卿、少卿之職:“凡朝貢、宴享、送迎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e(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八《鴻臚寺》,中華書局,2014 年,第504 頁。實際上,外蕃使者來唐,迎送、宴享、朝貢都會得到賜物,朝貢的賜物即是對貢物的酬答制度。f參見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959—962、965—967 頁。《通典》卷一三一《禮九一·開元禮纂類二六·賓禮·蕃主來朝以束帛迎勞》略云:
使者朝服出次,立于門西,東面。從者執束帛立于使者之南……使者宣制訖,蕃主進受幣。(采五匹爲一束。其蕃主答勞使,各以土物,其多少相准,不得過勞幣。勞於遠郊,其禮同。蕃主還,遺贈於遠郊亦如之。勞蕃使即無束帛也。)g(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中華書局,1988 年,第3367—3368 頁。
蕃主來唐在迎勞與辭還禮中享受束帛之賜。迎勞禮中的束帛只給蕃主。貞觀二十二年堅昆俟利發失鉢屈阿棧來唐時,唐應給予了迎勞束帛。外蕃使者告辭離開時,唐廷也會有賜物。《唐六典》卷一二內侍省“內府局令職掌”條記載“諸將有功,并蕃酋辭還,賜亦如之”a《唐六典》,第361 頁。,表明蕃使辭還時唐要給予賜物。
在宴享蕃使時,唐依然要給予賞賜。“皇帝宴蕃國主”的禮儀如下:
若有筐篚,舍人前承旨,降宣敕,蕃主以下皆再拜,太府帥其屬以衣物以次授之訖,蕃主以下又再拜。b《通典》卷一三一《禮九十一·開元禮纂類二十六·賓禮》,第3374—3375 頁。
這裏的“筐篚”,指的是賜物,主要是衣物。貞觀二十二年(648)堅昆俟利發失鉢屈阿棧來唐時, “并賚錦帛”;會昌三年(843)二月“黠戞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匹……[皇帝]乃命其使,見于內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c(唐)李德裕:《黠戛斯朝貢圖傳序》,《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二,第21 頁。。可見宴設賜黠戛斯使者的是“文錦”。前論的迎勞和辭還賜物,也應是錦綵。“賜蕃客錦綵”的構成:“率十段則錦一張、綾兩匹、縵三匹,綿四屯。”d《唐六典》卷三“金部郎中員外郎職掌”條,第82 頁。外蕃使者宴享、送迎所賜的正是這樣的錦綵,也可稱爲“錦帛”。
朝貢的酬答之物,也以絹帛錦綵爲主。關於納貢與酬答制度,《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二《蠻夷貢賦第二十六》“蕃夷進獻式”引唐主客式云:
諸蕃夷進獻,若諸色無估價物,鴻臚寺量之酬答也。e(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文物出版社影印,1987 年,頁73a。
外蕃貢獻無估價之物,鴻臚寺根據情况給予酬答之物;能夠估算價值的,則按價格給予更爲優厚的酬答。與宴賜“文錦”一樣,唐對黠戛斯進獻的酬答之物也是“錦綵”。
會昌二年(842)十月,黠戛斯使者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并未至長安,其所納貢物,應由邊州進行酬答。這種酬答外蕃之物,由中央統一撥付,送納邊州,用於酬答專項支用。“唐儀鳳三年(678)度支奏鈔”f大津透:《日唐律令制の財政構造》,岩波書店,2006 年,第33—48 頁。記載:
H7 -擬報諸蕃等物,并依色數送[納?]。其交州
8 都督府報蕃物,於當府折□□給(?)用。所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唐與黠戛斯的貢賜關係,也可以說是一種絹馬貿易關係。黠戛斯向唐進貢馬,唐給予貢使錦綵,同時又以錦綵絹帛支付馬價,作爲酬答。這種以貢賜名義進行的絹馬貿易,各以所有,以易所需,促進了雙方的經濟發展。
四、唐與黠戛斯的社會文化交流
黠戛斯與唐的不斷交往,也進入了社會文化層面,對雙方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對唐王朝來說,黠戛斯的歸附和通使,使唐朝的影響達到葉尼塞河流域,與黠戛斯的宗盟關係,使唐有效地維系了北方邊境的穩定。這對唐朝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都是有利的。
如上所論,黠戛斯貢品,主要是名馬,但隱藏在馬的光環之後,還有其他珍稀之物。如貞觀十七年(643),黠戛斯首貢貂裘與貂皮,此後貂裘、貂皮可能一直在黠戛斯的貢品中。會昌三年(843),和親回鶻的太和公主歸唐,“主次太原,詔使勞問系塗,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往賜”b《新唐書》卷八三《定安公主傳》,第3669 頁。。黠戛斯所獻的白貂皮、玉指環應是注吾合索帶來的,史料雖然只記載了注吾合索獻名馬兩匹,可以推知黠戛斯名馬之後還有其他如貂裘、貂皮、指環等罕見之物。這些貢品在唐代屬於珍稀難得之物,唐帝多賞賜高官貴族,豐富了唐代貴族階層的生活。
由於雙方的交往,黠戛斯進入了唐朝的視野。來往於兩地的使者和商人,將黠戛斯的風土民情、奇聞異事帶回中原,豐富了漢文文獻的記載。黠戛斯的使者成爲《王會圖》、《朝貢圖》描寫和繪畫的對象,并專門形成了《黠戛斯朝貢圖傳》c《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地理類》有“呂述《黠戞斯朝貢圖傳》一卷”,第1508 頁。的著作。此《傳》由宰相李德裕作序d《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二《黠戛斯朝貢圖傳序》,第20—22 頁。,《圖》及《傳》進呈武宗,武宗對此深感滿意,稱“深愜於懷”e《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一九《謝宣示進黠戛斯朝貢圖深愜於懷狀》,第371 頁。,朝野上下爲之震動。黠戛斯的來使,擴大了唐人的認知。
對黠戛斯來說,與唐朝的交往更是對黠戛斯社會和文化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由於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黠戛斯實行兩種官制。其中一種繼承了北方民族的官制傳統,最高統治者稱爲可汗,可汗下設特勤、匐、葉護、梅祿、俟斤、頡利發、達干、設(殺)等,但是否有定員以及對應的職責卻沒有明確記載。另一種官制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體係,“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員”a《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第6148 頁。。宰相下有都督、刺史、將軍,還有長史、司馬等官,但很多官職并非完全照搬,只是借用而已。b王潔:《黠戛斯汗國政治制度淺析》,《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3 期。黠戛斯來貢唐朝的使者中,擁有具體姓名的有9 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貞觀二十二年(648)親身入唐的黠戛斯君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并被冊封爲左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體現了黠戛斯對唐的欽慕之心以及唐太宗將之納入漠北羈縻體制的意圖。另外兩位地位較高的朝貢使者爲開元年間來朝的伊悉鉢舍友者畢施頡斤和俱力貧賀志頡斤,頡斤的等級要低於俟利發,但依然是有影響力的部落首領,他們的來朝,正是唐朝開元盛世的一種體現。之後會昌以及咸通年間來朝的使者,便不再有如此高的等級,其中,有具體官職的有4 位,都是將軍,另外兩位使臣則沒有記載他們具體的官職。安史之亂後,唐國力日益衰微,黠戛斯雖依然重視中原王朝,請求唐朝冊封以正式確立自己在漠北的政治地位,但是如唐初以及盛唐時期的首領入貢卻是再未出現,這也可能正是大唐江河日下的一個縮影。
據《資治通鑑》記載,黠戛斯曾兩度入朝求取曆法。《新唐書》記載:“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c《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第6147 頁。黠戛斯人稱“月亮”爲“哀”,指代突厥的“陰曆月”,黠戛斯人稱歲首爲“茂師哀”,在古突厥文中爲“開頭的月”d王潔:《黠戛斯文化管窺》,《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 年第4 期。,即中原人所說的正月,可見黠戛斯以往應使用的是突厥人的曆法。但在咸通四年(863)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e《資治通鑑》卷二五〇,第8107 頁。。咸通七年(866)十二月,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f《資治通鑑》卷二五〇,第8117 頁。。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至少在咸通年間,黠戛斯是在使用唐朝的曆法,雖然不知唐朝曆法在黠戛斯沿用了多長時間,但是新的曆法畢竟對黠戛斯部族社會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在日常生活層面,唐朝的影響也可以推見。據《新唐書》記載,黠戛斯部落的貴族穿著貂、豽製作的衣服,底層人民著皮衣,女子穿毛、褐織品,但也有錦和綾織品,“女衣毛褐,而富者亦衣綾錦,蓋安西北庭及大食貨易所得也”g《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黠戛斯》,第3822 頁。。上文已論,錦、綾都是“賜蕃客錦綵”的組成部分,因此黠戛斯自貞觀至天寶年間,當從唐領得不少錦、綾等賜物。會昌年間,唐宴設黠戛斯使者,也賜以文錦。因此重視錦,可能和貞觀以來黠戛斯與交往中受唐服飾影響有關。黠戛斯上層喜著綾錦織造的衣服,體現了對唐文化的欽慕。
唐與黠戛斯的經濟貿易往來也不能忽視。《唐會要》記載了這樣一道敕令:“九姓、堅昆諸蕃客等,因使入朝身死者,自今後,使給一百貫,副使及妻,數內減三十貫。其墓地,州縣與買,官給價值。其墳墓所由營造。”a《唐會要》卷六六《鴻臚寺》,第1151 頁。這些入朝的黠戛斯人中,有不少隨使者入唐貿易的商旅,這些蕃客攜家屬來唐,故而敕令中也提到了其“妻”。這些黠戛斯商人可能在中原停留的時間較長,亦或已定居在中原進行貿易活動。
來唐使者和商人往來於遙遠的兩地,將中原的種種文化習俗、衣著時尚傳播至遙遠的葉尼塞河流域,并獲得當地上層人士的喜愛。這對於黠戛斯社會生活和文化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黠戛斯與唐的經濟文化交流,對雙方是互利共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