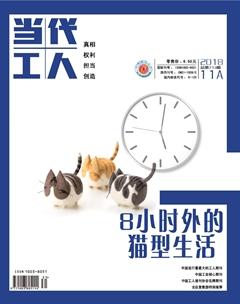工厂俱乐部:那些专属工人的欢乐时光
张瑞
暮色降临,穿过斑驳的光影,我从沈阳市的铁西沈重文化广场出来,沿着车水马龙的兴华北街向南,走到北二马路十字路口时,我看到西南角有一座老建筑,它的上端写着“沈阳工人会堂”。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是原来沈阳电缆厂的工人俱乐部。在一座座流光溢彩的商厦衬托下,它像一个佝偻的老者蜷缩在那里,落寞地注视着来往的车辆和行人。看到这一景象,我的眼睛不由一热。啊,逝去的岁月里,我不知在这里看过多少次电影,几十年过去了,大多老建筑已荡然无存,想不到它还在这里。久违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沈阳被称为“重工业之都”。提起工厂俱乐部,从小时候到参加工作,我数不清在多少个工厂俱乐部看过电影。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有机床一厂、拖拉机厂、冶修厂、三三零一、机床三、标准件、桥梁厂、化工厂、蓄电池厂、变压器厂、高压开关等,至于重型厂、电缆厂、冶炼厂等这样大型企业的俱乐部就更不用说了。仔细算下来,我至少在二三十家有名有号的工厂俱乐部里看过电影。那时给我的感觉是,凡是大的工厂都有俱乐部,没有俱乐部的工厂就不是大厂。后来,在铁西区的一份档案资料中我了解到,从1949年到1988年,铁西区的工厂俱乐部竟有80多家。
我能去这么多俱乐部看电影,缘于得天独厚的居住环境。我家住在工人村,在这个工人部落里,同学都是各个大工厂的工人子弟。
小时候,我家隔壁有个邻居,我叫他杨叔。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杨叔是一个挺大的官,后来我才知道,杨叔只是工廠俱乐部的主任。但不管是什么主任,我就觉得杨叔特能耐,了不起。
一到节假日,我老爱在杨叔家的窗底下转悠,转悠转悠我就把杨叔转悠出来了,这正是我最盼望的一刻。杨叔会面带微笑地走到我跟前,但那会儿我关注的不仅是杨叔的笑容,还有他的手。我会一直盯着他的手,看他伸进衣兜里,再慢慢地从里面掏出一个折叠着的小纸条,他将小纸条缓缓地展开。啊,电影票!每到这时,杨叔就会给我两场或三场电影票,有时还会一场给两三张。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约上小伙伴,到工厂俱乐部去看电影。当然,我也因此得到了小伙伴们的回报,他们也会隔十天半个月地带着我,去他们父母的工厂俱乐部看电影。
这些俱乐部中,规模最大的属沈阳冶炼厂俱乐部。据资料记载,建筑面积达4600平方米,有座位1760个。机床一厂文化宫的座位是最多的,共1870个,不过它的规模与冶炼厂俱乐部相比小了很多,建筑面积才有2600平方米。据统计,在当时的铁西,建筑面积超过千平方米、座位过千的工厂俱乐部有30多个。在这些俱乐部中,我一直认为重型厂文化宫是最好的,不但大而且还漂亮,甚至比当时市里许多大型电影院要好得多。尤其是观影大厅穹顶的葵花大灯特别典雅,可以同当时沈阳最好的东北电影院媲美。用现在的话说,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那时,有许多工厂俱乐部对社会开放。也许你不经意间走进哪个胡同,就会遇到一个工厂俱乐部。若是赶巧这场电影的票不太紧张,你可以花一毛钱买票进去,就能美美地看一场电影。
看电影在那时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也属于搞对象谈恋爱的规定曲目。男女之间有了暧昧或确立了恋爱关系,都愿意往电影院钻。如果有年轻人送一张电影票,约你看电影,那大概就是对你有点儿意思了。我和我老婆当年搞对象时,也是以约看电影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第一次看电影时,到厂文化宫里按票找座位,两个人中间隔着个过道,像是条三八线把我俩分开了。这电影还咋看,开演不到10分钟,我就把她从三八线那边拉出了电影院。与其让三八线隔着,不如进行双边会谈,我和她用看电影的时间,在兴华街通往工人村的路灯下,轧了两个多小时的马路。
为补偿那次没看成电影的缺失,后来的国庆节之夜,我俩在厂文化宫看了场通宵电影,一夜演4个电影,看到第三个电影时就困得迷迷糊糊了。现在想起来是真过瘾。
工厂俱乐部不只是看电影的地方,也是召开职工大会、举办职工文化活动的场所,所以它也是一个工厂人心聚集的地方。
以我上班的沈重为例,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大会,如职工代表大会、年终总结表彰会,还有一些逢年过节各类文艺活动。工厂有3万多职工,会场容纳不了那么多的人,只能是班组长、工会组长以上人员参加。“六一”儿童节时,厂子弟小学的孩子也会来这里看电影,表演他们的文艺节目。
在厂文化宫的两侧大厅,还张贴着光荣榜,悬挂着厂劳动模范戴红花的大照片。
1987年,我们厂在文化宫举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职工万人艺术展,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的创作热情。不仅有美术书法、摄影剪纸、编织工艺,还有很多从未见过的创作作品。如此大规模的职工文化活动,引起了省市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争相报道。记得我当时报道的标题是这样写的:《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凡是有俱乐部的工厂,基本上都组建了工人文艺宣传队,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带着自编的歌舞、样板戏等文艺节目,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在许多大厂,文艺宣传队都有着良好的传承,工厂投入了很多的财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艺活动积极分子。他们不但在厂内演出,还到社会上表演。当国家有重大活动时,经常会在家属区看到有两三辆解放车拼成的舞台,工厂文艺队的演员,以饱满的热情,为居民表演器乐、歌舞、快板、样板戏等节目。
说到演样板戏,大都是演《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唱段。一些中小工厂的文艺宣传队,因为没有那么多演职员,也没有足够的配合和组织能力,只能排其中的几个选段,或者一幕两幕。只有大厂才能排出全本8场戏。
当时我们厂文艺队演的样板戏,在社会上被认为达到了专业水平。因为特意从京剧团请了专业导演来指导,并对具有文艺特长的,或者是从文艺团体下放工厂的,都给了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在市、局举办的职工文艺汇演中,我厂演出的节目总是能获一些大奖,在社会树立了很好的口碑,为工厂赢得了荣誉。因此,一些演员在工厂被明星一样看待,走在厂区里总能吸引许多眼球,一些年轻貌美的女演员还被称为厂花。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下岗潮的袭来,许多国有企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下滑,那些大大小小的工厂俱乐部、文化宫也失去了活力,在被关停闲置后,成了企业的包袱。
再后来随着城市改造,工厂西迁,那些工厂俱乐部也被拆除了。
在拆除沈重文化宫那天,现场外围了很多人。有许多头发花白的老工人,还有一些老年夫妻结伴而来。随着轰鸣的机械声,有的人眼含热泪。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妇人抹着眼角说,当年他和死老头子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一位老职工说,他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是厂团委组织的集体婚礼。
写这篇文字时,我采访了原沈重厂的老工友宋敬泽,他是中国工业遗产影像(航拍)專项记录发起人,沈阳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他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在厂文化宫拆掉前的一天,他去文化宫拍照,步入走廊大厅时,里面传来了乐器的声音。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缓缓地走了进去。只见杂物堆积的舞台一角,一个人正在吹萨克斯管。在这个人的头顶上,一束耀眼的光从破漏的天棚上斜射下来,穿过尘埃笼罩在他花白的头上。那一刻,就感觉如同穿越时空隧道一般,饱含深情的乐曲把宋敬泽带回了那火红的年代。当这个人又吹奏了一曲《英雄赞歌》后,深深被感染的他才走上前去。那个人充满沧桑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花。原来他是炼钢分厂的退休工人关师傅,曾经在这里演奏过,今天他以这种方式,向即将消失的舞台致敬、告别。
当夜幕低垂,如果你来到灯火辉煌的沈重文化广场,会看到许多退休的老工人在跳舞、唱歌、吹奏乐曲。也许他们中就有像关师傅那样的退休老工人,虽然都已芳华不再,两鬓斑白,但他们的心中仍珍藏着那份青春的情怀。
俱乐部的消失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在家家有电视、甚至有家庭影院,到处有舒适电影厅的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的商业文化场所琳琅满目,谁还能去俱乐部看电影?
那么,就让曾经承载着欢乐时光和美好记忆的俱乐部,在温馨的感怀中留存吧。真想和老伴再回到当年的俱乐部看场电影,哪怕是隔着过道也行。
【典典滴滴】
工人文化娱乐活动空间的消失和内容的改变,映射出改革开放、社会变迁之下,工人群体的经济及社会地位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工人的文化娱乐生活比较单一,以看电影、看演出等集体性活动为主,工人俱乐部是他们活动的主要空间。在当时全国经济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这样的公共文化场所令社会其他成员羡慕。随着大批国企效益下滑,破产重组,工厂内工人的文化活动空间逐渐隐退甚至消逝,工人群体的文娱生活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下象棋、打麻将、晨练成了主要方式,工人文化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当下企业发展,工人的文娱活动再次受到重视,摄影、团建、健排舞……工会与时俱进地推动着工人文化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