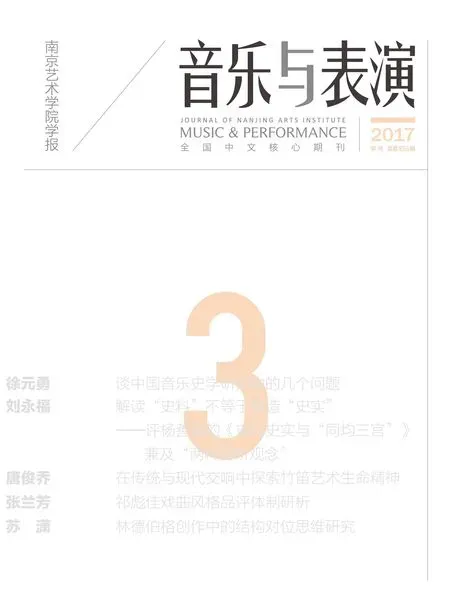论越剧在南京的传播与发展①
张婷婷(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3)
论越剧在南京的传播与发展①
张婷婷(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3)
越剧传入南京,肇始于1935年,40年代形成规模,获得南京观众的关注,最终开拓了南京的演剧市场,成为南京重要的剧种之一。50年代竺水招率领云华越剧团从上海到南京演出,并留驻南京成立南京市越剧团,为南京越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文革时期,越剧遭到毁灭性打击,其发展也全面停滞。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越剧沉睡的种子,但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越剧的观众市场逐渐萎缩,国营化的剧团改革势在必行。经过90年代以来的剧团改制,南京的越剧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越剧传播;竺水招;南京市越剧团;剧团改制
与滥觞于吴中地区的昆曲相较,作为浙江代表性戏曲剧种的越剧非常年轻,它发源于浙江省绍兴地区的嵊州一带,在“落地唱书”曲艺形式的基础上,借鉴余姚滩簧、绍剧等曲种的唱腔、曲调、表现方法逐步形成一种成熟的表演艺术。越剧于1906年初登表演舞台之后,发展得非常迅速。早在“小歌班”时期,便在与杭州、嘉兴、湖州毗邻的江苏地区演出,“应该说这是越剧早期跨出浙江省域的演出尝试”[1],但这时越剧的表演形式还非常粗陋,只有汲取其他优秀剧种表演形式,从剧本、布景、道具、灯光以及音乐等方面尽力改革,去芜存菁,才能“使她具有话剧的色彩,而带有京剧的情调,因此便提起了观众的兴趣和拥护”[2]。伴随着不断地创新,越剧很快也从农村传播到郊县,再从郊县流传到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最终登上“大上海”的舞台,被都市的观众普遍接受。20世纪40年代,越剧由上海沿沪宁一线,大量流传到南京,获得了南京观众的关注,最终开拓了南京的演剧市场,成为南京重要的剧种之一。
一、南京越剧的兴起期
越剧传入南京,最早在1935年,史料记载:“1934年4月,越剧首次进入江苏省苏州市,翌年进入南京市演出”[3]84,但由于越剧的受众面小,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直到1946年的3月份左右,相继有多家剧场邀请越剧搭班表演,才吸引南京民众的目光。署名为“倚虹阁主”的作者在1946年《南京越剧热》一文提到:“越剧在南京,在一个月以前才发现,最初是朱雀路的新亚俱乐社演越剧,很能叫座,随着中央茶室也约了一班越剧,营业相当不恶,但是新亚的观众便慢慢的抵减了下去,如今飞龙阁也在越剧的头上动了脑筋,南京同时已有三个越剧场了。”[4]当时,越剧在上海、苏州等地已经颇有影响,但在南京的发展规模始终不大,不被观众广泛接纳,其中既有方言差异的原因,也与南京当时的演剧环境有关,南京人对这种初来乍到的新剧种,并不十分看好,不仅认为“越剧是很单调的”,而且认为在南京的演剧市场上,如果有两家剧场上演越剧,市场需求就已经饱和,若三家剧场同时上演,则票房的前景甚为堪忧,“如果南京有一家越剧场,营业方面虽不能十分鼎盛,也不会吃上赔账,两处越剧已觉多余,再要开为三家,怎能使观众装满呢。”[4]为了赢得南京的观众,各家剧场煞费心思,各具风格地打造越剧演出的剧场环境与表演质量,出人意料的是,最终在南京掀起一阵“越剧热”。
民国时期的新亚俱乐社位于南京朱雀路刘公祠的一条巷子里(今天的太平南路附近),剧场不大,只能容纳三百多观众,但是布局却很别致,与普通戏院一排排座椅的安放位置不同,场内设有小圆桌七十余个,每桌配备四个座椅,使观众进出方便,类似于夫子庙的戏茶厅,因此“观众对之,存着很好的印象”[5]5。新亚俱乐社由“芳英四美越剧团”挂牌演出,有四个女子挑梁台柱:头牌老生王桂芳、头牌小生张雅芳,标准小生何美芳,闺阁花衫王玉英。四个女子虽然是绍兴人,却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其中王桂芳与张雅芳是老搭档,一同来自苏州的护龙街怡园,张桂芳“唱功殊佳,发音亦正,脸上有戏,做派传神,与老生宋绍臣的艺术相伯仲,每剧的主角,多由桂芳扮演,前台捧者大有人在,雅芳是标准小生,有时能反串花衫,因有武术的根底,台上工架弱,在小生中可称为全才。”[6]5由于四人的名字或有“芳”,或有“英”,因而剧团取名“芳英四美”,后来又有上海的老生宋少臣加入演唱队伍,构成了强大的演出阵容。“芳英四美越剧团”全团共有三十余人,除了三、四名管理人员外,几乎都是绍兴女子,分别“由上海‘浙东’、‘天潼’,苏州的‘怡园’约来的”[5]5,她们生活极为简朴,吃住均在新亚俱乐社后台,除了有时去南京电台播送越剧外,没有丝毫交际。每日演出日夜两场,观众主要是在南京的绍兴商人,新编的现代越剧“说不出的苦”也颇受南京人的喜欢。“芳英四美越剧团”在南京“虽是唱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是社会上已经轰动。”[6]5
飞龙阁则约来杭州的新生越剧社挂牌演出,取得极好的效果。飞龙阁在当时的生存已经岌岌可危,为了吸引观众,赶时髦地上演了新兴话剧,票房仍然不见起色。在这种情况下,遂引进杭州的越剧团体,希望以此打开市场局面。飞龙阁引进的越剧班社有三十多个女演员,由“一颗红星”“越剧皇后”之称的白牡丹担任领导,与她同挂头牌的演员是“越剧新帝”裘绿琴,二人“一帝一后,恰是一花衫一小生”,上演的剧目多为越剧唱腔擅长表现的生旦爱情戏,“总离不开夫妻的关系,……因此也撑起了飞龙阁的场面。”[7]10尽管白牡丹与裘绿琴的擅于抒情戏,演唱较为清幽婉转,但为了增加戏曲的表现力,丰富戏剧的表现形式,在裘绿琴的邀约下,她的姐姐裘大倌也被拉入戏班,搭入飞龙阁。裘大倌擅长花脸,这在越剧中是难得的角色,配在生旦戏的表演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无不受到南京观众的喜爱,“架子大面裘大倌,她的芳龄二十有九,是绍兴嵊县人,气魄雄伟,巾帼丈夫,扮演伟岸,绝不似一个女子,而且在台上发音洪亮,做派大方,是她难能可贵的地方。”[7]10飞龙阁的越剧演出,迅速引起了南京社会人士的追捧,也帮助飞龙阁度过了生存的危机,“她们在飞龙阁打泡中间,上座成绩甚佳,每天可以有三百万的收入,照着这样的成绩下去,她们决定在飞龙阁连续演唱两个月”[7]10,从“三百万的收入”可以窥见,南京观众对越剧的追捧程度。越剧演员,为了博得南京观众的喜爱,也主动开拓市场,寻找表演的各种路线、改进戏剧的表现手段、从而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自此,越剧在南京已经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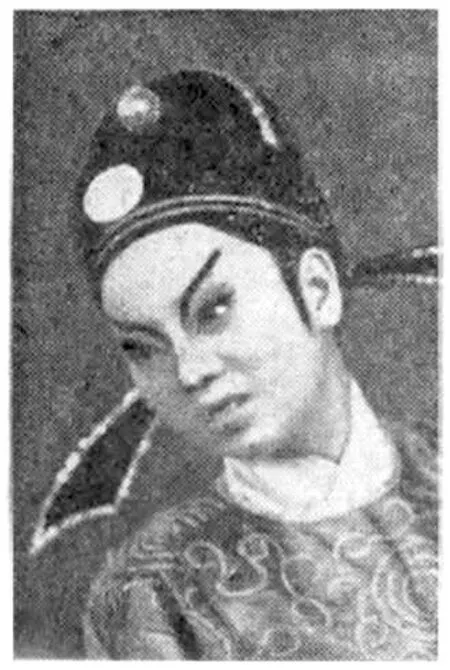
图1.《新上海》1947年第65期刊登的裘绿琴戏装

图2.《新上海》1947年第65期刊登的裘大倌戏装
南京自1946年兴起越剧热之后,越剧便留在了南京的戏剧土壤中,成为众多剧种的一员,更拥有了一群忠实的戏迷为其沉醉痴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47年筱丹凤前往南京被盛情接待的事件,解读出当时南京越剧迷的捧角状况:“天才越伶筱丹凤,前在南京中央剧场演唱当家旦时,曾红过南京半片天,本月二十一日,她因事往南京去。一般国府委员金陵越迷,颇尽地主之谊,设宴备点,大事招待,弄得她应接不暇,外加武装同志保镖,风头着实出足。”[8]南京的越剧演出日益繁荣,尤其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除了上海等地的越剧团常来南京演出之外,本市也成立多个民营越剧团,如新生、群乐、和合、联友、大众等,均是这一时期成立的越剧团。位于鲜鱼巷的大鸿楼也“成了常演越剧的剧场”[9]105。1954年春天,随着竺水招率领云华越剧团来宁演出,遂被挽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实验越剧团,南京的越剧发展又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南京越剧的蓬勃发展期
1947年9月,“云华越剧团”在上海国泰大戏院成立,这个剧团由芳华剧团改组而成,以竺水招为首要演员,这便是南京越剧团的前身。1954年的秋天,竺水招率领云华越剧团从上海到南京演出,在明星大戏院连续演出了《柳毅传书》《文天祥》《南冠草》《范蠡与西施》等剧目,引起了强烈轰动,也得到了南京市委领导的重视,尤其是当南京市委领导彭冲、徐步等人观看了《范蠡与西施》这部爱国历史剧后,对云华越剧团极为重视,建议南京市文化局对该团给予关怀,“南京市文化局特地派人和竺水招洽谈,准备吸收‘云华越剧团’为民营公助性质的南京实验越剧团”[10]。1956年2月26日,实验越剧团又正式改为国营体制的南京越剧团,竺水招任首任团长。
南京越剧团团长竺水招,擅长生、旦两行,她所扮演的小生,有各种类型,如神话剧《柳毅传书》中柳毅、历史剧《南冠草》中夏完淳、民间传说《莫愁女》中徐澄、传统剧《梁祝》中梁山伯、现代剧《家》中觉新、《卖婆记》中李阿大等。她能根据人物的性格,将每一位人物特征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拿捏有度。分寸之间的差异性表现,能使不同的人物活泼泼地立体在舞台上,台风大气稳重,张弛有度。她扮演的旦角,如传统剧《碧玉答》中李秀英、历史剧《蔡文姬》中蔡文姬、现代剧《江姐》中江雪琴、《铁骨红心》中向永贞等,真实细腻,落落大方,毫不做作,不落俗套,加之“纯朴大方、缠绵悱恻、刚柔相济、极富韵味”[11]的唱腔特点,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南京越剧团被批准为国营剧团时,正值竺水招带领筱水招、商芳臣、筱月凤等演员排练《柳毅传书》《南冠草》《文天祥》三个剧目前往北京作第一次巡回演出。三个表演剧目中,《南冠草》是根据郭沫若1943年创作的历史剧改编的,因此郭沫若饶有兴趣地两次前往观看,并评价竺水招扮演的主人翁“就是我心目中的夏完淳形象”[12]970。1956年3月4日,《南冠草》再次在由中国科学院包场的政协礼堂演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被郭沫若邀请前来观剧,这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得到高度评价:“南京市越剧团,在艺术改革上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保持了一定的艺术水平。越剧团根据郭沫若同志的同名话剧改编的‘南冠草’以及‘文天祥’,不仅丰富了上演剧目,而且也扩大了题材范围,剧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鼓舞着观众。”[13]而正是这次历时半年多的北上演出,“奠定了以竺水招为团长的南京越剧团的在艺术上的飞跃,也使南京人民真正拥有自己的越剧团。”[14]《柳毅传书》《南冠草》《文天祥》也成为南京越剧团的优秀保留节目。
1956年—1965年,是南京越剧团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是南京越剧团飞速发展的十年,该团多次赴其他省份进行巡回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也扩大了南京越剧的影响力,例如1957年后,剧团排练了《南冠草》《天雨花》以及《孔雀胆》《柳毅传书》等剧目,再次在全国进行巡演,“两次北上赴京津、东北等地巡回演出,并受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会的热情邀请到汽车城作慰问演出”[15],又于1958年9月“赴福建海防前线慰问海防战士,历时七十三天,演出一百六十九场,观众逾十四万人次”[12]688,为战士们演出了“《柳毅传书》《金凤树开花》《关不住的姑娘》等剧”[16],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颇具一定的影响力。
南京越剧团在剧目的创新编排上,也花费了大量心血,例如1962年由商芳臣主演的《孙安动本》,演遍江苏南北;1963年编创的《莫愁女》,首演于南京大华电影院,“一千八百多个座位,每天日夜两场,场场座无虚席,连满两个多月,创造了南京戏曲舞台卖座的新纪录”。[12]6881964年至1966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推动下,剧团排演了《芦荡火种》《江姐》《血泪荡》《姜喜喜》《铁骨红心》等一批现代戏”[12]688。剧团又将《柳毅传书》等多个剧目搬上电影屏幕,摄成彩色戏曲艺术片并向国内外发行。为了解决越剧现代戏,男角扮演的问题,南京越剧团于1965年9月,招收男演员,实验男女合演,实为“全省首创”[9]105。
专业剧团在南京得到良性发展的同时,也培育了一批越剧爱好者,观众群体也越来越壮大,由民众主动参与的业余性越剧活动也纷纷开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除了南京越剧团之外,玄武、下关区,南京电瓷厂、无线电厂,以及江浦县都有业余越剧演出。”[9]105
三、南京越剧的衰落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的越剧进入全面衰落期。由于越剧女扮男装擅长表现“公子”“书生”,与“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差距过大,并且违背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立场,再加上“才子佳人”的剧种风格,“散布了多少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17],越剧的“命”被“革”了,不仅受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批判,还被贴上“靡靡之音”“60年代怪现象”等标签,被停止在全国范围内流播,大量原有的剧团或解散或改组,“浙江全省73个女子越剧团一下子全部被撤销,上海区级越剧团也全部被撤销,全国其他省市县越剧团体同样难以幸免,惨遭灭顶之灾。”[3]334南京越剧的发展也不能幸免地走向衰落,甚至“一度濒临解散,一部分演职人员被迫转业或下放农村”[12]689,各类越剧活动被纷纷叫停,“六合县越剧团和江苏青年越剧团被先后撤销,各业余剧团也纷纷停止活动”[9]105-106,越剧机构被砸烂,演出队伍也被驱散,群众活动被迫取消,而老一辈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也被关进“牛棚”,受到审查甚至刑罚,遭到轮番“揪斗”或“示众”,竺水招就是这样的受害者,她被残酷地迫害,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于1968年5月26日去世,这给南京越剧界沉重一击。此时,越剧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文革结束,中国的历史进程迈入改革开放的阶段。“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人民性”文艺观念逐渐弱化,戏剧舞台表演呈现出现多元化的景象,平等意识、人权思想、自由观念、人道精神、个人权利等过去被视为禁区的思想观念成为新时期文化语境的重要元素。南京的越剧,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复苏。戏曲是依附于演员展现的舞台的艺术,经历十年政治运动,耽误了演员的舞台生命,也阻碍了人才储备,人员年龄、艺术水准、机构体制等问题,都为越剧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为了解决演员青黄不接的现实问题,南京越剧团在苏锡常一带,招收男女学员进行培养,大胆地“创作排演了在戏曲舞台上第一个塑造周恩来总理艺术形象的现代戏《报童之歌》”[15],赴京参加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获得创作、演出二等奖。在此时的演出活动中,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演员,如郑嘉琴、夏文君、竺小招、袁小云、赵时莺,韩林根、章文全等,都成为剧团的艺术骨干。1983年,南京越剧团又创作演出了《秦淮梦》,以此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并在同年的江苏省青年演员新剧目调演中获得演出奖、创作奖和优秀演员奖。除了专业剧团迅速恢复演出,取得了较大成绩外,群众的业余性活动也纷纷开展,“不仅玄武、下关恢复了业余活动,白下、鼓楼也都有了业余活动,鼓楼区先后成立过四个业余越剧团。1983年,下关区成立了全市第一个,由自己创建、自负盈亏的‘星星越剧团’。”[9]106这些活动,像一股清新的文艺春风,吹入群众的生活,解开了被禁锢已久的思想,也唤醒了沉睡在人们心中的文艺种子,受到了南京市民甚至外地人民的欢迎。
这一时期的越剧复苏,某种程度依赖于摆脱“文革”、思想解禁的兴奋,老观众又能看到阔别舞台已久的越剧剧目,新观众带有一丝新鲜的眼光去欣赏表演,呈现出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期。但改革的春风给戏曲带来思想解放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根本性地改变着艺术生存的环境。市场经济的冲击,流行文化的兴起,电影电视的普及,使大众随时随地就能得到娱乐,不需要买票进入剧场。多元化的娱乐形式,带走了大量的戏曲观众,越剧演出的票房收入急剧下滑,因此,“越剧真正的全面衰落主要在1985—1988年”[1]。全国的越剧界如此,南京越剧也不能幸免,在短暂地复苏之后,却又逐渐走向低谷,观众流失,演出减少,人才转行,越剧事业全面萎缩。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原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托于国家财力支持的国营剧团的弊端日益凸显,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成为多数院团亟待解决的问题,“领导体制和经营管理不适应艺术生产的需要。领导部门管得太多,统得过死,艺术表演团体缺乏必要的自主权,艺术人员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又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存在着软弱涣散的问题。”[18]戏剧演出日益脱离民间演出的原始土壤,可以说剧团的生存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号称‘走向全国’的第二大剧种,她的覆盖面已大大缩小:江浙沪以外地区原有的专业越剧团体只存福建芳华一枝独秀,其它早已不复存在;就连江浙沪这三个越剧立身之地,江苏也硕果仅存南京市越剧团‘单’桂飘香了。”[15]在整个戏曲市场萎缩的背景下,南京的越剧不得不思考“改革”的问题,无论是剧目编创,还是从舞台表演,甚至是多媒体时代下艺术形式的创新,均需要提上改革的日程,在旷日持久的摸索中不断前进。
四、南京越剧的改革期
越剧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吸纳借鉴,自我革新的过程,要面对市场,获得大众的认同,需求生存的良性空间,就必须不断改革,从外在的形式,到内在的内容,吐故纳新,才能赢得市场,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目光。因此进入到90年代,直至今日,南京越剧界的一个关键词便是“改革”。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冲击,政府必须变直接干预为间接引导,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让剧团自行负责剧目的创作与演出。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南京市越剧团与江苏沙钢集团暂签了两年协议,以图以与社会力量多种形式联盟的形式,寻求剧团体制改革的出路,推动剧团的发展。沙钢将连续2年,每年给越剧团50万的投入,而越剧团也相应地要沙钢的经济协作单位每年演出5—10场,此外,沙钢在越剧团的引进人才、剧目创作上再投入资金。这也意味着剧团上演的剧目,不再听命于行政性的命令,逐渐回归到市场,根据合作方或观众的要求编排剧目,社会效益被绝对地放在了剧团发展的第一位。经过6年时间的摸索,2010年,南京市越剧团正式转企改制,更名为南京市越剧团有限公司,直接面向市场,寻求发展的活泼生机。
走向市场后,南京的越剧发展开始逐步升温,无论是保留的传统剧目,还是新编越剧,在市场化的运作过程中,既拥有了资金,也赢得了观众。例如南京越剧团复排《柳毅传书》,在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创新性元素,该剧于2012年入选文化部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但戏剧并不是为“评奖”而生的,而是为观众存在的,《柳毅传书》并未因获得了政府奖项而止步,而是被越剧团带到了更广阔的市场,“至 2013年7月,《柳毅传书》剧组下工地、到社区,深入敬老院、慰问子弟兵,与农民兄弟零距离接触……诚如戏中所唱,做惠民之青鸟,把精品的魅力传播到四面八方”[19],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观众戏迷的追捧,“仅在洞泾镇一地,《柳毅传书》就创造了连续3场、场场爆满的观演盛况。南京的部分戏迷利用周末时间,长途往返洞泾,只为再次领略两组演员不同组合的演绎特色,并通过网络呼吁精品剧目增加在本地演出的场次,更多满足观众感知经典、了解越剧的需求。”[19]回归到市场后,传统剧目也焕发出时代的生机,重新获得戏迷,受到观众的喜爱。又如,2011年,编排的现代越剧《丁香》的演出,在市场化的运作下,联合江苏演艺集团的舞美设计,江苏交响乐团的伴奏,甚至从其他剧团外借演员,利用可资利用的资源,以跨剧种、跨院团、跨地域的合作方式,开拓市场,增加收益,也赢得了一批新的观众。
除了专业剧团通过体制改革回归到市场,在市场的指导下良性发展之外,群众性的越剧活动也逐渐升温。例如于1989年成立的秦淮青年越剧团,完全是由一个戏迷票友组建的业余性剧团,先后创作演出了《花潭洗砚》《送花楼会》《乡红旗》《争当文明好市民》《秦淮风光好》等一批传统剧目和演唱曲目,还积极参与全国性的票友大赛,拿到过优异的成绩,如1996年中央电视台、中国剧协举办的全国越剧业余卡拉OK比赛中,获2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2001年,央视戏曲频道“过把瘾”栏目江苏地方戏专集中,夺得优胜杯。群众性的越剧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形式多样,妙趣横生。
越剧艺术的发展尽管常常以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为基本前提,但传统的艺术经验与智慧永远都是创造性与突破性力量得以生长的肥衍土壤,任何创新性改革的前提,必须是扎根于自身的流派唱腔,才能既能绵延文化命脉,又能保持越剧创造性生机。因此,南京越剧的保留剧目《柳毅传书》《莫愁女》《汉宫怨》《双玉婵》《玉堂春》《珍珠塔》《唐伯虎点秋香》《孟丽君》等,很好地保留了传统越剧经典的精神、技法、方式和神韵。但是剧目的创作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题材,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意识,使其焕发出当下的时代生机,吸引到年轻的观众,甚至是80后、90后观众,都是越剧必须思考的问题。南京越剧的发展,也在不断保留老剧目,编排新剧目的过程中获得的。为了吸引新观众,剧团也打造了许多新编的剧目,不仅在题材上契合当代人的精神,在舞台美术、音乐声腔上,也有大胆的尝试。例如越剧《丁香》,“不同于传统越剧的‘景在演员身上’,越剧《丁香》舞台设计大胆:以灰砖墙为主体,台左侧一株丁香树引人注目,预示着灰色年代的丁香树浓香袭人和依然故我的品质”[20],在声腔上方面,“尽可能地保留与呈现越剧本体音乐的流派特色,另一方面,在用音乐塑造人物、渲染气氛时,也融合了江南风格的民族音乐以及西方古典音乐大线条的旋律”[21]。越剧作为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让国人自豪,但是它毕竟生活的当下,必须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环境,面对新的观众群体,如果“一种艺术一旦成了‘古典’,其艺术结构也就被封闭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系统之内,名声上是‘高雅’了,但其代价却是失去了活生生的生存方式,也就失去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以活生生的面貌在舞台上与广大观众见面的机会。”[22]因此,越剧想要成为当下大众视野中的“活”的艺术,就必须寻找新的生存方式。而南京的越剧界也看到这一点,不断践行“传承”“改革”“创新”的使命,甚至将新兴的科技技术融入舞台表现,例如新版《柳毅传书》就运用3D效果展现龙王、水晶宫、下海入地等场景。
当然,任何改革与创新必须以遵循传统艺术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不能以伤害传统艺术为代价。成为经典的艺术,并非因其绚丽的外在形式,而在其内在精神,绝不可以为了留住观众,就用奇巧的声色、迷幻的形式娱乐“大众化”,戏剧首先要考虑的对得起历史。要用艺术思考力,表现人类精神价值的广度与深度,在“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核”两方面,寻找戏剧发展的张力,从而“化大众”,唯有如此,才能促进越剧艺术的当下传承。
[1]沈勇.越剧在全国流播的现象及本质[J].文化艺术研究,2013(2).
[2]魏凤娟.闲话越剧[J].沪光,1946(4):7.
[3]应志良.中国越剧发展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4]倚虹阁主.南京越剧热[J].大地周报,1946(51).
[5]老夏.越剧在南京[J].新上海,1947(58):5.
[6]倚虹阁主.越剧二红星降落在南京(附照片)[J].新上海,1947(59):5.
[7]倚虹阁主. 飞龙阁越剧姊妹花[J].秋海棠,1946(3).
[8]秋人.越劇圈[J].宁绍新报,1947(17—18):17.
[9]江苏戏曲志编辑委员会,江苏戏曲志·南京卷编辑委员会,编.江苏戏曲志,南京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10]汤雅洪.越剧名家竺水招母女的悲欢人生[J].档案与建设,2008(8).
[11]孙静.她的品德教育了我她的艺术感染了我——纪念太先生竺水招诞辰九十周年[J].剧影月报,2011(2).
[12]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苏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戏曲志,江苏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2.
[13]海.南京市越剧团在北京演出[J].戏剧报,1956(6):42.
[14]陶基富.南京市越剧团的一次北上演出[J].剧影月报,2007(1).
[15]潘迎宪.南京越剧的回顾与思考[J].剧影月报,2009(3).
[16]戏剧报编辑部.南京市越剧团在海防前线[J].戏剧报,1958(20):9.
[17]尹桂芳.不演“公子”、“书生”,要演革命英雄[J].戏剧报,1966(3):26.
[18]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编.1981—1985《文艺通报选编》[G].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130.
[19]王立元,刘焱.《柳毅传书》:做惠民之青鸟[N].中国文化报,2013年7月30日:第1版.
[20]冯晓岚.从越剧《丁香》几大亮点看越剧的市场[J].剧影月报,2012(4).
[21]一丁.红色恋曲 英雄颂歌——就现代越剧《丁香》采访南京市越剧团团长潘迎宪[J].剧影月报,2011(3).
[22]董健.《戏曲本质论》序.//吕效平.戏曲本质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
J809;J825;J819
A
1008-9667(2017)03-0123-06
2017-02-22
张婷婷(1979— ),女,贵州贵阳人,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艺术学。
① 本文为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构与文化创新研究”(2015ZSTD008)阶段性成果、《江苏省高校社科团队: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构与文化创新研究(DGXYJYS15)》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王晓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