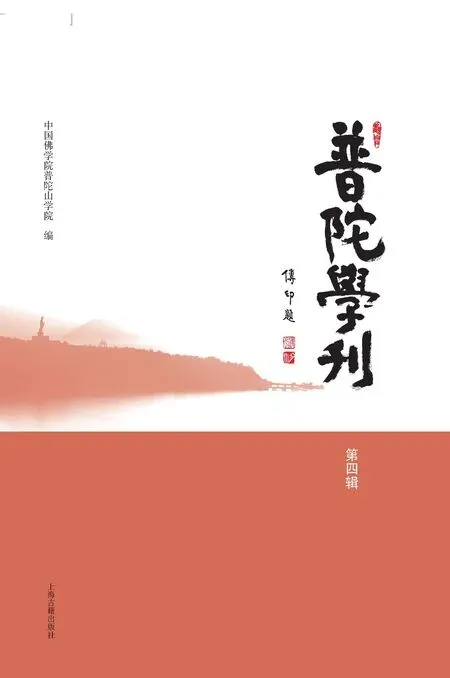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发现犍陀罗语佛教写本综述
庞亚辉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熟悉佛教史的人对犍陀罗在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多半不会陌生。佛法最初来华据信即从西域传入,汉代中国佛教的渊源首称大月氏、安息、康居三国,而犍陀罗正处于古书中所说的“大月氏”版图之内。一般认为,佛教早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时期即已传入犍陀罗,以后犍陀罗又成为佛教向外传播的重要阵地,但13世纪以后佛教即已在印度本土上消亡,对犍陀罗佛教的文字记载十分有限,尽管汉传一系尚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大唐西域记》等传世文献述及犍陀罗,但唐代去古已远,近人对玄奘所说亦颇有疑虑。事实上,我们对犍陀罗佛教从整体到细节均不甚了了——犍陀罗地区所流传的佛教属何种派别?其教义教理究竟如何?与原始佛教传统以及其他佛教传统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犍陀罗如何成为了印度佛教重镇,又具体通过怎样的方式推动了佛教的传播?我们期待对新发现佛教经卷的研读能对这些疑问有所应答。*本文收稿时间在2014年初。大约同一时间出版的《宗教研究2013》(方立天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12月)一书中恰好同步刊出了一组犍陀罗佛教研究文章。其中,新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南亚佛教研究系主任马克·阿隆所作《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佛教写本的近期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亦系统说明了犍陀罗语佛教写本残卷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所作《美国华盛顿大学早期佛教写本项目及其前沿性研究》更对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现状作了全面介绍。但本文与其侧重颇有不同,可资相互参考与补充。
一、 犍陀罗语佛教写本的发现
自19世纪初以来,中亚、南亚各地就陆续发现了用犍陀罗语或梵语、以佉卢文和婆罗谜文字书写的佛教文本残片,还有大量刻写在雕像、陶器、壁画上的供养铭文,铭文中往往标有具体年代,有时甚至会提及当时国王、大臣的名讳。到19世纪80年代,在新疆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至罗布泊沿岸的古代遗址,甘肃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及喀什和洛阳古董市场上,不断发现大批写有佉卢文的木牍、残纸、帛书、皮革文书、题记,还找到了以佉卢文刻写的碑铭和汉-佉二体钱币。*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13页。1890年,英国军人H.Bower在新疆库车获得了一部书写在桦树皮上的古印度医家遮罗迦所著的《医道论集》,*即“鲍威尔手稿”,属笈多王朝时期,其书写文字当是天城体之前的那加里(Nagari)字体,见A.F.Rudolf Hoernle, The Bow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 Nagari Transcript, Romanis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Calcutta (India): Supt., 1893.这些发现方始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1892年,两位法国学者J.-L.Dutreuil de Rhins和F.Grenard在新疆和田地区首次发现用犍陀罗语以佉卢文字书写的佛教文本《法句经》残卷,正式翻开了重建犍陀罗佛教历史及其政治文化背景的新篇章。到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陆续又有几批新的犍陀罗佛教写本现世,引发了学界内外的极大兴趣。至此,已发现的重要犍陀罗语/佉卢文佛教写本包括:
于阗犍陀罗语《法句经》
内容:一件犍陀罗语版本《法句经》残卷
手稿材质:桦树皮
现存地点:分别存放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发现地点和时间:新疆和田,1892
断代: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初
已出版研究成果:*本文所列“已出版研究成果”仅指全面介绍性的或以出土文献为中心的研究论文或专著。
John Brough《犍陀罗语〈法句经〉》,*Gndh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1962
林梅村《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二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53—262页。1989
新疆尼雅佉卢文古卷
内容:大量佉卢文文献中间包含几部佛经,主要有《法集要颂经》、《波罗提木叉(解脱戒本)》、《温室洗浴众僧经》的残本*据林梅村先生的研究,Kh.511和Kh.647号文书均为《温室洗浴众僧经》残本,但Kh.511为佉卢文书写的梵语文本,其他几种当为犍陀罗语。《法集要颂经》残本的基本结构为犍陀罗语,但连声规则等明显受到了梵语的影响。见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第151页。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温室洗浴众僧经》为“伪经”,因为根据对其回鹘语译本的研究,可以肯定是从汉语转译为回鹘语的,见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的《谈回鹘语文献夹写汉字现象》,为2011年9月29日在复旦大学一次公开报告的内容。但既然有佉卢文版本的存在,要确定这部经是否伪经恐还需要对佉卢文版本的考证。在新发现佉卢文经卷中出现了与洗浴养生在大的分类上有所近似的医学文献,对此一问题似亦有所补充。
手稿材质:简牍
现存地点:大英图书馆
发现地点和时间:新疆尼雅,1905—1906
断代:公元4世纪前后
已出版研究成果:
Franz Bernhard《法集要颂经》,*Udnavarga, Vol. 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5.1965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版权前揭。1988
林梅村《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1995
林梅村《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法集要颂经〉残片》,*《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版权前揭,第151—156页。1998
林梅村《尼雅出土佉卢文〈温室洗浴众僧经〉残卷考》,*《华林》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7—126页。2003
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007
大英图书馆佉卢文经卷
内容:29件犍陀罗语佛教文本残卷,残片大小不一,保存情况亦有较大差异;文本涵盖多种类型和体裁,书写笔迹多样;基本可确定属法藏部或与法藏部密切相关
手稿材质:桦树皮
现存地点:大英图书馆
发现地点和时间:阿富汗东部(推测),1993
断代:公元1世纪(推测)
已出版研究成果:
Richard Salomon《来自犍陀罗的古代佛教经卷——大英图书馆的佉卢文残片》,*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ndhr: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1999
Richard Salomon《一部犍陀罗语版本的〈犀牛经〉:大英图书馆佉卢文残片5B》,*A Gndhrī Version of the Rhinoceros Sūtra: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 5B,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2000
Mark Allon《三篇增一阿含类经文:大英图书馆佉卢文片段12和14》*Three Gndhrī Ekottarikagama-Type Sūtras: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12 and 14,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2001
Timothy Lenz《一个犍陀罗语〈法句经〉的新版本及一部本生故事集:大英图书馆佉卢文残片16+25》*A New Version of the Gndhrī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16+25,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3.,2003
王邦维《论阿富汗新发现的佉卢文佛教经卷》,*《中华佛学学报》第13期,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2000年,第13—20页。2000
陈明《犍陀罗语译本〈犀牛经〉评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51—456页。2004
萨尔吉《马克·艾伦:〈三篇犍陀罗本的增一阿含型经:英国图书馆所藏佉卢文残片12和14〉》,*《中国学术》总第15辑,2003年第3期,第315—320页。2003
陈明《〈犍陀罗语《法句经》新译本及本生故事集〉评介》,*似仅发表于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官方网站上:http://www.eastlit.pku.edu.cn/show.php?id=6206。2005
惟善《美国华盛顿大学早期佛教写本及其前沿性研究》,*方立天主编:《宗教研究2013》,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本文中对华盛顿大学针对大英图书馆与斯尼尔收藏的研究现状及进展亦有详尽介绍。2013
斯尼尔(Senior)佉卢文经卷
内容:24件犍陀罗语佉卢文佛教经卷或残卷,其中一部分保存近乎完好;几乎全部出自同一手笔;内容多属经藏,另有一篇《阿耨达池偈》
手稿材质:桦树皮
现存地点:英国私人收藏
发现地点和时间:阿富汗东部(推测),20世纪90年代初
断代:公元1—2世纪迦腻色迦王时期
已出版研究成果:
Andrew Glass《四篇犍陀罗语杂阿含经:斯尼尔佉卢文片段5》,*Four Gndhrī Samyuktagama Sutras: Senior Kharosthī Fragment 5,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2007
Richard Salomon《两篇犍陀罗语〈阿耨达池偈〉写本:大英图书馆佉卢文片段1和斯尼尔经卷14》,*Two Gndhrī Manuscripts of the Songs of Lake Anavtapta (Anavatapta-gatha):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 1 and Senior Scroll 14,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此书为大英图书馆经卷和斯尼尔经卷之《阿耨达池偈》的对照研究。2009
李颖《〈四部犍陀罗语杂阿含经〉初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Further inquiries into the Four Gndhrī Samyuktagama Sutra (in the Senior Collection): Discussion Based on Four Gandhari Samyuktagama Sutras: Senior Kharosthi Fragment 5 by Andrew Glass, in China Tibetology, No 1, March 2012.2011/2012
斯奎因(Schøyen)佉卢文残片
内容:129件残片,多数较小;代表几十篇写本,内容各异
手稿材质:贝叶(棕榈叶)
现存地点:挪威M.Schøyen的私人收藏
发现地点和时间:阿富汗巴米扬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
断代:部分可早至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推测)
已出版研究成果:
Jens Braarvig《斯奎因藏品中的佛教写本》卷一、卷二、卷三,*Buddhist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0;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I,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2;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II,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6.2000、2002、2006
平山(Hirayama)佉卢文残片
内容:27件佉卢文残片,部分残片与斯奎因、林寺残片同属一组
手稿材质:贝叶
现存地点:日本丝绸之路研究所
已出版研究:未知
林寺(Hayashidera)佉卢文残片
内容:18件佉卢文残片,部分残片与斯奎因、平山残片同属一组
手稿材质:贝叶
现存地点:日本私人收藏
已出版研究:未知
华盛顿大学经卷
内容:10件佉卢文残片;其中8件出自同一经卷,另外2件出自另一经卷
手稿材质:桦树皮
现存地点: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发现地点和时间:未知
断代:1世纪或2世纪(推测)
已出版研究:准备中
巴焦尔(Bajaur)佉卢文经卷
内容:18件佉卢文经卷,约出自19位抄写者之手;内容广泛
手稿材质:桦树皮
现存地点: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考古学系
发现地点和时间:巴基斯坦巴焦尔地区,1999*巴焦尔残片最初发现于1999年,之后被送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考古学系。在那里,将这些桦树皮经卷展开几乎花费了几年的时间,直到2006年才首次有介绍性的文章发表。
断代:1世纪或2世纪(推测)
已出版研究成果:
M. Nasim Khan & M. Sohail Khan《犍陀罗佛教佉卢文写本:一个新的发现》,*Buddhist Kharosthī Manuscripts from Gndhr: A New Discovery, i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1-2. Peshawar: 9-15, 2004 (2006).2004 (2006)
Ingo Strauch《巴焦尔佉卢文写本》,*The Bajaur Collection of Kharosthī Manuscripts -A Preliminary Survey, in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25 (2008), pp.103-36.2008
巴基斯坦私人收藏佉卢文经卷
内容:总数未知,研究者获得授权研究其中5件经卷;各经卷书写风格迥异,当出自跨度较大的不同时期
手稿材质:桦树皮
现存地点:巴基斯坦私人收藏,2004年
发现地点和时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据称),2004
断代:公元前后至公元2世纪(C14测定,但结果可疑)
已出版研究成果:
Harry Falk《佉卢文写本的“碎裂”藏品》,*The ‘Split’ Collection of Kharosthī Texts,《创价大学国际佛学高等研究所年报》14: pp.13-23, 2011.2011
Harry Falk & Seishi Karashima《一世纪的犍陀罗〈般若经〉写本(出自碎裂藏品1)》,*A First-century Prajpramit Manuscript from Gandhra -Parivarta 1 (Texts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1), 《创价大学国际佛学高等研究所年报》15: 19-61, 2012.2012
目前比较重要的犍陀罗语佛教文献大致就是这些。佉卢文(又名佉卢虱咤文、驴唇体)主要用来书写犍陀罗语、是一种与犍陀罗语相适应的文字,但从新疆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它也曾被用来书写梵语和吐火罗语。这里所说均为以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佛教写本,像上世纪初发现的现存于法国图书馆的伯希和藏品(Pelliot Collection)为佉卢文书写的梵语文本,遂不在论列。*对伯希和藏品的研究,见Sylvain Lévi, Documents de l’Asie centrale(Mission Pelliot), Textes Sanscrits de Touen-Houang, Nidna-Stra, Daçabala-Stra, Dharmapada, Hymne de Mtrceta, in Journal Asiatique, Vol.10(16), 1910, pp.433-456. 对新疆发现的梵语佛教文本的研究,可参见[俄]榜迦德-列文、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著,王新青、杨富学译:《新疆发现的梵文佛典》,《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2期。上述佛教经卷或经卷残片中的第10种“巴基斯坦私人收藏佉卢文经卷”尚未正式命名,*受委托的研究者称其为“碎裂藏品”(the ‘split’ collection,见前注),当然不可能成为正式名称。其他藏品或者以收藏者命名,如欧洲的斯尼尔、斯奎因,日本的平山、林寺,或者以永久存放地命名,如大英图书馆、华盛顿大学,或者以发现地点命名,如中国的于阗、尼雅和巴基斯坦的巴焦尔。在这些经卷之外,世界各地肯定还有其他的零星残片,B. Pauly 在1967年就曾提到于阿富汗巴米扬的红城(Shahr-i Zuhak)发现4件小型佉卢文写本残片,但并未释读,细节亦不可知。*Bernard Pauly, Fragments Sanskrits d’Afghanistan(fouilles de la D.S.F.A), in Jounal Asiatique 255: 273-283, 1967; Quoted in R.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ndhr: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p.66.这10种残卷或残片中,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世的大英图书馆经卷、斯尼尔经卷、斯奎因残片、巴焦尔经卷和巴基斯坦私人收藏经卷这5种所属年代较为集中,数量较多或保存相对完整,经文涵盖内容也更为广泛,因而显得尤为重要。
二、 新发现犍陀罗语佉卢文佛教经卷的主要内容
古印度的佛教文本均刻写或书写在棕榈叶(贝叶)和桦树皮上,材质本不坚固,加之中亚和南亚气候湿热,极少有经卷能长久保存,19世纪末之前在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发现的梵语和犍陀罗语写本很少早于公元6世纪。而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因气候特殊,文本保存条件得天独厚,自19世纪后期开始即陆续发现了一些用婆罗谜文和佉卢文书写的佛教文本,前面所说的于阗佉卢文《法句经》即是其中最早的一部。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英图书馆、巴焦尔等经卷的发现,再次刷新了这一记录。于阗经卷仅为一部2世纪前后的《法句经》,尼雅简牍则包括3世纪末4世纪初的《法集要颂经》《波罗提木叉》等,新发现经卷在规模和内容的覆盖面上显然均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发现。
大英图书馆新发现佉卢文经卷* 这里和以下所说的“经卷”均指犍陀罗语佉卢文残卷、残片,亦有个别保持相当完整,将特别指出。中已基本辨识的内容* 大英图书馆佉卢文经卷的大体内容,在邵瑞祺(Richard Salomon)教授1999年出版的《犍陀罗古代佛教经卷:大英图书馆佉卢文残片》(英文,版权前揭)中已作出了系统的介绍,中文也有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2000年所写的《论阿富汗新发现的佉卢文佛教经卷》一文,本文对王邦维先生的译介内容有所调整,为与其他新出经卷比照,分类方式和名称也有所改变,如邵瑞祺教授对经卷分类中的“经类”据内容改作“阿含类”等,可参见邵瑞祺、王邦维的原作,以下不一一注明。
1. 阿含类:三种增一阿含/增支部经及注疏,*本文“增一阿含”指梵语传统及汉传佛教所传,“增支部”则属南传巴利圣典传统,以下“长阿含”与“长部”、“中阿含”与“中部”、“杂阿含”与“相应部”的区别亦同。一种与《增一阿含》中《众集经》相应并有经注,一种涉及四禅那,另外一种则与巴利语《增支部·四集》中的三段经文对应。*事实上绝大多数经卷的标题均已不存,因而所谓的经名,也只是与其他梵语、巴利语、藏语、汉语等佛教传统中所能找到的文本名称,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 注疏类:主要是一些偈颂的注疏。这些偈颂本身大都可以在巴利圣典《小部》中的《经集》《自说》《法句》《如是说》《长老偈》中找到,但排列次序不同;注疏则与任何已知佛教传统均没有对应关系,一般认为出自犍陀罗本土。
3. 偈颂类:包括《阿耨达池偈》《犀牛角经》《法句经》三种。
4. 其他:包括一些譬喻类文本、一部本生故事集、一篇严重残缺的佛赞等。
斯尼尔经卷已经辨识的内容* 据Mark Allon为《四篇犍陀罗语杂阿含经:斯尼尔佉卢文片段5》(版权前揭)一书所作的《导言:斯尼尔写本》编译整理。
1. 阿含类:四篇杂阿含经,包括杂阿含的《众集经》《非汝所应法》《斧头柄经》和相应部的《善男子》。
2. 偈颂类:一篇《阿耨达池偈》。
巴基斯坦私人收藏经卷中受委托研究的五件经卷* 据Harry Falk《佉卢文写本的“碎裂”藏品》(版权前揭)编译整理。
1. 阿含类:《小部·经集·义品》。
2. 大乘类:《般若经》,与《八千颂般若》第一章和第五章对应。
3. 偈颂类:一篇《法句经》的较大残片,包含89节。
4. 譬喻类:一部譬喻故事集,其中提及一些人名和法藏部、大众部等部派名称。
5. 其他:有关佛陀生平的一篇韵文。
巴焦尔经卷中包含的佛教文本* 据Ingo. Strauch《巴焦尔佉卢文写本》(版权前揭)编译整理。
1. 阿含类:中部/中阿含中的一篇,即巴利圣典《中部·142经·施分别经》,汉译《中阿含·180经·瞿昙弥经》。
2. 律藏类:包括两种,《羯磨本》和《波罗提木叉》。
3. 大乘类:一部与《庄严宝王经》有关的早期大乘经。
4. 注疏类:此类文本多关注教义问题,匿名作者,但使用专业用语。
5. 护卫类:包括两种,其中一种近于完整,属早期佛教后圣典时期的护卫类(辟邪魅用)文献;在梵语中没有对应的内容,与藏文中的同类文献相似并使用同样的术语体系。
6. 其他:主要为佛赞,包括四篇独立的偈颂和一部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偈颂集。
斯奎因残片内容驳杂,年代跨度较大,且有些内容重复出现* 斯奎因残片的内容根据已出版的三卷《斯奎因藏品中的佛教写本》(版权前揭)综合整理。
阿含类:
《中部·商伽经》多篇(属大众部支派说出世部)
《长阿含·大般涅槃经》多篇(贵霜王朝时期)
《增支部·三集·鸯觉经》和《相应部/杂阿含·谛相应·黑暗经》
《长阿含/中阿含·善生经》
律藏类:
《波罗提木叉·经分别》多篇(属大众-说出世部)
《羯磨本》多篇,其中一部注明供受戒用
一件律类残片,涉及对持律者品质的论述
论藏类:与《舍利弗阿毗昙论》有关的三个残片
注疏类:一篇对《长部·20经·大会经》的注
大乘类:
《八千颂般若》
《胜鬘经》
《相应部·自恣经》的一个大乘版本
《诸法无行经》
《阿阇世王经》多篇
《月上女经》
《妙法莲华经》
《月灯三昧经》
《无量寿经》
《金刚般若经》
《弥勒授记经》
《菩萨藏》相关内容
譬喻类:一部《撰集百缘经》残片,一部《光明童子因缘经》残片
偈颂类:包括一篇佛赞,一篇圣勇造《本生鬘》,一篇诃利跋咤造《本生鬘》
其他:
一篇早期注疏残片
一部佛陀传说集残片
一篇《阿育王传》
一部非佛教的弥曼差派文论
一部戏剧残片(尚不确定是否为佛教戏剧)*19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曾发现过用贵霜体婆罗米文字写在贝叶上的梵语佛教戏剧残本,经德国学者Heinrich Lüders研究,指出这批写经中有三部佛教戏曲剧本残卷,其中题记中注明为马鸣所著的《舍利弗剧》保持了9幕中比较完整最后两幕。见Heinrich Lüders, 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Kleinere Sanskrit-Texte I Berlin, 1911;转引自陈明:《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文献季刊》2003年1月第1期。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文献中佛教戏剧也很多,如《弥勒会见记》等剧本,说明在新疆佛教戏剧相当常见。斯奎因经卷中亦有与《弥勒会见记》关系密切的《弥勒授记经》,但是否直接与佛教戏剧有关尚不能确定。
三、 如何看待新发现犍陀罗语佛教写本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陆续发现的佛教写本,所属时期大多集中在公元1、2世纪,从整体上看无疑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一批佛教文献和印度文献。诚然,更“古”并不必然意味着更有价值,但文本价值既取决于文本自身的内容,也取决于研究者对它的理解和解读,显然更古老的文本潜在价值也会更大。那么,作为犍陀罗语、佉卢文、印度、佛教四重“最古”的文献,它们除了基本的古文字学、语言学研究价值和文献的收藏、保存价值之外,在佛教史和佛教义理方面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见识?
1. 关系到对犍陀罗佛教史以及与佛教有关的社会生活史的重建
众所周知,犍陀罗对于佛教向印度本土外的传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犍陀罗地区上世纪以来发现的考古遗存相当丰富,根据这些发现,现代学者至少可以对犍陀罗佛教的历史、艺术、建筑等方面大致加以重现,但令人遗憾的是,正如邵瑞祺教授在《来自犍陀罗的古代佛教经卷——大英图书馆的佉卢文残片》中所说,我们对犍陀罗佛教的认识一向十分模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扭曲。*R.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ndhr: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p.6.之前发现的犍陀罗语佛教文本《法句经》《法集要颂经》《波罗提木叉》《温室洗浴众僧经》等,均非出自犍陀罗故地,却是来自古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尼雅河下游)等地,而新发现的几批写本的来源地虽并不十分明确,但大致均处于古代“大犍陀罗”的区域之内。在大英图书馆经卷的譬喻类写本中,提到了两位犍陀罗地区的月氏王(“总督”或“国王”)名号,而这两个名字恰好在出土的公元1世纪早期的金币和铭文中出现过,为这些佛教写本形成的年代提供了直接佐证。王邦维先生又注意到,在东晋法显从师子国(斯里兰卡)带回的《佛说杂藏经》里也提到过“月氏王”,尽管未必就是上面佉卢文譬喻写本里所说的两位,却足以说明公元4世纪末法显所翻译的《杂藏经》在产生或流传过程中,确曾与犍陀罗地区的某一位或某几位月氏王发生过关联。*王邦维:《论阿富汗新发现的佉卢文佛教经卷》,版权前揭,第17页。眼下,正有中国学者根据新疆尼雅遗址的佉卢文发现,试图对古鄯善国僧伽的社会地位、世俗生活、政治参与、经济关系等方面作出探索,业已初见成效。*杨富学、徐烨:《佉卢文文书所见鄯善国之佛教》,《五台山研究》2013年第3期。而犍陀罗语文本所反映的犍陀罗地区的情况,比如像法藏部和说一切有部的兴衰与新旧王朝更迭的关系等问题,*R.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ndhr: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p.11.同样填补了印度史和佛教史上的缺环。
根据所发现的文本复原犍陀罗佛教的派系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亦不无可能,但需格外谨慎。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大英图书馆经卷已被认定属法藏部,且没有出现任何与大乘经典有关联的迹象,同时人们过去又向来认为犍陀罗地区确曾在大乘佛教的发展中发挥过关键作用,邵瑞祺教授曾就此认定,“如果说这些新文献对犍陀罗地区之于大乘佛教的发展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也是否定的,至少是间接的”。*R.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ndhr: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p.12.据当时已知的大英图书馆经卷和斯尼尔经卷来看情况确是如此,但就在之后不久发现的巴焦尔经卷和巴基斯坦私人收藏经卷中均出现了大乘经籍,其中巴基斯坦私人收藏中的《般若经》可以确定为公元1世纪的写本,*See Harry Falk, The ‘Split’ Collection of Kharosthī Texts; Harry Falk & Seishi Karashima, A First-century Prajpramit Manuscript from Gandhra -Parivarta 1 (Texts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1).至少在年代上并不明显晚于大英图书馆经卷和斯尼尔经卷。这只能说明此前的经卷很可能恰好是出自法藏部的一批寺庙藏书,而当时法藏部又与刚刚兴起的大乘部派之间少有学术上的交流往来。
中国佛教经典大多从西域传来,大乘经典与后来所贬称的所谓“小乘”大体同一时期流入并被译介为汉文。在中国本土学者成长起来以后,对于佛教义理的理解多有争论,这些争论最终往往要诉诸于印度原典方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这时那些大乘、小乘原典的原始出处、渊源流变就变得至关重要,不但可能决定哪一派别所奉经典在判教中地位更高,更关系到对佛教义理的理解是否原汁原味、是继承还是扭曲了佛陀的教化这类根本性的问题。
以《般若经》为例,有学者研究表明,在中国最早译介大乘经的支娄迦谶所译《般若经》的原始文本即当为犍陀罗语,其中带有一些同一时期其他印度俗语中没有、仅存于犍陀罗语的音调变化,而在巴基斯坦私人收藏经卷新发现了《般若经》残片,这些残片的内容恰可与汉译《八千颂般若》第一章和第五章大体对应,也辅证了这一假设成立的可能性极大。*Harry Falk, The ‘Split’ Collection of Kharosthī Texts, p.20; Harry Falk & Seishi Karashima, Afirst-century Prajpramit manuscript from Gandhra -parivarta 1, pp.19-20.这一发现无疑将牵涉到大乘经典的源头、出现时间、汉译大乘经的根基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即便不能马上提供明确答案,也必将给这些问题的讨论增添极具分量的证据。
2. 带来了观察和理解不同佛教传统的新视角
以佉卢文手稿所代表的犍陀罗语文献与婆罗谜文字体系所代表的梵语文献相比,总体数量明显较少,不过却也比我们向来以为的多很多。从前文所列的目前已基本辨识的文本来看,犍陀罗语佛教文本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经、律、论到偈颂、注疏、史传、佛赞、譬喻、本生故事、戏剧,囊括了后世佛教典籍的大部分类型,而这一点很可能喻示着一个激动人心的假设——一部古“犍陀罗圣典”即“犍陀罗三藏”体系的存在。这些犍陀罗语文献在义理上与我们熟悉的早期印度佛教决无分歧,但文本体系却与已知的任何一种佛教传统均不相同。一方面,新发现的各种犍陀罗语文本大多与已知的梵语、巴利语、汉语、藏语系典籍中的一种或几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的对应,但从文本内容、文本组织到文本内部段落的编排上看,又与任何一种已知的佛教传统均不尽一致;另一方面,这些犍陀罗文本中明确存在着在其他任何一种佛教传统中均找不到的内容,尤其是存在着一些有别于所有其他传统的论注,其中不乏一些与犍陀罗当地的人物、传说直接相关的记述。这些证据即使尚不能充分论证一个独立于其他佛教传统之外的成熟的“犍陀罗圣典”体系存在,却足以勾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它们很可能正处于邵瑞祺教授所说的“前圣典”或“原圣典”阶段,作为圣典,其内容、结构编排、文本范围尚未完全成型,而在这些写本所属的年代,“佛教文本书写不过是对更古老的口传心记传承方式的一种替代或补充”。*R.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ndhr: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p.11.
存在一个“犍陀罗圣典”体系的假设,对未来的佛教研究将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对佛教义理的学术探索,还是从修证角度探寻佛教的真精神,都会生发出还原原始佛教的诉求。至于还原的方式,西方学者一向的做法是从南传佛教的巴利圣典中寻找依据,认定巴利语文本是最早、最可靠的文献,甚至对历史同样悠久的汉传佛教传统亦不屑一顾。不用说,这种看法本身即有所偏颇。更何况巴利语典籍的原始版本据信是用僧伽罗语所写,今已所存无几。如此,则新发现的犍陀罗语文献至少在年代上要比现存的巴利圣典更早,基本可以确定是印度古代俗语论着原始版本的最早遗存,那么按此前的逻辑也就比巴利圣典更为“可靠”。因此“犍陀罗圣典”体系的浮出水面,至少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西方学界长时期以来独以巴利圣典为尊的偏见,同时也将提供一种与先前已知的早期印度佛教巴利语、梵语、汉语及其他文本传统进行比较和评价的新标准。
3. 从佛教文学的角度可以看出早期佛教布道的本土化策略
新发现写本的文本类型尽管十分多样,但整体上看,与义理并不直接相关的各类佛教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也像新疆出土的梵语、吐火罗语佛教文艺作品一样,这些犍陀罗语佛教文学作品中既有与其他佛教传统相重叠的部分,也掺入了犍陀罗本土的内容,带有某种特殊的犍陀罗风格。
偈颂类文本是几批写本中出现较多的一种类型。显然,偈颂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易学易诵,琅琅上口。邵瑞祺教授曾基于大英图书馆藏品推测说,这些藏品当是供学习使用的不同类型典籍的代表性选本,表现为一些常用的研修文本和背诵文本的随机组合。*R.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ndhr: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p.12.但结合其他几批来源不同的经卷来看,偈颂文本的反复出现,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在佛教早期向外传播过程中对偈颂这一体裁的偏爱。众所周知,《法句经》是佛教初学者的入门书,中译本中已有四种不同版本,南传亦有自己的版本,出土文献方面,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于阗三地均发现了犍陀罗语的《法句经》写本,至少一种属大众部的梵语《法句经》残片,另外还有佛教混合梵语《法句经》(Patna Dharmpda)写本,这些《法句经》分属多种不同的传本;*对不同版本《法句经》的比较研究,可参见Miroslav Rozehnal, The Dharmapada: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Dharmapada:Research in Chinese Versions of this Ancient Buddhist Text, 1998; Margaret Cone trans., Patna Dharmapada, 1989.大英图书馆藏品和斯尼尔藏品中均出现了佛陀弟子在喜马拉雅山阿耨达池湖滨自说本起的《阿耨达池偈》;而在巴焦尔藏品和斯奎因藏品中则同时出现了最基本的律藏文本《羯磨本》和《波罗提木叉》,大英图书馆藏品中亦有些内容与汉译律藏中沙弥学处类文本存在相似之处,这些迹象似乎在在表明了这几批新发现经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布道”这一总目的,同时或许也揭示了这一时期犍陀罗佛教寺院在布道方式上的初步性、基础性特征。在几批经卷中均大量出现的另一种体裁是譬喻。据邵瑞祺教授的看法,犍陀罗语譬喻类文献可分为在佛陀时代为人熟知的传说人物相关的一类和以当时月氏人治下的犍陀罗为背景的一类。陈明先生在研究新疆出土的佛教譬喻作品后指出,“譬喻故事不仅为印度譬喻文学的宝库增添了数块宝石,更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研究譬喻故事的整体形态的演变,以及研究印度原生的故事在西域的本土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融合与变异”。*陈明:《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文献季刊》2003年1月第1期。但除了文学和文学史价值之外,我们从犍陀罗语藏品中还可以看到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所施设的方便以及佛教对本土化的注重。通过后期汉传文本传统不难了解,犍陀罗曾是早期阿毗达磨研修的重要中心,在新发现写本中也存在为犍陀罗所独有的论注类文本,也足以说明犍陀罗地区佛教研修的深度。但在那些具有广博艰深之义理知识的僧伽带领下,我们所见到或者说僧伽所乐于展示给众人的恰是艰深的反面,即以脍炙人口的偈颂、圣歌等形式表达对佛陀的颂扬和赞美,同时极富热情地讲述具有教化意义的譬喻故事和本生故事,或热衷于给月氏王、阿育王这种有功于佛教传播的王者作传。显然,这些类型的文本在社会上的宣传功效和传播效率要远优于经院式的讲经说法。事实上,这正是佛教在各地传播时一向优先采取的本土化策略,实践证明也确实行之有效。由此,我们还可进一步探索佛教僧伽与佛教义理阐述、佛教宣传策略的关系,僧伽如何通过对典籍的拣选来实现以佛法改造人性的布道理想,以及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惩戒机制与佛教教诫传播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4. 还牵涉到其他一些对佛教典籍的认识问题
根据对出土文献的考察,有些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佛教典籍中的律藏文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均以口传心记的方式传承和传播,直到贵霜王朝以后才开始逐渐付诸笔端。如邵瑞祺教授注意到,出土的早期梵语文献中完全没有经藏和律藏文本,而新发现的古犍陀罗语文献中也完全没有律藏文本,经藏虽有但所占比例较小。因而他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在公元1世纪,寺院的藏经阁里原本就少有或压根没有律藏文献,因为这一时期将经文记录下来只是保存经文的次要或补充手段,而口传心记仍是经文传承的首要方式,“像《波罗提木叉》这种基本的律藏经文,被记录下来的可能性十分微小,集体诵戒制度完全避免了它们惨遭遗忘或损毁的危险”。*R.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ndhr: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 p.163-164; see also Ingo. Strauch, The Bajaur Collection of Kharosthī manuscripts -A Preliminary Survey.邵瑞祺等学者的这种猜测对于梵语和其他佛教传统来说准确性如何尚难断定,但对南传佛教一系而言恐难成立。巴利语系佛教根据自身传统,始终相信律藏在第一次结集时即已形成,到公元前1世纪记录成卷,也就是成文于南传佛教的第四次结集“阿卢寺结集”之时。*See Wilhelm Geiger Trans., The Mahqva/sa, Dehiwela(Sri Lanka): Buddhist Cultural Center, 1912, p.237.而在邵瑞祺教授提出这一说法几年之后,巴焦尔经卷中就发现了与大英图书馆藏品大体同一时期的律藏文本《羯磨本》和《波罗提木叉经》,很大程度上推翻了这种假设,却支持了南传佛教对巴利圣典的普遍信念。
大乘经与不同部派之间的思想渊源问题,之前与大众系的关联是相当确定的,与法藏部的关系则有所存疑,而从大英图书馆手稿中发现的属法藏部一系的本生故事和斯奎因手稿中发现的《菩萨藏》文本,很大程度上为犍陀罗地区法藏部对“本生”说的重视及其与大乘《菩萨藏》之间的渊源关系提供了明确的佐证。其他像已经发现的多部《法句经》写本,其源头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是由于时代、地域、部派人为形成的文本差别,还是各地各派原本就有各自不同的《法句经》,这一历时弥久的悬案将随着各版本的比较研究日趋明朗。我国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一度兴起过佛教究竟何时传入、《四十二章经》到底源出于阗还是大夏的论争,对于追求佛教义理的人来说似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但无论如何仍是书写中国佛教史无法规避的正式开端,而要重建历史细节、敉平纷争,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与《四十二章经》渊源颇深的《法句经》的版本考察。
总而言之,新发现佛教文本的价值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不难预见,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犍陀罗语佉卢文佛教写本还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