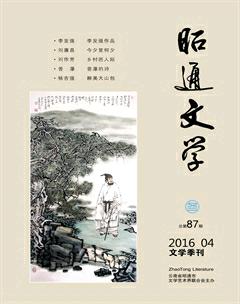父亲的岁月
父亲是一棵树,一棵植根于丛林中既不高大也不出众的树。没有挺拔的身姿,也无耀眼的枝叶,惟有深深扎在厚厚泥土中深长的根须。历经风的肆虐,有过雨的洗礼;经过霜的考验,更有冰雪的冻结。艳阳高照之后枝叶仍郁郁葱葱,生命的枝叶依然如故,哪怕土地贫瘠、哪怕缺光少雨,总是默默心怀对泥土的一腔眷念,对周围环境,对同生同长的树木,对养育自身的土地从未存点滴怨言,总是一往情深。
父亲说,既然落地生根,与脚下土地的结合就是上苍注定的缘分。既是缘分,就要珍惜就要认命。是的,即便在暴风骤雨生活清苦的年代,父亲这棵树对土地的挚爱仍丝毫未减,并不曾懈怠,对一路走过的艰难困苦总是付之一笑甘之如饴。终将岁月的年轮扩展到耄耋之年。
父亲原是生长在乡间的一棵弱小的杉树,有幸能从农家土地挪到丛林中成为一株国家名下的有用之树已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事。
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建设为热血青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父亲这棵树那时正抽枝发芽,正值勃勃生长之季。正巧,一次不期而遇的机缘突兀而幸运撞到初中刚毕业的父亲跟前。
心怀一腔报国情怀,父亲报名参加了当时地区人行在县内的招干考试,在众多的应试者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笑绽枝头,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成了国家这片林地中一棵有用之材。
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离开了曾经生养过的土地,父亲这棵树一心扎根于国家这块沃土,想成长为国家和人民的有用之材。虽成不了栋梁、成不了主干,但成为一块边角小料,成为安放桌椅的垫木父亲也心甘情愿,毕竟也派上用场。在同辈人眼中,父亲就是个爱跳爱唱乐于做事而又不争名夺利之人。别人不愿做的杂事,父亲总收入囊中,事后一一梳理。
多次转换角色并对工作总抱极大热情的父亲始终将耕耘土地的情感与勤劳全倾注于工作之中。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勤勤恳恳的德行一直与父亲如影随形。被组织看重的他4年之后从金融部门调到了当时的县委会。调过去几年后又被单位要回,归队之后才几年又再次调动到县委会,那时双方领导都有些不舍,几进几出之后才不得不于80年代初因金融部门的归队政策而再次返回原单位,直至退休。
二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正是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据父亲说,自参加工作之日起至“文革”结束,他其间经历了“三反五反”“大鸣大放”“反左”“大跃进”等运动,一生经历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就有数十个。特殊年代,每个运动结束都会有一部分人成为批斗对象。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头天晚上两人还同宿一屋,同为一个战壕里的革命战友,次日醒来可能其中一个就成其为“敌人”。说怪不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成就了特殊的政治气候。当时就这样,运动要求个个表态,人人过关,无一例外。因运动而致夫妻离婚、父子反目和弟兄成仇等例子不胜枚举。对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父亲虽弄不明白,但银行的业务总是要有人去做的,这是父亲最质朴的观点。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从小生长在农村的父亲,既不是林中之秀也未堆出于岸行高于人。自植根于新生共和国这片热土并爱上她广袤的大地和欣欣向荣的未来之后,忠诚善良、勤劳节俭、秉直刚正的本色如山间岩石的本性一般难以改变。在对待国家和集体、整体与局部、组织与个人及人与人关系上,事事以大局为重,处处为他人着想,从不损人利己。做事不偷尖耍滑,对人以诚相待,工作竭尽全能,且从不夸夸其谈,干得多说得少,从不张扬。“尽善矣,尽美矣”是他处事为人的目标,以致之后成为单位为数不多的业务骨干。
在反右斗争的前夕,小组会上有人天天点名要父亲及所有人员行动起来,敞开心灵海阔天空想说啥说啥,或把观点写在一张大纸上,张贴出去让群众看或评论,与不同观点的人展开辩论。这对过惯苦日子只愿多干少说的父亲来说,有份稳定工作,且每天风不吹雨不淋,吃得饱穿得暖,还有啥意见可提呢?感谢党感谢组织还来不及嘞。
当别人痛痛快快“大鸣大放”表达各自观点,将“大字报”撒得雪花般漫天飞舞之时,父亲向组织倾吐的都是肺腑之言和感恩的话。
一番痛快淋漓的语欲之后,接二连三地就有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被下放到农村去改造,这一改如水如花的年华就随水漂去,许多个人许多家庭的命运就因这顶一戴二十年多年的帽子而被迫彻底改变。改变得有些突兀有些让人唏嘘不已。
父亲未曾料到对业务的执着竟让自己逃过一劫。在接下来接二连三的运动中,父亲总是恪守自己的原则,不害人不整人不赶政治时髦;工作趋重避轻,只要有抛头露面和出风头之事,就退后半步让别人风风光光去“抓革命”,自己甘愿辛辛苦苦“促生产”从早到晚忙业务,将枯燥无味的繁琐之事一个劲地往自己身上承揽。
金融工作需要一个懂业务乐于奉献之人将精力全心身投放到琐碎事务中,这才能让领导放心去“抓革命”。那时的父亲已升至会计股股长,单位的性质早已决定了父亲无法脱离柜台。当别人将热情消耗在无休止的运动中,父亲的业务水平却在慢慢变化,变成金融部门为数不多的业务能手。金融工作有其特殊性,不管“革命”闹得如何轰轰烈烈,银行现钞每天都得进和出,金库还得要有业务强思想过硬的人管。父亲就此成其为这项工作不二的人选。
用当时时髦的话说,父亲根正苗红,祖孙三代都是贫农,根没问题,值得信赖;政治过硬,实践证明一直对党忠心耿耿,无半点对党不忠不敬的言语和行为,不可谓不红啊,可重用;业务能力强,无论出纳、会计和信贷等业务都能独立承担,且没出过错,最适合担此重任。最让领导放心的还有任劳任怨,从无怨言,不管头天晚上下班多晚,只要安排,第二天一样不会误时。
最令大家难以忘怀的是临下班前一个下午,出纳付款时多付了500元给对方,在与之复核现金账目时被父亲发现出纳霎时惊出一身冷汗,紧张得连抽泣声都时断时续,一时竟语无伦次。反复核对无误之后,她说,这几乎我两年的工资啊!经提示加快确认,出纳认定了多拿走现金之人。将工作安排妥当,父亲即刻带上人一同找到那个人的单位,因是周末,单位上的人说他已经下班回老家去啦。父亲又连忙赶了二十多里地,插小路超近路,费尽周折在途中拦截到此人。通过解释、说服和软硬兼施的法子,最终追回了这笔多付的款。这让当事者、股室及单位三方都皆大欢喜。
父亲就这样成为了单位业务的一根拐杖。也就是这根拐杖让身为造反派头目的单位领导可高枕无忧领着人去“抓革命”。这一抓,苦的却是父亲。每天接下来的事繁杂枯燥不说,而且干的是两三个人的工作。因为需要有更多的人同去“抓革命”。父亲也争气,不论任务多繁重,人手如何紧,几十年的金融工作都没因经济出过错,也没赔偿过哪怕一分钱。这在金融系统父亲那一辈人中,极为罕见。
父亲常常以此为荣。正因如此,父亲在业务上被“抓丁”已是家常便饭。也因如此,父亲才错过一场又一场,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无休无止的批斗会。当时,有人曾为父亲感到惋惜,惋惜有文化、有能力的父亲错过了无数次让自己风光、出风头的大好机会。对此,父亲总一笑了之。谁料,这也是一柄双刃剑。当浑浊渐渐变清,曾经用这柄剑伤害过别人之人,日后却又反过来伤了自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才仅仅十年,也许十年都不到。真是盛衰无常,世事难料!
我清清楚楚记得,下班之后的父亲,时常让饥肠辘辘的我们兄妹几人久等在菜饭飘香的桌前。此时的母亲就会要求我去看看父亲,催促他不要耽误,尽量下班早些回家。也只在这样的景况下,我终有机会得以帮父亲提上装有大量现钞的箱子一同进入一间戒备森严,没有窗户且铁门重重的钱库。以后才知晓那叫金库,是银行专门存放现金的地方。
许多时候,也就是“造反者”在台上风光之时,父亲却还伴随着昏黄的灯光,翻着他的账本,用母指、食指和中指上上下下一遍又一遍娴熟地拨弄着一把宽大、深赭色算盘上的珠子……
每当那时,我最爱看的就是父亲手指拨弄算盘珠时回来舞动的神情,那一刻,有忘情、有专注,还有陶醉。那一刻,我觉得父亲的手拨弄的不是算盘珠,而是在跳舞,正跳着一曲像《红色娘子军》或《白毛女》一样使我着迷的巴蕾舞。还有珠子上下撞击所发出时急时缓、时轻时重的声响。那声音、那韵律如同从当年家喻户晓的钢琴演奏家殷承宗弹奏的琴键间汩汩流淌出的美妙旋律。
父亲早已将枯燥的业务演化为一门他所钟情的艺术。算盘是他的钢琴,算盘珠则是助思想自由驰骋的按键。这是我多年后的感悟。父亲喜爱音乐,但那时的家境不容许父亲有过多的想法。难怪父亲那样执著、那样投入、那样痴迷。在父亲眼中,那把与他朝夕相处的计算工具是算盘,但对父亲来说又不仅仅只是一把算盘。是什么呢?也许只有父亲最明了。还有,父亲从不杀生。母亲偶尔买回来一只鸡,每次都是父亲请单位食堂一位姓方的伯伯帮忙宰杀一家人才能够得以食用,无一例外。
母亲常常说,我们家一年吃多少只鸡,方伯伯最清楚,而且比我们都清楚。是的,在我记忆中,从没见过父亲动过刀。母亲不希望大事小事都去惊动别人,要父亲学会杀鸡这等小事,以免事事麻烦他人。不知何故,父亲一直不愿学。成人之后的我联想到他老人家的为人,一生的处世之道和平安走过那段风雨交加的岁月,我,似乎有所感悟。
三
“文革”是各项运动中斗争最激烈、最残酷且时间最长的一场暴风骤雨。是“走资派”和造反派你争我斗的内耗。当年许多与父亲一同共事的战友就活生生被划分成两派,斗争不可避免地在彼此间展开。父亲虽划在“造反派”一边,但却不参与造反,不说没良心的话,更不会充当愤青似的打手,同事有难都会情不自禁出手相助。
记得一个闷热得让人出气都感到热辣辣的星期日下午,“造反者”将一位 “走资派”拉到会议现场,强行下跪要求“坦白”,一“造反者”习惯性地摘下被批斗者的帽子,用五指狠狠一抓,才发觉头发早已剃得精光,只留下一个灯泡似的光头。对“造反者”来说,怎一个“气”字了得。见无“辫”可抓,接下来就上演一阵拳腿相加的“少林寺”,将被批斗者原光滑的脸面加工成起伏的山丘和沟壑相间的峡谷。鼻青脸肿的被斗者连连叫唤,还直呼父亲的名字,不停地呼救,呼喊声像猛然间从天空中滚落而下的雷声,极具穿透力。别人是怎样感觉我不知道,反正一听到这声音我就会心生悲怆和怜悯,声音仿佛能穿透我的心脏,使我怯怯的。喊得令人发怵,并击破厚厚的人墙、穿过层层的门窗传至营业室。闻讯之后的父亲即刻放下算盘和账本一路小跑直奔会场,请求手下留情,还陈述了一大通领袖人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精神。由于双方都信赖父亲,批斗会的氛围才少了些火药味,批斗者这才放弃了往死里打的狠心,将武力攻击改为语言批斗。
当时的举动虽冒了些风险,但能为被斗者减轻肉体苦痛,父亲总是乐此不疲情愿冒此风险。
另一次批斗会,被斗者被打得奄奄一息丢在一间阴暗潮湿屋子里无人照管,无食无水,疼痛和折磨将呻吟在夜色中放大得愈加凄惨。临睡前的父亲怀揣心事,一番侦察之后乘夜深人静,将备好的食物、水和一包东西给了母亲,要求带着我一同去给这位伯伯送去。已在睡梦中行走了多时的我不得不收回睡意与母亲一同轻一脚重一脚地摸到那里,我在暗中放哨,待母亲将食物悄悄放下一番交待之后,才拉着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转了几个圈折回家中,使那位可怜的伯伯度过了难熬之夜。
阴霾散尽之后,凡与“四人帮”有牵连的造反派人物纷纷进了“学习班”,个别头目还锒铛入狱,丢官不说,饭碗也丢了,最终还被逐出革命队伍。
谈起这段历史,当年与父亲一同共事过的前辈曾对我说,你父亲是运动中的常胜“将军”,每次都能毫发无损顺利过关,狡猾狡猾的。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父亲说。
四
无论何时,做人都得讲原则,要有是非观念。上能对其天,下能对其地,这是退休后父亲对那段历史的切身总结。当然,世事难料,那年月,无辜被诬陷以致含冤而亡者有之。那段历史在父亲眼里就如同身上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只要一触及便会隐隐作疼。虽然自己没受到冲击,但只要一想起同事、战友分为两派相互打斗……就不寒而栗!
时光如水,岁月无情。曾不可一世之人都为此付出了应有代价。吃尽若头受尽折磨者也苦尽甘来。父亲当年因心甘情愿地演奏他的“钢琴”——忙于业务工作而躲过了一次又一次抛头露面及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红不紫也就不足为奇。他总默默地完成自己的戏路,该衬就衬该退则退,从不抢主角的戏,甘为配角。这是父亲的做法。在我看来,父亲更像一棵树,一棵甘愿深藏在密林中毫不起眼的树。既不是临风的玉树,更不是林中之秀。又像一棵草,一棵甘为红花相衬的草。也许是父亲的性格,父亲的做事风格和他的处世方法让他躲开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境地。
事物有其内在规律。水至零下变成冰,升到极点已为气。冰和气还是水吗?人与物一样,谋事为人不能越矩,一旦过了头性质就会变化。性质发生变化还能像先前一样与人友好相处吗?回答是肯定的。
能在荆棘丛生的岁月中穿行几十年仍安然无恙,毫发无损地软着陆是何等不易啊!假若是我肯定做不到。
父亲是幸运的,幸运的父亲的岁月是我人生的一面镜子。
作者简介:刘平,男,笔名文丰。作品散见于《云南工人文艺》《时代风采》《黄金时代》《故事大王》《昭通文学》《楚雄文艺》《云南日报》《云南经济日报》《亮报》《昭通日报》《达州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