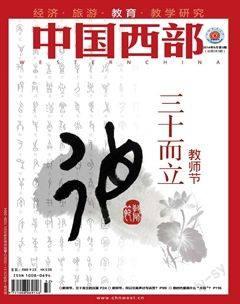教育救国: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傅国涌
从鸦片战争开始,古老的中国揭开了一幕千古未有的变局,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之威,蛮横地敲开了中国封闭了两百年之久的国门,惊破了天朝大国的千年美梦。一批开明的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经过痛苦的蜕变,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已不再是位居世界中心的强大的“中央大国”,中国人只有勇敢地正视自身落后的现实,积极自强自救,才能在优胜劣败的生存竞争中免遭淘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弥漫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几乎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带着国家危亡无日的深切忧思,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探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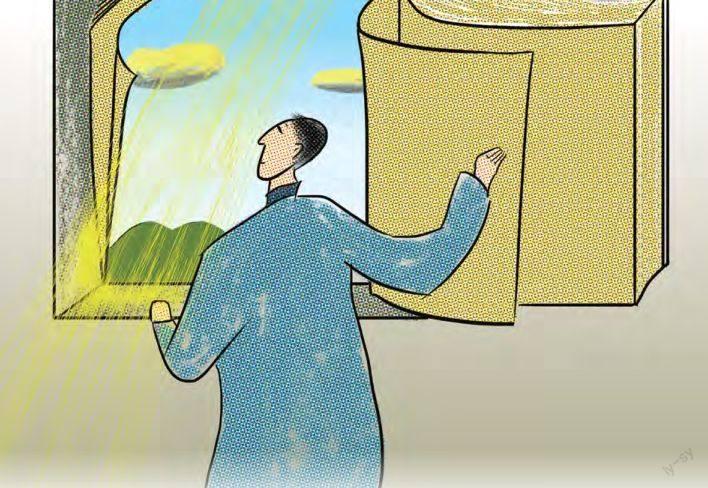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正是满怀着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爱国激情,投身教育探索的。像蔡元培主张五育并举、学术自由、教育独立,黄炎培提倡“大职业教育主义”,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运动,陶行知从事乡村教育改造,与其说是一种教育探索,毋宁说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追求更为贴切。教育救国是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不仅如此,振兴颓唐国势,挽救民族危亡,还是他们提出自己教育理论、学说、主张的立论依据。这些教育理论、学说和主张,实际上是教育家们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为救国所开出的药方。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为教育救国所开出的药方,各具特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受惠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又得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滋养,对中国教育问题这一病症的把握更为精确,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也更为深入,因而更能对症下药。
在民国教育界扮演重要角色的蔡元培,一向视教育为救国之唯一法门。早在民国元年出任教育总长时,蔡元培就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即以军国民主义教育谋求强兵,以期保卫国家,抵抗强权,恢复国权,且防范军人专政;以实利主义教育充实国民生计,发达国家生产事业,谋求国家之富强;以公民道德教育培养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以消弥兵连祸结、贫富血战之惨剧;以世界观教育提倡超越现象世界的实体观念,使人泯营求而忘人我,时时以全人类的永恒幸福为鹄的;以美育沟通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帮助完成世界观教育。蔡元培认为此五者不可偏废,“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身;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 。应该说,蔡元培的主张是高瞻远瞩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比较全面地考虑到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其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能动作用,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个既重治标,又重治本的教育方案,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一经提出,就得到普遍认同,开一时风气。美感教育,尤其是世界观教育,虽说最初人们反应冷漠,但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在他主持北大校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也被人们逐渐认识。
与蔡元培着眼全局不同,民国时期的另一些教育家则是从以下三个不同角度把握中国问题,进而提出各自具体的教育救国方案的。
一是从社会现象角度来把握中国问题。黄炎培,他有感于“一般社会生计之恐慌为一刺激。百业之不改良为又一刺激。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者之无算为一大刺激”,积极倡导职业教育。黄炎培大声疾呼,“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之问题,阙生计。曰:求根本解决生计问题,阙惟教育。”在黄炎培看来,“人类社会,所以扰扰不宁,是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人生而有求,求之不得而有争,有争而有杀,爱群之心泯灭,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大千世界,惨祸遂伏其中。”因此,“人类间唯一大问题,是‘全生去杀。”中国要自强自救,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大问题,具体的办法便是实施职业教育。黄炎培认为,要解决“全生去杀”这一问题,“从客体言,在增进所以供给生活需求之分量与效用;从本体言,在广其知以大其爱” 。而职业正是“增进所以供给生活需求”的最好手段,教育又是“广其知以大其爱”的最好方法,教育与职业的沟通、结合,必将“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如此人世间的一切不幸、一切罪恶、一切惨变,通通都会消失,国家自然也能富强起来。
二是从国民素质的角度把握中国问题。有晏阳初、陶行知诸人,以晏阳初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晏阳初积极投身平民教育运动,将平民教育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我们内受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同潮流的教训,自觉欲尽修齐治平的责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别无根本良策。”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基本的问题只有四个,可以用“愚、穷、弱、私”四字来概括。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国民素质太低。只有着眼于全体国民,从事平民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造就一代新民,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因此,晏阳初认为,“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
三是从文化的角度把握中国问题。代表人物是梁漱溟。与晏阳初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愚、穷、弱、私”等问题,而是中国何以存在这四大问题。仅仅着眼于表面的病象是不够的,必须往深层追究其所以然,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在梁漱溟看来,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其现象而言,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结构在欧風俄雨的冲击下日趋败坏,呈现出“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混乱景象。就其实质而言,“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解救之道就是如何为中国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如何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吸收现代欧美的科学技术文明,重建新的民族文化。简言之,就是如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梁漱溟认为:“教育的功能,不外是‘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换句话说,就是‘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文化的改造与重建维系于教育,这种教育便是民众教育,便是乡村建设。因此,“教育必须站在社会的第一位,以学术指导社会的一切。”梁漱溟试图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形成一种教育家的社会运动;或是社会运动者运用教育功夫,去培养新礼俗,完成新的“乡村文明”;或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从而为整个社会开出新的生机。
在这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无论是从哪個角度认识中国的社会问题,都得出同样的结论:教育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与前几个阶段的教育家不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突破了运用意识形态处理政治问题的传统观念,不再天真地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就在于教育落后,因此也不再把教育作为救国的直接突破口。他们开始认识到,教育落后,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中国积贫积弱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要救亡图存,必须着眼于社会的整体改造。在他们的救亡逻辑中,主导中国自强自救的载体是社会改造而不是教育改革,教育是作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手段而受到重视的。他们开始从宏观上研究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政治、经济的整体关系,强调教育必须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作相应的改革,才能真正为救亡图存服务,施何教育必须要察何社会。他们不再把教育当作一项脱尘离俗的事业,而是强调教育应“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不能脱离整个社会条件,并将之视为教育救国的前提之一。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为教育在整个救亡图存事业中作了新的定位。
确实,由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把握中国的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所提出的教育救国方案,众说纷纭,但所有这些药方的“药引”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提高国民素质,养成健全人格。他们继承并发展了维新派“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进而深入到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在新的高度上探讨了文化教育问题。他们试图把社会改造建立在千百万人的觉醒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上。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提高国民素质,养成健全人格作为教育的重要目的。譬如蔡元培就主张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以为培养完全人格是学校爱国教育的主旨。他在爱国女学校演说时,明确指出:“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晏阳初则把“除文盲作新民”作为平民教育的目标,试图通过平民教育,培养二十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公共心及健康体魄的“完整的人”。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从人生问题上对人进行启发指点,使之有合理的人生态度,奋勉向前。所有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教育家们对人的主体价值的高度弘扬,他们试图通过教育和谐地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因此,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在设计教育救国方略时,往往就社会与人生两方面立论,给人以通贯内外之感,较维新派单向为社会“开民智”,思想更为深刻。